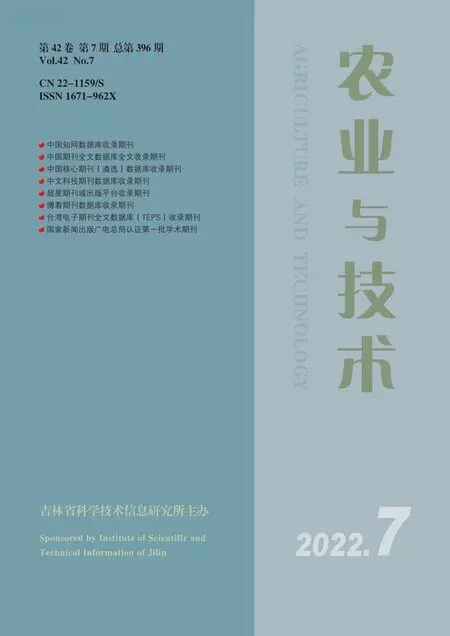社会工作助力民族村落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以文化敏感性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
王钰 佴彩霞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引言
2020年我国已实现所有的贫困县脱贫摘帽,昔日的贫困人口不愁吃穿,住房、医疗和义务教育均得到有效保障,当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成为了新的时代主题。习总书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贫困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民族村落,大部分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缺少支柱性产业发展,民族村落的乡村振兴是现阶段我国乡村振兴工作的一项重难点内容。
社会工作,诞生之初的重点关注领域就是工业化的西方社会中日益突出的贫困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社会工作也是一门强调助人自助的科学与艺术。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中,社会工作已经协助取得突出成就,将社会工作继续引入民族村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民族村落实现乡村振兴不仅是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必然要求,也将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力量在民族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中的优势,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民族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文化敏感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村落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社会工作要介入民族村落乡村振兴,需澄清一个核心概念——何谓民族社会工作,开展民族社会工作要依据国家的相关民族政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还要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对物质或精神上处于困境的少数民族个体及群体实施救助服务,并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最终起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谐的作用[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除了要遵循社会工作专业理念、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外,由于在民族地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且面向的群体是少数民族群体,其常常有着独特的文化,所以开展民族社会工作与一般的社会工作相比,开展工作更要注重与服务对象的文化差异[2]。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各学派有众多不同的解释,不过有一点几乎为各学派都认同,那就是文化是特定社群的独特生活方式。把这个概念继续延伸,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对事物的看法和观念也大致相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尽管各民族之间的共性逐渐增多呈民族融合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各个民族仍然拥有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特征,尤其是一些世代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其与外界的联系较少,较多地保持着本民族世世代代的生活习惯和浓厚的文化特色。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曾是脱贫攻坚的重难点,新的时代主题下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振兴,这些地区依旧是党和国家最关注的地区。
社会工作不但强调助人自助,而且注重文化敏感性与价值中立,社会工作者可以深入民族村落充分调动少数民族群体的优势资源,促进其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振兴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工作引入民族村落中去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外来的社会工作者尽管理论学习扎实也具备着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深入民族村落之前还做好了相关功课,如查阅了该民族以及当地的相关资料,做足了心理准备,然而只有这些专业知识、其他地区工作积累的大量工作经验和外在学习来的“文化敏感”性,就深入民族村落开展工作,常常会陷入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下去的尴尬局面。张和清等学者在云南省一个壮族村落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最深的感悟竟然是“面对复杂的民族村落文化环境,有种无能且无知的感觉,这常常使我们感到举步维艰。与村民接触的越多,在村庄工作的时间越久,反而更加察觉到自己无知与无能为力。我们用在外界习以为常的‘助人’价值观和方法在民族村落开展许多活动时,总是意想不到的遭遇种种困难,效果不但不明显,有时甚至会与我们‘能力建设’的目标相左[3]。”外来的社会工作者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在面对与自己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群体开展服务时,很难实现预期的服务效果和目标,对当地民族文化和习俗、生产生活方式、价值信仰等无法进行深入了解,就会不自觉地产生“文化震撼”,甚至产生“文化偏见”。
“文化震撼”是一种客观现象,没有善恶之分,指的是由于文化风俗、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原本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初次接触另一种文化模式时,心理上和精神上受到冲击的感觉,对文化震撼的处理会有2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处理不好就会陷入“文化偏见”中。文化偏见是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中需要极力避免的一种现象,常常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默认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总是不自觉地会用自己的文化,来评价其他文化群体。社会工作进入民族村落,要帮助其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使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这个过程中不免会涉及到许多少数民族乡村的社区建设、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权利发展的服务,外来的社会工作者依据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就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灌输给服务对象,造成一种文化上的压迫,要实现服务应有的效果,就有可能改变村民惯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村民大多对外来的社会工作者抱有一种戒备心理,如社工带着大家开展打跳、唱歌等这样类型的活动,村民通常是非常愿意参加的,但打跳和唱歌结束后,社工开始拉着大家开会,建议大家少种一些粮食,因地制宜地多种植一些花卉、蔬果之类的经济作物,以此提高家庭的收入,或建议村民送孩子去县城读高中,多读些书走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村民的态度就没有那么热情了,要么以沉默来应对,要么消极的说不懂、不会。这样一来工作就根本无法有效展开。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现阶段不管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还是社工机构对社工的培养,均是通过“灌输式”的学习或培训,告诉社会工作者要具备“文化敏感性”,那究竟什么是文化敏感性呢?尽管专业学习和机构培训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也仅仅只是教导社工开展工作时要做到持有他者文化视角、尊重及同理心等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一种附加的价值伦理,无法真正做到内化。尤其是当面对的服务对象是与社工本人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之前对文化敏感性的“外在培训”就无法避免服务过程中因为存在巨大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震撼甚至文化偏见。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仅给民族村落的服务对象带来困惑,也给提供服务的社工自己带来了巨大挫败感。
因此,在推动社会工作助力民族村落乡村振兴的发展中,必须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根据不同民族服务对象的文化特征,因地制宜的设计和实施专业服务,并充分利用好服务对象文化资源的优势方面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外来社会工作者单凭“文化敏感”的理论负载[4],不但不能促进民族群体“助人自助”,更无法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要求,要真正具备文化敏感性,是一个耗时耗力且需要深入细致的过程,可能需要社工深入民族地区,在当地民族村落与村民同吃同住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做到了解其生活,理解其价值,然而民族村落多位于偏远山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如此大费周折,很难吸引到优秀的外来社工来此服务,面对这种情况,培养一批由当地民族人才组成的本土专业社会工作队伍,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2 本土人才培养:社会工作介入民族村落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2012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教育部等就联合出台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方案要求大力发展“三区”社会工作发展,积极推动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2012—2020年,每年支持“三区”培养500名专业社工人才;每年吸引1000名外来专业社工人才到“三区”提供服务或工作。近年来兴起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也开始进入民族地区,然而这些项目实施的效果却不尽如意。
这些项目通常都有很强的时效性,通常是1a或2a的短期服务,项目时间短就注定了外来的项目社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当地的独特民族文化习俗,设计的服务内容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当地民众的诉求,而且随着项目结束专业人员离开,开展起来的服务活动多数也就随即终止;进入“三区”提供社工服务的通常是高校和研究机构,大多是把“三区”当作一个田野点、试验品来摸索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而且服务提供过程中常常因为其他工作需要等原因而更换提供服务的社工,无法与当地群众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也无法保障工作内容的持续性;培养起的“三区”社工人才也因为当地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不完善而很少留在当地从事社会工作服务,选择去机会更多的东部地区发展。
推动社会工作助力民族村落乡村振兴发展,培养社工人才是关键,现阶段,更多采用的从东部地区吸纳社工人才进入民族村落工作存在着“难吸引、难留住、难根扎”等困境。边疆社会学者李安宅认为,发展边疆社会工作尤其要注重文化方面的沟通,促进边疆社会工作发展就要培养边疆优秀人才[5],值得学习。培养本土的社会工作人才到民族地区提供服务,不仅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服务中因为文化敏感性所带来的各方面不适应,而且现阶段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广大民族群众对社会工作专业不甚了解,对外来的社会工作者也常常心存芥蒂,为实现乡村振兴,社工开展的服务一旦涉及到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时,民族群众出于不信任,配合度往往不高,要在民族村落开展好有深度的,真正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作服务,培养好一批本土民族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必定会事半功倍。
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应积极与高等院校合作增强培养“家乡社会工作者”的力度,鼓励少数民族青年报考社会工作专业,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相关政府部门也应对回乡投身社会工作事业的毕业生给予支持。这些民族社会工作人才,来自当地民族村落,与村民之间有着共同的地缘甚至血缘关系,其在家乡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向村民传授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有利于为村民接受,促进村民的改变,最终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振兴。
要吸纳更多的本土社会工作人才留在家乡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持续的推动民族村落乡村振兴,本土社会工作机构以及民族社区工作岗位的开发就尤为重要。尤其建立本土社工机构,不但可以为少数民族社工人才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使民族社会工作发展日常化、常规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更好地研究社会工作助力民族村落乡村振兴提供一个“实践的大本营”,更好地探索其发展模式。所以,民族地区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本土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政策支持,本土社工机构也要积极争取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以及当地社会组织孵化和培育中心等的专业支持。
3 结语
民族村落的脱贫攻坚,经历了艰难探索和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至关重要,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要求不谋而合,在民族村落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面对民族地区多元的文化环境,要使得社会工作服务能够深入可持续的开展,真正起到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要处理好文化敏感性问题。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和培养致力于乡村振兴发展的本土社工机构,是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一种新探索,不仅可以为民族村落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巨大力量,还可以有效改善少数民族人才外流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