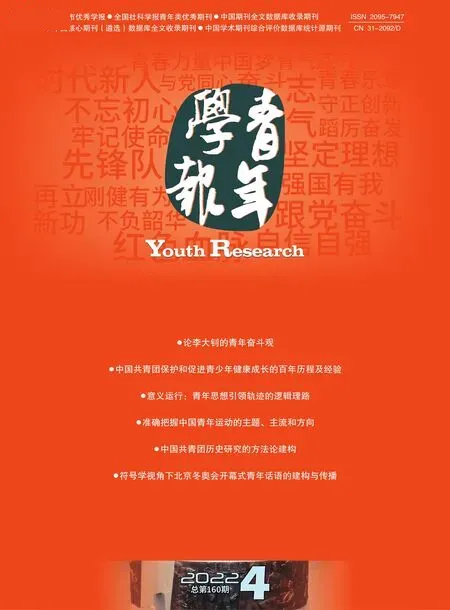研学旅行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制
——基于涉入理论的实证研究
陈莹盈
研学旅行作为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对内往往缺乏明确的自我定位,对外容易受环境与他人的影响。研学旅行在生活与教育之间搭建桥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体验相结合,有助于青少年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之情;体验自然、观照他者,感受文明和谐之意;欣赏他人、完善自我,感悟诚信友善之真。研学旅行的教育功能已为社会、学界认可,相关研究阐述了研学旅行实现其教育功能的内在机制[2]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3]。然而,研学旅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制为何,有待实证揭示。
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研究多以价值观认同情况来衡量,具体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较少。定性论述如董海霞认为要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引导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4];祝新宇从认知、认同、行动三方面阐述了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逻辑[5]。定量研究如王贺以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测量维度[6];王丹从认知、理性、情感、行为四个层面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量表[7]。尽管在衡量维度上略有差异,究其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可划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本研究延续多数研究成果,结合研学旅行情境以认知(cognition)、情感(emotion)、行为(behaviour)三个维度设计量表测量研学旅行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
涉入的概念最初应用于研究社会事件中个人态度的问题,反映某个对象或事件的重要性及与个体的相关程度,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8],之后在消费行为、心理学、休闲旅游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发展。虽然暂未见将涉入理论应用于研学旅行研究,但研学旅行作为一种以教育为首要目标的旅游方式,学生在参与研学旅行时必然涉及由研学旅行所引发的动机或兴趣的心理、情感状态。也有不少学者论述了情感因素在德育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9-12],但少有实证检验。本研究基于涉入理论,以研学旅行涉入的概念来指称个体对参与研学旅行的心理感知与情感状态,它是个体遇到研学旅行这一特定事件时所唤起个体兴趣、关注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个体感知到的关联度越高,涉入度就越深,进而产生一系列与该事件相关的行为。关于涉入的测量目前已有一些较成熟的量表,包括PII 量表[13]、CIP 量表[14]、EIS 量表[15]等。本研究借鉴EIS 量表将研学旅行涉入分为吸引力涉入(attraction involvement)、中心性涉入(centrality involvement)与自我表达涉入(self-expression involvement)三个维度,参考相关研究形成研学旅行涉入量表。其中吸引力指学生对研学旅行的兴趣和重要性感知,以及参与研学旅行所得到的愉悦感;中心性指学生参与研学旅行对其社交圈所产生的影响深度;自我表达指借由参与研学这一行为所体现的主体表征,包括个体的自我价值、品位等。
本研究引入涉入的概念衡量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情感与心理倾向,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为调节变量,探讨研学旅行涉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之间的关系,以期从实证的角度揭示研学旅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制,为研学旅行发挥德育作用提供理论参考与有效建议。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一)研究假设
1.研学旅行涉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影响关系
社会实践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径[16-18],在通过实践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过程中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参与主体的心理感知与情感状态。“情感”与“德育”之间是紧密关联的[19],个体对事物的情绪情感直接影响其对该事物的价值认知和判断[20],情感因素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中不容忽视[21]。不少研究阐述了情感认同、情感共鸣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作用[22-23]。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如果对某一教育形式、内容或方法持有积极或肯定的情感,那么,他们更可能将这些积极的情感转化为接受教育的动力,促进其认真学习相应知识以及主动践行的意愿[24]。可以说,生活态度、心理倾向、情感意志等是影响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主观因素[25]。研学旅行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载体与方式,青少年对这一活动的心理感知、情感投入也会影响培育效果。本研究以研学旅行涉入衡量学生对研学旅行的心理倾向,并作出如下假设:
H1:研学旅行涉入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2.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在消费行为领域,满意度是顾客消费体验后的情感状态[26],旅游者满意度指旅游者的总体愉悦度或满足感,与旅游者的需求、期望、具体旅游经历等有关[27]。旅游涉入与满意度是旅游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相关研究表明涉入是满意度的前因变量,旅游涉入正向影响满意度[28-30]。通过研学旅行体会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旅行体验,根据已有研究结论,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涉入程度会影响研学旅行满意度。同时,个体参与休闲活动的投入程度会影响休闲体验的获得[31]以及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32-33],结合情感因素在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可以推断满意度这一情感状态对研学旅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存在影响。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研学旅行涉入对研学旅行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H3:研学旅行满意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H4:满意度在研学旅行涉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之间起中介作用。
3.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指在参加研学旅行前青少年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持有的认识、认知、认同情况。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复杂过程[34-35]。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朋友圈子,社会环境,媒体舆情,青少年主体需要、动机、兴趣等都会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36-37]。在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少年已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一定的认识、认知、认同。尽管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其思想状况、心理特征、社会意识等呈现出相似的群体特点[38],但不同个体所接触的外部环境、所体认的主观意义具有差异性,因而对价值观的理解也存在不同。有的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不深,有的则抱持着强烈的认同感。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建立在自身原有认知图式和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个体的意识自觉会对价值观形成产生影响[39]。因此,在这样的心理发展与价值观形成规律作用下,可推测经由研学旅行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路径会受到个体已有认知的影响。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a: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对研学旅行涉入与满意度的关系强度有调节作用。
H5b: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对满意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关系强度有调节作用。
H5c: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对研学旅行涉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关系强度有调节作用。
(二)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构建“研学旅行涉入—满意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结构关系模型,探讨研学旅行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为了检验结构关系模型的稳定性,以年级、性别两个类别变量对该结构模型进行跨群组对比分析。需要指出的是,青少年的心灵成长是一个连续的有机过程,不宜作过于详细的区分[40],因此年级上仅划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组别。

图1 研学旅行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取福建作为调研案例地。福建作为东南沿海较发达省份,中小学素质教育起步较早,发展态势良好;且福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具备开展研学旅行的有力基础。研学旅行纳入国家教育教学计划后,福建省积极推进研学旅行教育实践。其中,福建省龙岩市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福建省厦门市、福州市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因此,依据案例地选取的关键性、独特性和启示性原则,遵循三角互证方法,在闽东、闽南、闽西分别选取福州、厦门、龙岩三个地方作为研究样本区域。
(二)变量设计与测量
1.因变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
从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测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本研究所获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数值较好,均值为4.28。
2.自变量:研学旅行涉入
参考旅游涉入相关量表设计研学旅行涉入的题项,从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达三个维度测量研学旅行涉入。
因变量与自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 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变量测量题项及来源见表1。

表1 问卷测量题项及文献来源
3.中介变量:满意度
受访者直接对研学旅行整体满意度打分,该变量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之间的5点测量。本研究所获取的满意度数值较高,均值为4.2。
4.调节变量: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
该变量为连续型数值变量,从“1”代表“完全不清楚它的内容”到“6”代表“对它的全部内容不仅有深入认识,还有强烈认同感”,数值越高代表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已有认识越深入,认同感越强。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数据收集以12—19 周岁中学生为样本。通过问卷网调查平台收集,于2020 年2—5 月在福州、厦门、龙岩三地对有过研学经历的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请他们回忆最近一次研学旅行经历并填写问卷,共收集了735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15 份,有效问卷720 份。福州209 份,厦门278 份,龙岩233 份。有效样本中,女生占55%,男生占45%;年级上,初一占13.33%,初二占13.89%,初三占20.14%,高一占17.92%,高二占20.83%,高三占13.89%。将初一、初二、初三重新编码为初中组,将高一、高二、高三重新编码为高中组,重新编码后初中组占47.36%,高中组占52.64%。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
(一)研学旅行涉入对满意度和培育效果的影响检验
1.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中的量表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学旅行情境设计的,因此先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测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借助SPSS25.0 分析问卷数据,结果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与研学旅行涉入这两组变量的KMO 值均为0.953,Bartlett 球体检验都显著。各个测量题项的负荷因子在0.618—0.841,符合要求。其中,培育效果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634%,研学旅行涉入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035%。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个变量及整个量表的Cronbachα 值介于0.857—0.950,具有较高的信度。
2.测量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研学旅行涉入对满意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借助AMOS23.0 对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与路径系数的影响显著性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表2),测量模型的CMIN 值为562.651,DF值为181,CMIN/DF=3.109,CFI值为0.976,TLI值为0.972,IFI值为0.976,RMSEA值为0.054,满足适配标准(CMIN/DF<5,CFI、TLI、IFI>0.90,RMSEA<0.08)[44],表明测量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2 测量模型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各变量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值在0.801—0.929(因子负荷值>0.71 时项目具有理想质量[45]),各变量组合信度CR 均大于0.8,平均抽取方差AVE 值在0.684—0.850,满足Hair 等提出的评断标准(CR>0.7,AVE>0.5),表明变量的收敛效度良好。经计算(表3),各个潜变量的AVE 值的平方根都大于它与相关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的各潜变量之间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46],适合进一步使用结构模型进行分析。

表3 量表潜变量相关系数与AVE 值比较
3.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拟合指标如下:CMIN 值为562.651,DF 值为181,CMIN/DF=3.109。CFI 值为0.976,TLI值为0.972,IFI 值为0.976,RMSEA 值为0.054,均达到适配标准。结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且与测量模型是等值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研学旅行涉入对满意度,满意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研学旅行涉入对培育效果,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分别是0.661、0.270 与0.575。假设H1、H2、H3 得到支持。假设检验结果说明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情感投入越多,越能获得满意体验,这种满意体验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并且,青少年对研学活动的情感投入对培育效果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正向激发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兴趣、强化青少年与研学旅行的情感联结对达成研学旅行的教育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表4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二)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strap 方法检验满意度在研学旅行涉入与培育效果之间的中介效应。使用Amos23.0软件实施 boostrap 程序,设定样本为5000,置信水平95%,得出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点估计值及标准误差,如表5 所示。间接效应为0.191(Z 值为0.191/0.041=4.659),直接效应为0.617(Z值为0.617/0.059=10.458),总效应为0.808(Z 值为0.808/0.050=16.160),Z 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96,且Bias-corrected 与percentile 两种检验方法估计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的标准化估计下限值与上限值均不包含0,表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与总效应都显著。因此,满意度在研学旅行涉入与培育效果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 得到支持。检验结果说明,研学旅行涉入对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部分通过满意度起作用。研学旅行涉入通过中介变量满意度对培育效果产生影响,意味着给予青少年满意的研学旅行体验对达成研学旅行的教育目标大有裨益。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三)调节效应检验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为连续变量,适合采用SPSS 统计软件的process 程序检验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在研学旅行涉入对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中不起调节作用,假设H5a 未得到支持。这与该影响路径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产生联系有关。假设H5b 与H5c 得到了支持,P 值分别在0.01 与0.05 水平显著,即调节效应存在。其中,H5b 检验结果表明前置认知在满意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关系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系数为-0.069,表明研学前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认知、认同弱化了满意度对培育效果的正向影响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认同感的个体越不会因为对研学旅行的满意程度而影响培育效果;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不多的个体在研学旅行中也较难感受到价值观的隐性教育,这种影响作用自然也会减弱。H5c 检验结果表明前置认知在研学旅行涉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关系路径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系数为0.038。换言之,研学旅行前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认知、认同越深,则研学旅行涉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影响作用越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成中,青少年主体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强化对价值观的已有理解并进一步增强认同感[47]。前置认知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也体现了意识自觉对发展抽象化价值观的重要性[48],个体对价值观认同的意识自觉越高,越能在实践中与研学旅行的德育引导形成正向合力,强化培育效果。与此相应,认识越深,认同感越强,越不会因研学旅行体验满意度不足而影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满意度对培育效果的路径作用相对弱化。

表6 前置认知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2.结构模型跨群组稳定性检验
以年级和性别检验结构模型的跨群组稳定性。年级变量编码“1”为初中,“2”为高中;性别变量编码“1”为男生,“2”为女生。年级检验结果如表7、8 所示,模型适配性数据符合评判标准,跨群组不变性的P 值大于0.05,表明结构模型具有性别跨群组稳定性。性别检验结果与年级类似,各模型拟合指标良好(CMIN/DF 值在2.436—2.528,CFI 值均为0.966,TLI 值在0.960—0.963,IFI 值均为0.966,RMSEA 值均小于0.08);跨群组不变性P 值均大于0.05,表明男生组与女生组的跨组结构模型稳定。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构建的结构关系模型具有跨群组稳定性。

表7 多群组分析适配表(年级)

表8 跨群组不变性检验(年级)

(续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研学旅行涉入—满意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作用机制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研学旅行涉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有效预测变量。研学旅行涉入正向影响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和研学旅行满意度。满意度在研学旅行涉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青少年对参与研学旅行的情感投入越多,对研学旅行的满意度越高,越有利于通过研学旅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结论实证检验了情感因素在德育中的作用,也揭示了研学旅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内在机制。本研究从涉入理论视角为研学旅行的德育功能发挥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据此,研学旅行组织者应充分考虑情感培育的重要性。
第二,研学旅行满意度正向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研究假设得到支持,表明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满意度越高,培育效果越好。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成立进一步说明研学旅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学旅行组织者应注重研学旅行的过程管理,提高青少年参与研学旅行的满意度。
第三,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显著调节着满意度—培育效果以及研学旅行涉入—培育效果的路径作用,体现了个体认知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也进一步揭示了研学旅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理,培育效果的好坏不仅在于研学实践场域中,也在于研学实践场域外,二者互相配合能有效提升培育效果。此外,年级与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本研究的结构关系模型具有跨群组稳定性,意味着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据此结论提出的管理建议适用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群体。
(二)建议
关注青少年的研学旅行涉入度。研学旅行涉入直接作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研学旅行组织者可通过下列途径强化青少年研学旅行涉入度:一是做好研学旅行的动员工作,从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达层面激发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参与兴趣;二是做好研学旅行活动设计,充分考量青少年兴趣与教育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青少年仅将研学旅行视为强制性教学行为;三是在适当的范围内给青少年合理的研学旅行线路选择权,强化其情感投入;四是提供参与研学旅行后的情感反馈或分享渠道,提高青少年对研学旅行的情感联结。
重视青少年参加研学旅行的满意度。满意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具有积极影响,也起着中介作用。研学旅行组织者应采取措施关注和提升青少年参加研学旅行的满意度。一是树立游、学结合理念,避免将研学旅行视作纯粹的教学行为或游玩行为,忽略了青少年的想法与需求,要引导青少年从研学旅行中意识到宏观的社会变迁与进步[49]。二是学校与研学旅行机构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学生对研学旅行的满意度评价,在合理范围内完善研学旅行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三是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强化情感服务体验,做好价值观隐性教育。
强化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置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多方努力,而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本身是我国治理体系的优势[50]。一是要继续做好学校、家庭、社会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中的教育引导作用,深化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以使其在研学旅行实践中能够充分感受到价值观的隐性教育并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二是要加强研学旅行的行前知识教育,让青少年更为充分地认识到研学旅行的价值观教育目标。通过行前教育唤起或补足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置认知,进而提升培育效果。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研学旅行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促进作用并非朝夕之功,而是通过研学旅行这一途径将能体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实践成果展示给青少年群体,激发青少年的情感认同,转化为成具体的行为习惯。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空间与社会氛围。要从宏观的顶层设计到中观的制度建设、再到微观的日常生活,全方位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合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为研学旅行德育目标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