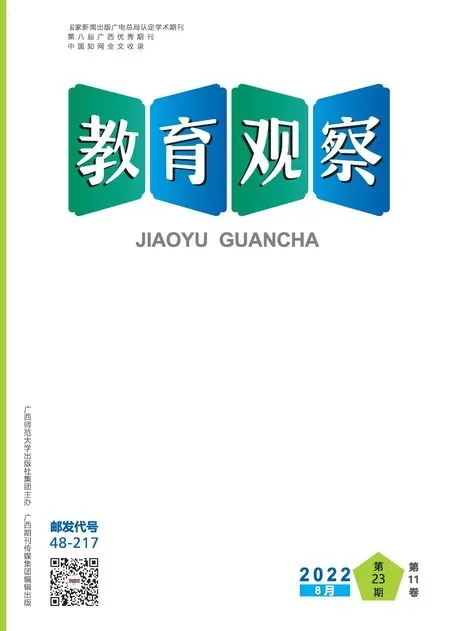高中生适应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赖彩华
(柳州高级中学,广西柳州,545006)
适应是指个体能灵活、适当地应对自身面临的各种日常生活压力,个人需要得到满足并承担社会责任,在与外界互动时行为和情绪表现积极,与其能力、年龄相当,符合所处文化群体的期望和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1]良好的适应意味着个体社会化顺利,有安全感和自信心,能够悦纳自我,保持内心和谐与情绪稳定,并富有创造力。[2]适应不良行为常被视为问题行为,主要有内向型情绪问题和外向型行为问题两种表现形式。[3]适应不良的青少年容易出现抑郁、羞怯、低自尊、网络成瘾和攻击性强等问题。[1-5]总之,适应良好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适应不良则容易出现各种情绪困扰和行为偏差。
生命意义感指个人在目标和动机等意义寻求因素指引下,以认知理解和价值观为中介,在实践活动中体验到的目标实现感、人格统合感和价值感、效能感的总和。[6]已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高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和自尊水平更高,自我效能感也更强,在学校中更可能获得良好的学习成绩。[7-9]相反,低生命意义感的青少年则容易出现自杀、孤独、焦虑、抑郁和药物成瘾等心理健康问题。[10-13]
适应的状态容易识别,属于社会存在的一种。生命意义感则比较内隐,属于意识的范畴。基于两者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密切关系,每当出现校园心理危机事件时,人们常倾向于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虽然关于适应与心理健康或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只从某一个角度很难看清心理健康问题的全貌。基于适应与生命意义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有诸多相似之处,本研究认为适应与生命意义感二者间可能存在某些关系,其内在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然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拥有意义对烦心事通过压力知觉影响个体心理适应的过程具有调节作用。[14]这一观点并没有反映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的主张。对此,本研究尝试从个体的适应切入,即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解释生命意义感这一问题,探讨高中生的家庭适应与学校适应的主要维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为学校更有效地开展生命教育、提高高中生的生命质量提供数据支撑。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广西市级和县级普通高中抽取4所学校共78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2份,有效回收率92.6%。其中,男生281人,女生441人;高一405人,高二159人,高三158人。
(二)工具
1.青少年适应量表
该量表包括家庭适应和学校适应两个分量表,家庭适应分量表包含凝聚力、基本功能的满足、问题的有效解决三个维度,学校适应分量表包含学习能力、学习动机、人际互动三个维度。该量表共39题,采用4点计分法计分(1为“不曾这样”,4为“总是这样”)。其中,第3、7、9、10、11、13、15、16、18、20、21、22、29、31、33、39题属于反向计分题。经分数转换后,得分越高,表示适应越好。本研究中,青少年适应量表的Cronbach’s α是0.87,两个分量表以及6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在0.71—0.82,表明信度良好。KMO值为0.878>0.6,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生命意义感量表
该量表有求意义的意志、生命态度与生命自主、苦难与死亡的接纳、存在的空虚四个维度。该量表共33题,采用5点计分法计分(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其中,第1、4、7、10、20、25题为反向计分题。经过转换后,得分越高,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生命意义感量表的Cronbach’s α是0.91,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在0.70—0.86,说明信度良好。KMO值为0.862>0.6,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三)施测程序和统计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带领研究人员进班,利用自习课时间进行施测。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生命意义感与适应状况的描述性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高中生的适应(2.730±0.341)和家庭适应(2.925±0.453)处于中上水平,学校适应(2.523±0.373)相对前两者稍低,处于中等水平。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3.931±0.494)处于中上水平。由表1可知,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的平均得分在2.5分以下,生命意义感四个维度的平均得分都处于中上水平。其中,基本功能的满足的得分最高,问题的有效解决次之,凝聚力、人际互动再次之;求意义的意志得分最高,苦难与死亡的接纳次之,生活态度与生命自主、存在的空虚再次之。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高中生的学校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家庭适应水平(t=-29.17,p<0.001)。

表1 高中生适应与生命意义感描述性统计情况
(二)生命意义感与适应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高中生适应状况及各维度与生命意义感及各维度呈现显著的中度正相关;学校适应和生活态度与生命自主、存在的空虚两个维度呈显著的中度正相关;人际互动维度和生命意义感及其生活态度与生命自主、存在的空虚两个维度呈显著的中度正相关;家庭适应与存在的空虚维度呈显著的中度正相关;其他维度之间呈显著的低度正相关。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高中生适应与生命意义感相关分析
(三)适应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采用逐步进入法,以青少年适应的六个维度为自变量,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在凝聚力、基本功能的满足、问题的有效解决、学习能力、学习动机、人际互动六个预测变量中,能进入回归方程且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变量共有五个,如表3所示。
这五个预测变量对生命意义感的决定系数R2为0.298,可联合解释29.8%的生命意义感变异量,即五个变量能联合预测生命意义感的29.8%。就个别变量的解释能力来看,人际互动的预测效果最佳(解释量为16.9%),接下来依次是凝聚力(解释量为24.5%)、学习动机(解释量为27.8%)、基本功能的满足(解释量为29.0%)和学习能力(解释量为29.8%)。最终得出的标准化回归方程为:生命意义感=0.196×人际互动+0.169×凝聚力+0.185×学习动机+0.140×基本功能的满足+0.094×学习能力。

表3 适应各维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四)学校适应在家庭适应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适应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家庭适应为自变量、学校适应为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将对应的分值取均值并中心化后,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6],参照更具有优势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17],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检验学校适应是否中介了家庭适应对生命意义感的效应。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学校适应中介模型
检验结果表明,家庭适应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受学校适应的中介影响,95%置信区间为[0.12,0.20],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大小为0.16。此外,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学校适应之后,家庭适应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直接影响,95%置信区间为[0.24,0.39],包含0,直接效应值为0.32。因此,家庭适应对生命意义感有直接效应,也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33.5%。
三、讨论与建议
(一)高中生适应发展不平衡,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
结果显示,高中生适应状况总体处于中上水平,学校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家庭适应水平。根据家庭适应和学校适应的界定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判定[18],高中生能从家庭中获得基本的经济与物质支持,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等匮乏性需要在家庭情境中可以得到较好的满足,家庭是他们满足匮乏型需要的主要途径。本研究发现,除了人际互动维度得分较高,学习动机维度和学习能力维度的得分都明显偏低。此结果意味着在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滋养内在动机和自我决定行为的学校环境因素中[19],高中生自主需要和能力需要的满足状况并不理想,高中生的成长型需要满足程度较低。高中生在学习自主和学习胜任感方面的不足可能是影响高中生学校适应的主要原因。对此,学校应采取措施重点加强高中生学习能力培养,提升其对高中阶段学习的适应性,为他们提供自主性支持。例如,教师可以适当对高中生放宽管理,让他们学会自己作决定,自己承担责任,选择作业的形式、合作的伙伴、获取学习资源的方式、如何呈现学习结果等,使他们体验到自主性和力量感,满足自主需要。
结果显示,高中生生命意义感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求意义的意志维度得分最高,说明高中生在行动目的性和动机方面表现最好,对生命的自主性、控制感较低,对苦难及死亡的理解较少。这可能与高中生考试、升学目标相对明确有关。本研究中,生命意义感量表求意义的意志、生活态度与生命自主、苦难与死亡的接纳三个维度可以较好地匹配马特拉和斯泰格著名的动机、价值与理解三因素生命意义感模型[20],存在的空虚维度则可以反映了生命意义感发展的结果。因此,本研究调查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基本情况。
(二)提高适应水平,增进高中生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适应状况、家庭适应和学校适应与生命意义感都呈显著的中度正相关,且适应各维度可以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从适应的具体维度来看,人际互动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效果最好。积极的人际互动意味着良好的社会支持与有效的社会连接,是提升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
此外,凝聚力、学习动机、基本功能的满足和学习能力4个预测变量可以反映出高中生相关需求的满足情况及学校、家庭方面的适应状况,是预测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指标。这与李婷婷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1-23]
家庭适应中,问题的有效解决反映个体与父母存在价值观冲突及解决情况。在本研究中,该维度被排除在回归模型之外。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高中生处于青春期后期,家庭主要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和发挥安全基地的作用[24],他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向父母要求自主和独立转向寻求家庭之外的同伴接纳和认可,以及现实任务的控制感。二是青春期早期比较常见的亲子冲突在高中阶段可能相对缓和,亲子双方都能更平和、理性地看待彼此一些小的偏好差异,不至于爆发强烈的冲突,导致挫败感。
总之,学校要积极引导家长关心高中生的生活和学习,满足高中生的基本需求,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爱意。在高中生探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学校应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校园环境,努力设计丰富的学习和课外活动,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提升社会技能和社交技巧,拓展人际空间,实现目标,感受成功的喜悦。
(三)发挥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成长型价值观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除有直接影响之外,家庭适应对生命意义感还通过学校适应的部分中介作用发挥间接影响。结合上文的研究结果,学校可以采取举措重点提升学生的学校适应水平,进而提升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比如,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可以引导高中生树立内部目标,让他们看到即使在面临升学压力的高中阶段,他们也能够决定自己的行动和行为。在施瓦茨的成长型价值观指引下[25],高中生可以把当前的学习任务理解成创造与发挥个人潜能,是帮助自己迈向自我超越,实现深刻影响人类未来命运的崇高事业的阶梯。正如《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6]总而言之,教师应鼓励高中生向成长型价值的成功践行者学习,成为自主行动者,开创自己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