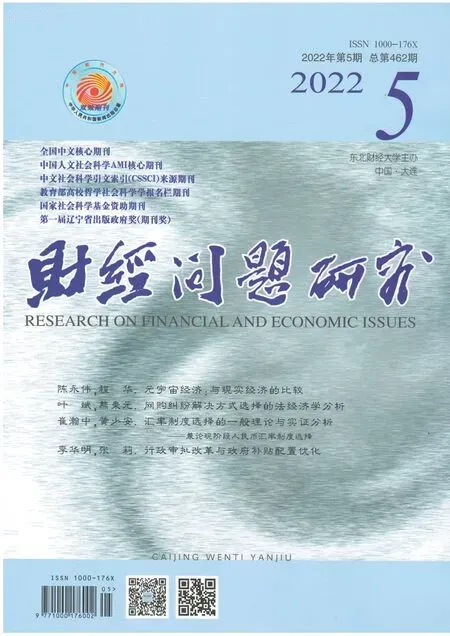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法经济学分析
叶斌 熊秉元



摘 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化解网购纠纷的制度路径,但是,要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流作用,前提是当事人会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本文假定网购纠纷当事人对解决方式的选择是成本收益机制,延伸法经济学的LPG条件,对网购纠纷当事人如何选择解决方式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理论分析通过论证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连接理论因素和观测对象,提出可证伪假设。实证研究则以网购较活跃的杭州西湖区10个街道为样本,采用二值逻辑回归的混合效应模型,检验了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当事人的职业、学历和收入等有关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解纷结果估计的属性和纠纷标的额对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影响机制符合成本收益机制。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经验规律与理论假设完全一致。
关键词:网购纠纷;纠纷解决方式;成本收益机制;LPG条件;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713.36;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2)05-0017-10
一、引 言
截至2021年2月,中国网购的用户规模达7.82亿人,2020年交易规模达11.76万亿元[1]。蓬勃发展的网购市场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却是纠纷增长的重要来源。[ 网购纠纷,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2018年9月3日通过)所列出的十一种纠纷,本文的网购纠纷主要指其中的前三种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
收稿日期:2021-11-09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经济学视角下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研究”(20NDQN308YB);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司法去地方化研究”(20CJL005)
作者简介:叶 斌(1985-),男,浙江杭州人,讲师,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法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E-mail:11501007@zju.edu.cn
熊秉元(1957-),男,台湾南投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法律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hsiung@zju.edu.cn]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的统计,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网购类案件的收案量在所有案件类别中排名第二。另据杭州互联网法院[3]的统计,在2018年,网购合同纠纷和网购产品责任纠纷成为收案案由中的主要增长点。 “电诉宝”的数据也显示,2016年以来,网购纠纷的投诉数量持续高增长,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商法》正式实施的2019年,投诉量仍然居高不下[4]。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多元化解决方式是化解网购纠纷的制度路径。这是因为,司法审判在短期内难以增加供给,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却容易增加供给[5]。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目标是促成当事人的互利和解,其形式包括协商和解、行政督察、和解会议、行业调解、第三方专家评估和律师合作等[6]。截至2021年6月,国内网购较活跃的城市已经建立了诸如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等网购纠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现行网购纠纷的在线纠纷解决方式(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ODR)中,典型的如广州互联网法院的调解咨询服务,杭州市委政法委的“一码解纠纷”线上平台。]
根据互联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购纠纷的诉讼原告多为普通消费者,因为,要实现网购纠纷的非诉解决,应掌握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规律。尽管现有研究在多种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上论述颇丰,却对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机制选择问题付之阙如。纠纷及其解决方式的特征能够改变解纷行为的决策机理,使得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布发生结构性变化。与一般民事纠纷相比,网购纠纷至少有三点特征:首先,纠纷发生在社会关系原子化的陌生人之间。其次,纠纷标的一般只涉及财产权。最后,网购交易一般是单回合博弈,机会主义行为容易成为占优策略。因此,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一般民事纠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探索网购纠纷当事人如何选择解决方式,具有理论补充意义。
在本文结构上,首先,笔者回顾纠纷解决方式的事实描述和理论解释框架,评述现有理论解释与网购纠纷的契合性。其次,把纠纷当事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基于法经济学的LPG条件,理论分析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成本收益机制,并通过成本收益机制理论因素的可观测对象,提出可证伪假设。最后,基于问卷调查和统计推断,实证检验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归纳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经验规律,以验证理论假设。
二、文献回顾
纠纷解决方式研究的文献回顾分为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事实描述框架和理论解释框架两个方面。两者的区别是,事实描述框架通过纠纷发生和纠纷解决的概念框架,呈现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理论解释框架则通过当事人行为决策机理的分析,探寻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根据既往文献评述,探讨适合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事实描述框架和理论解释框架。
(一)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事实描述框架
1. 民事纠纷的发生
纠纷发生阶段的概念化表述是描述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理論基础。Felstiner等[7]认为,民事纠纷的发生分为三个阶段,需经过当事人对可感知伤害经历(Perceived Injurious Experience)的“定义”“ 归咎”“ 索赔”(Naming-Blaming-Claiming)。经过“定义”,主观感知的伤害经历通过归纳共性,进入客观化的“可感知伤害经历”阶段;经过“归咎”,伤害经历可确认潜在侵害人,进入“抱怨”(Grievance)阶段;潜在受害人向抱怨对象发起“索赔”,如果索赔遭到拒绝,则进入“纠纷”阶段。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因为纠纷发生是纠纷解决的逻辑前提或者特殊形式,而潜在纠纷在可感知伤害经历或抱怨阶段几乎必然受到当事人属性的影响。如同样是残次商品的网购消费者,高学历当事人认为是侵权,应当积极索赔;而低学历当事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自认倒霉,潜在纠纷在抱怨阶段就以无行动的形式解决了。于是,高学历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方式会较多分布在索赔及以后阶段。因而当事人属性与纠纷解决方式分布存在相关性。
2. 纠纷金字塔和纠纷树
基于纠纷发生的三阶段论,Miller和Sarat[8]采用五层纠纷金字塔描述潜在纠纷从发生到解决的五个阶段,底层是抱怨,[纠纷金字塔也可在抱怨层之下加上可感知伤害经历层和不可感知伤害经历层。]依次向上的层级是索赔、纠纷、咨询律师和诉讼。如图1(a)所示,纠纷金字塔的上层是下层的子集,每一层的宽度表示进展到该阶段的纠纷相对于抱怨的数量比例。通过纠纷在每个阶段的比例,纠纷金字塔呈现出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布。但是,这种经典纠纷金字塔假设从抱怨到诉讼是单向的串行路径,忽略了非诉机制作为纠纷解决并行路径的存在[9]。事实上,多数民事纠纷或被容忍,或直接由非诉机制解决,极少单向地经历每个阶段直到诉讼[10-11]。因此,Morrill和Rudes[12]采用并行金字塔,使得可感知侵权可以同时直接通向四种解决方式,如图1(b)所示,诉讼(法律行动)、准法律行动(Quasi-Legal Action,如行业组织投诉)、法外行动(Extralegal Action,如直接对抗的媒体呼吁)和无行动(如忍耐)。
由于纠纷金字塔无法描述纠纷解决方式的后验结果和演化动态,Albiston等[13]提出“纠纷树”的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描述框架。纠纷树通过树枝和花果的隐喻表现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果和演变。比如,健康的树枝意味着实现正义,如诉求表达畅通且归责明确;枯萎的树枝意味着没有正义也没有救济;只开花不结果的树枝意味着归责明确却没有救济,如调解后执行不到位;只结果不开花的树枝意味着有补偿却不公开承担责任,如私下协商和解,等等。
除了纠纷金字塔和纠纷树外,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描述框架还有以下三类:一是棚濑孝雄[14]根据纠纷解决是否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合意性”“ 决定性”;根据纠纷解决的内容是否受到规范确定,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规范性”“状况性”。二是Black[15]将纠纷解决方式概括为自我帮助、逃避、协商、通过第三方解决和忍让五种。三是强世功[16]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三种。
(二)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理论解释框架
当事人的解纷行为决策是形成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原因,对于解纷行为决策机制存在多角度的理论解释,主流的是社会结构理论解释和成本收益理论解释两类。
1. 社会结构理论解释
社会结构理论解释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法学界,至今方兴未艾。按照解释角度及其研究对象划分,可归纳为以下六类:一是从社会结构塑造不同权利认知的角度,解释忍耐或不行动[17-19]。二是从社会制度变革重新界定权利,从权利主体无需积极维权的角度,解释诉讼选择的突变[20-21]。三是从纠纷解决方式的后验结果角度,解释诉讼选择预期的变化[22-23]。四是从律师重塑當事人权利观念的角度,解释诉讼选择[24-26]。五是从社交环境塑造当事人观念的角度,解释和解或诉讼的选择[27-28]。六是从人际关系特征的角度,解释私力救济或诉讼的选择[29-30]。社会结构理论解释一般认为,不同社会情境的互动模式能够塑造不同的权利观念,因此,社会情境决定解纷行动决策,而且,这一决定机制具有全面而恒久的性质,不易被政治经济等其他条件所改变。具体而言,当事人如何进行解纷行动决策可由社会学属性解释,包括职业、教育、家庭和社会网络等。以中国农村社会为例,民事纠纷当事人宁可上访政府部门而不诉诸司法就是普遍的观念和解纷行动[31]。
社会结构理论解释被国内外研究广泛应用。如程金华[32]发现,收入、学历和单位等当事人属性可以解释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意愿,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的群体倾向忍耐或避免司法解决。陆益龙和杨敏[33]发现,收入、学历和年龄等当事人属性可以解释农村纠纷的诉讼解决。 Gallagher和Yang [34]发现,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和学历可以解释劳动纠纷的司法解决。刘青和石任昊[35]发现,当事人的学历、收入和所在城市等属性可以解释民事纠纷的司法解决。
2. 成本收益理论解释
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另一主流解释是成本收益理论解释,社会结构理论解释与成本收益理论解释的侧重点不同。根据Hoffmann[36]对法律行动诱因的分析,社会结构理论解释侧重当事人的法律意愿,在认同法律的前提下再讨论法律能力;成本收益理论解释则假定法律意愿价值中立,着重讨论法律能力的成本收益均衡。换言之,成本收益理论解释认为,当事人只在工具理性层面权衡利弊。
Landes [37]-Posner [38]-Gould[39]条件(三位法经济学名宿的理论贡献,简称“LPG条件”)是成本收益理论解释的典型,该理论将诉讼的决策机制表述为预期成本收益的权衡,即当原告预期的诉讼收益高于被告预期的和解成本时,发生诉讼,否则达成和解。
以LPG条件为代表的诉讼理论没有涉及影响成本收益的具体因素,其他研究对此做了补充。比如,Sandefur[40]认为,法律资源能够影响索赔或诉讼的成本收益,因此,与法律资源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索赔或诉讼数量成正比关系。Genn[41]对于诉讼数量与经济地位成正比的现象,也提出法律资源能够影响诉讼成本的解释。Michelson[42]认为,由于政治关联能够影响法律行动的成本收益,所以,中国农村的干部和党员更多以法律行动解决纠纷。Sandefur[43]认为,诉讼决策应包括不能由货币度量却能间接影响成本收益的因素,比如社会网络。李俊[44]认为,纠纷标的额是否涉及生存利益是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或者和解忍让的原因。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三)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事实描述和理论解释
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机制选择,取决于网购纠纷及其现行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在纠纷特征上,网购纠纷标的额是单一维度的财产权,双方当事人是原子化的陌生人,解纷决策既无需在价值理性上考虑法律认同,[成本收益解释可能无法刻画人身权利的复杂内涵,从而简化诉讼决策机理。比如,Morgan[45]发现,当事人是否起诉性骚扰不仅考虑成本收益,还会考虑到诉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Quinn[46]发现,当事人为了体现对公司文化的适应性,而默许工作场所的性骚扰。Major和Kaiser[19]发现,当事人因为避免报复和负面声誉,而不对种族歧视采取法律行动。]又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只需在工具理性上考虑解纷成本和收益。[类似于中国农村的经济纠纷,受访者选择什么也不做的原因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搭不起时间和搭不起钱。 这些原因与法律认同无关,只与实用主义或者工具理性意义上的解纷信息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47]有关。]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网购在中国兴起不过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商法》颁行不到3年,无论正式制度层面还是规范习俗层面尚未形成纠纷解决方式的主流,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是潜在选项,由当事人自主决策。因此,可以假定权衡预期成本收益是当事人选择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机制。
如果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是成本收益机制,并且网购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成本差,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当事人应根据成本大小逐级权衡。网购纠纷解决方式从忍耐、和解、调解、投诉到诉讼,程序越来越复杂,成本也依次增加,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成本差。因此,网购纠纷解决方式从忍耐到诉讼的分布,会呈现越来越少的金字塔形态,经典纠纷金字塔是描述网购纠纷解决方式分布的合适形式。纠纷解决方式的事实描述框架由当事人的选择机制决定。
三、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理论分析
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成本收益解释,可藉由LPG条件的延伸理论刻画。
(一)纠纷解决方式决策的成本收益解释
LPG条件将诉讼决策表述为,双方当事人根据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对于诉讼与和解的利弊进行权衡,如式(1)所示:
PpJ-Clp+Csp>PdJ+Cld-Csd(1)
其中,Pp是原告估计自己获胜的条件概率;Pd是被告估计原告获胜的条件概率;J是原告胜诉时,被告对原告的赔偿,也可称为案件标的额;Clp和Cld是原告和被告的诉讼费用;Csp和Csd是原告和被告的和解费用。式(1)的含义是,当原告所估计的诉讼收益高于被告所估计的最高和解赔偿时,发生诉讼,否则达成和解。重写式(1)为式(2):
Pp-Pd>K(2)
其中,K≡(C-S)/J,C=Clp+Cld,S=Csp+Csd。
LPG条件是诉讼与和解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决策理论,是否可以延伸解释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据Spier[48]的论述,LPG条件的逻辑前提是存在诉讼与和解的成本差距,也即式(2)中的C>S。如果在忍耐、调解和投诉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同样存在成本差距,那么,LPG条件的逻辑就可以延伸解释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决策。网购纠纷解决方式可以归纳为诉讼、投诉、调解、和解、报复、忍耐和替换七种[49-50]。[本文的调解是指第三方机构,如网购平台、媒体居中介入的和解谈判,不包括诉讼和投诉程序中的调解。其中,假定網购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是诉讼,不存在“涉法涉诉信访”。]七种纠纷解决方式中,报复的实施形式和成本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其他6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比较稳定,假设六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成本差距。
多种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LPG条件延伸理论如下:令双方当事人从纠纷解决方式的可行集R中选择一种解决方式,R=(r1,…,ri)。对于任意的ri,rj∈R,如果Cri>C(rj),则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方式是ri的条件如式(3)所示:
PpJ-Cpri+Cp(rj)>PdJ+Cdri-Cd(rj)(3)
式(3)左边是受害人[为行文简洁,将发起纠纷解决方式的潜在受害人称为受害人,将接受纠纷解决方式的潜在侵害人称为侵害人。]在ri的预期收益,等于受害人在ri的解纷预期收益减去受害人选择ri的机会成本,这也是受害人在rj的最低要价。式(3)右边是侵害人在ri的预期成本,等于侵害人预期受害人在ri的解纷收益减去侵害人选择rj的机会成本,也是侵害人在rj的最高出价。所以,式(3)有两层含义:其一,当受害人在ri的预期收益高于侵害人估计rj的最高成本时,受害人就选择ri。其二,当受害人的rj最低要价高于侵害人在ri的预期成本时,侵害人也选择ri,所以,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ri。
当然,如果受害人在ri的预期收益低于侵害人在rj的最高成本,或者说,受害人的rj最低要价低于侵害人在ri的预期成本,那么双方的选择就是大事化小,一致选择较低成本的rj。rj的条件是:PpJ-Cpri+Cprj Pp-Pd>(C-S)/J(4) 其中,C=Cpri+Cdri,S=Cp(rj)+Cdrj。定义式(4)为LPG条件延伸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对式(4)进行静态分析,可推出三则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规律:其一,纠纷标的额J越大,式(4)越可能成立,因此,标的额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产生正向影响。标的额越低,则越可能选择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标的额越高,则越可能选择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二,C-S越小,式(4)越可能成立,因此,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差距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产生负向影响。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差距越小,越可能选择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差距越大,则越可能选择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三,Pp-Pd越大,式(4)更可能成立,因此,双方当事人对于解纷结果的估计差距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产生正向影响。如果受害人对解纷结果的估计越乐观(Pp越大),或者,侵害人对解纷结果的估计越乐观(Pd越小),只要一方对解纷结果的估计越乐观,双方越可能选择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反之,只要一方对解纷结果越悲观,则双方越可能选择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假设六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序列如下:诉讼>投诉>调解>和解>替换>忍耐。将三则选择规律作为大前提,将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序列作为小前提,可运用选择规律推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以诉讼和忍耐为例,诉讼作为最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选择诉讼的必要条件是足够高的标的额、与替代解决方式之间足够小的成本差或当事人足够乐观的诉讼结果估计;忍耐作为最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选择忍耐的必要条件是足够低的标的额、与替代解决方式之间足够大的成本差或当事人足够悲观的解决结果估计。 (二)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理论假设 LPG条件延伸理论通过三个因素(标的额、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建构了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成本收益解释。然而,要形成可证伪的理论假设,需要连接理论因素与可观测对象。理论因素中,标的额的观测对象明确,可直接将式(4)的第一则选择规律作为理论假设1: 假设1:纠纷标的额越低,越可能选择较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纠纷标的额越高,越可能选择较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 连接理论因素与可观测对象,需明确理论因素的内涵。纠纷解决方式成本的内涵是,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具有稳定性并且任意两者间存在显著差距。比如,诉讼的成本一般高于其他方式。当事人的职业、学历和收入等属性,可能与特定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相关。比如,法律职业或电商职业人士通过专业技能、社会网络和机构支持等方面的优势,降低诉讼、投诉和调解等方式的实施成本。根据式(4)的第二则选择规律,如果诉讼、投诉、调解和和解的成本差距下降,法律或电商职业人士就会倾向选择较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同理,高学历或高收入的当事人通过信息获取和社会网络甚至制度结构等方面的优势,降低诉讼和投诉等高成本纠纷解决方式的实施成本,也会倾向选择较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只要当事人在职业、学历和收入等属性与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差相关,这些当事人属性与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就会呈现规律性。 解纷结果估计的内涵是,不同的先验信念,导致当事人对特定解纷结果有不同的估计误差。当事人的职业、学历和收入等属性,通过法律文本、司法程序和后验结果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性,塑造不同的先验信念,从而与解纷结果的估计误差相关。根据Priest和Klein[51]的理论,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解纷结果的估计误差减小,当事人会倾向选择较低成本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比如,法律职业的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估计误差较低,就会倾向选择较低成本的非诉讼解纷方式。因为,如果法律职业的当事人估计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收益相当,为了降低解纷成本会把预期信息传递给对方,双方当事人就能以较低成本解决纠纷。换言之,对纠纷解决方式投入更多成本是因为当事人对解纷结果有错误的乐观信念。因此,只要当事人在职业、学历和收入等属性与解纷结果的估计误差相关,这些当事人属性与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就会呈现规律性。 由于当事人在职业、学历和收入等属性可能同时成为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的观测对象,并且两种理论因素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产生相反的影响效应,所以,通过两种理论因素的观测对象,只能预测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但无法预测影响方向。比如,法律职业的当事人,会因为诉讼相对成本较低而倾向诉讼,也会因为估计诉讼结果较准确而倾向非诉讼解纷方式。同样的,学历较高和收入较高的当事人,会因为纠纷解决方式相对成本的降低而倾向选择较高成本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会因为解纷结果估计准确性的提高而倾向退出较高成本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假定在网购纠纷中,与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相关的当事人属性,包括职业、学历和收入等。[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当事人的职业、收入、教育和地区等属性,可以影响解纷行动。Nielsen等[52]发现,特定职业属性的原告不太可能选择和解,如管理层、专家型、资深和任职工会组织。Morrill等[6]发现,高中生很少采取法律行动维权。Eisenberg 和 Hill[53]发现,低工资原告的仲裁结果较差,也不愿意选择仲裁。刘青和石任昊[35]发现,当事人的学历、收入和所在城市等属性,可以解释民事纠纷的司法解决。]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的当事人属性,能够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当事人的相关属性实际产生哪个方向的选择倾向,取决于糾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影响效应的大小。 四、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实证分析 对网购纠纷当事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系数估计和统计推断,实证检验理论假设。 (一)数据来源 问卷调查以网购纠纷当事人为调查单位,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收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城市、网购频次、网购纠纷类别、纠纷标的额和纠纷解决方式等。问卷调查的受访当事人生活或工作所在地是网购较活跃的杭州市西湖区,调查的抽样单位为西湖区的10个街道,设计抽样率大概为常住人口的2‰,本次调查共发放2 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1 982份,问卷有效率为82.58%。问卷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达到0.972,调查结果的信度较高。值得说明的是,调查重点是有关理论假设的样本,比如职业因素,调查员特地走访司法机关和电商企业。所以,样本中法律和电商职业当事人所占比重较高。 (二)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布 根据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序列,将除报复以外的网购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四类:忍耐与替换为潜在纠纷解决方式,和解与调解为协商解决方式,投诉为行政解决方式,诉讼为司法解决方式。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序列为:司法方式>行政方式>协商方式>潜在纠纷方式。在遭遇可感知伤害的1 982位网购纠纷当事人中,有162位选择司法机制,占8.17%;有280位选择行政机制,占14.13%;有496位选择协商机制,占25.03%,与商家和解和第三方调解的当事人分别有332位和164位;有844位未向潜在侵害人索赔,以忍耐或替换商家等方式平息潜在纠纷,占42.58%;另有200位选择各种形式自行报复,占10.09%。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根据上述分析,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呈现出随着纠纷解决方式成本的提高而频次下降的趋势,纠纷解决方式分布所呈现的宏观事实与成本收益的微观解释相一致,分布型态与经典纠纷金字塔相当符合。样本分布还呈现出两点事实:其一,网购纠纷的主流救济途径是私力救济。将诉讼和投诉视为公力救济,样本中的公力救济占比达到22.30%。如果将所有没有官方部门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视为私力救济,则私力救济占比为77.70%。其二,有超过一半的网购潜在纠纷未发生。网购可感知伤害中有接近一半(42.58%)的未索赔,索赔的当事人有29.17%达成和解,也就是59.33%的潜在纠纷没有进展到对抗性的纠纷。 (三)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 采用二值逻辑回归的混合效应模型进行系数估计和统计推断,[因为七种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任意两种,其选择依赖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例如,选择和解或诉讼,受到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所以,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不满足无关方案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假设,不能采用多项逻辑回归等多值选择模型。另据Hausman检验,以纠纷类别为数据截面,二值逻辑回归混合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二值逻辑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并无系统差异,因此,实证检验采用对纠纷类型计算聚类稳健标准误的二值逻辑回归混合效应模型。]考察各种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以5%显著性水平为标准,表1给出了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标的额对于忍耐、替换、投诉、诉讼和报复都有显著影响;学历对于调解和投诉有显著影响;收入对于忍耐、和解和调解有显著影响;电商职业对于调解有显著影响;法律职业对于调节和诉讼有显著影响;城市对报复有显著影响;网购次数对替换有显著影响。 表1中的系数是几率比,表示解释变量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几率的变化倍数。根据解释变量的含义和系数值,各解释变量与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呈现出以下六条经验规律:其一,纠纷标的额越高,当事人选择忍耐和替换越少,选择投诉、诉讼和报复越多。标的额数值每增加10元,當事人选择忍耐的几率减少2.4%,选择替换的几率减少4.2%,选择投诉的几率增加2.4%,选择诉讼的几率增加2.1%,选择报复的几率增加1.1%。标的额与成本之间的负向相关性与理论假设1的预测基本一致。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其二,当事人从高中生到研究生,随着学历的提升,将更多选择投诉,更少选择调解。当事人的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选择调解的几率增加23.3%,选择投诉的几率增加16.6%。较高学历的当事人更多选择调解和投诉,而较低学历的当事人更少选择调解和投诉。其三,当事人的收入从每月不足3 000—10 000元以上,随着收入增加,将更少选择忍耐和和解,更多选择调解。收入每增加1 000元,选择忍耐的几率减少8.5%,选择和解的几率将减少4.4%,选择调解的几率增加10.4%。较高收入的当事人更多选择调解,更少选择忍耐或和解。其四,电商职业的当事人更多选择调解,法律职业的当事人更多选择调解,却更少选择诉讼。电商职业比非电商职业选择调解的几率增加3.123倍,法律职业比非法律职业选择调解的几率增加3.020倍,选择诉讼的几率减少52.3%。电商职业的当事人更多选择调解,法律职业的当事人更少选择诉讼。其五,家乡所在地是一二线城市的当事人更少选择报复。一二线城市的当事人较其他地区的当事人选择报复的几率减少47.3%。其六,每月网购次数较多的当事人会更多选择替换新的网购平台,网购次数每增加1次,选择替换平台的几率增加2.3%。 第二条—第四条规律显示,学历、收入和相关职业属性都对调解有显著影响,学历对投诉有显著影响,收入对潜在纠纷有显著影响,相关职业对诉讼有显著影响。这三条规律表明,包括特定职业、学历和收入等有关因素相对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的当事人属性,能够普遍影响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假设2的预测基本一致。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律虽然未被理论所预测,却也相当符合直觉。成长于大城市的当事人,更容易求助公力救济渠道,因而毋需诉诸于报复。网购次数较多的当事人掌握了较多的购物信息,更容易通过替换忽略可感知伤害。 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纠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比如,收入、学历和职业等会影响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意愿[32]; 收入、学历和年龄会影响农村纠纷的诉讼行为[33];法律知识和学历会影响劳动纠纷的司法解决行为[34];学历、收入和所在城市会影响一般民事纠纷的司法解决行为[35]。这种影响因素上的一致性,意味着成本收益分析很可能是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一般机制。值得解释的是,标的额是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未见影响其他纠纷,这是因为网购纠纷的诉求往往是有价商品或服务,而其他类型纠纷的诉求难以用市场价格度量,甚至并非是财产权利。 五、结 论 本文的理论分析有三个论点:网购纠纷的标的额与所选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正相关;有关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的当事人属性能够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会产生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到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六条经验规律,其中,当事人的职业、学历和收入等有关纠纷解决方式成本和解纷结果估计的因素以及纠纷标的额能够对网购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制符合成本收益理论。 本文从法经济学的一个视角,即假定网购纠纷当事人是理性经济人,进行网购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法经济学的另一视角,社会福利最大化价值上的规范分析,结论很可能殊途同归。借用Shavell[54]的观点:法律所处理的纠纷,应该是涉及利益较大的纠纷,只有大是大非的纠纷才值得动用珍贵的司法资源。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只有让适度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来处理适度价值的纠纷,才能实现法治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了解纠纷当事人的机制选择,才可能提供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參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8-20].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2/t20210203_71361.htm. [2] 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白皮书[EB/OL].(2019-09-03)[2021-08-20].https://www.bjinternetcourt.gov.cn/cac/zw/1567483035819.html. [3] 杭州互联网法院.电子商务案件审判白皮书(2018年度)[EB/OL].(2019-03-19)[2021-08-20].http://hztl.zjcourt.cn/art/2019/3/19/art_1225222_41380785.html. [4]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19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EB/OL].(2020-03-04)[2021-08-21]. http://www.100ec.cn/zt/2019yhtsbg/. [5] 理查德·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861. [6] MORRILL C, TYSON K,EDELMAN L B,et al.Legal mobilization in schools: the paradox of rights and race among youth[J]. Law & society review, 2010, 44 (3-4): 651-693. [7] FELSTINER W L F, ABEL R A, SARAT A.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and claiming[J].Law & society review,1980, 15(3-4): 631-654. [8] MILLER R E, SARAT A. Grievances,claims, and disputes: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culture[J]. Law & society review, 1980,15(3-4):525-566. [9] MERRY S E.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0] MAYHEW L H. Institutions of representation: civil justice and the public[J].Law & society review,1975,(9): 401-429. [11] DIAMANT N J.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0, 44(4):523-546. [12] MORRILL C,RUDES D S. Conflict resolution in organiz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law & social science, 2010,(6):627-652 [13] ALBISTON C R,EDELMAN L B,MILLIGAN J.The dispute tree and the legal forest[J]. Annual review of law & social science, 2014, 10(1):105-131. [14] 棚濑孝雄.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 [15] BLACK D. Sociological justice revised ed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2. [16] 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75-428. [17] KRITZER H M,VIDAR N,BOGART W A. To confront or not to confront: measuring claiming rates in discrimination grievances[J]. Law & society review, 1991,(25): 875-887. [18] WAKEFIELD S, UGGEN C.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in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claims[J]. Sociological inquiry, 2010,74(1): 128-157. [19] MAJOR B,KAISER C R. Perceiving and claiming discrimination[C]//NIELSEN L B,NELSON R L. Handbook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2005:285-299.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20] ENGEL D M,MUNGER F W.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21] ABREGO L J. Legitimacy,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law: the effects of assembly bill 540 on undocumented students in California[J]. Law & social inquiry, 2008, 33(3):709-734. [22] GALANTER M. 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J]. Law & society review, 1974,9(1):95-160. [23] ALBISTON C.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litigation process: the paradox of losing by winning[J]. Law & society review, 1999, 33 (1): 869-910. [24] SARAT A, FELSTINER W L F. Lawyers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law talk in the divorce lawyers office[J]. The Yale law journal,1989,98(8):1663-1688. [25] MATHER L,MCEWEN C A, MAIMAN R J. Divorce lawyers at work: varieti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practi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 TRAUTNER M N. Tort reform and access to justice: how legal environments shape lawyers case selection[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11, 34(4):523-538. [27] ALBISTONl C R.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social institutions: competing discourses and social change in workplace mobilization of civil rights[J]. Law & society review,2005, 39 (1): 11-50. [28] MARSHALL A M. Idle rights: employees 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policies[J]. Law & society review,2005,39 (1):83-124. [29] EMERSON R M. Responding to roommate troubles: reconsidering informal dyadic control[J]. Law & society review,2008,42(3):483-512. [30] BLACK D. The behavior of law[M]. Somerville: Emerald publishing, 2010:47-48. [31] O'BRIEN K J, LI L.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171. [32] 程金華.中国行政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以公民需求为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 2009(06):144-160. [33] 陆益龙,杨敏.关系网络对乡村纠纷过程的影响——基于CGSS的法社会学研究[J].学海,2010 (03):176-182. [34] GALLAGHER M,YANG Y. Getting schooled: legal mobilization as an educative process[J]. Law & social inquiry, 2017,42(1):163-194. [35] 刘青,石任昊.当代中国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CGSS2005的法社会学分析[J]. 社会发展研究,2016 (04):26-46. [36] HOFFMANN E A. Dispute resolution in a worker cooperative: formal procedures and procedural justice[J]. Law & society review, 2005,39 (1): 51-82. [37] LANDES W M.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ourt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1,93(1): 559-603.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 [38] POSNER R A.An economic approach to legal procedure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J].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73,2(2): 399-458. [39] GOULD J P.The economics of legal conflicts[J].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73,93(2): 279-300. [40] SANDEFUR R L.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nothing: everyday problems and responses of inaction[C]// PLEASENC P, BUCK A, BALMER N.Transforming lives: law and social process. London: Stationary office books,2007:112-132. [41] GENN H G. Paths to justice: what people do and think about going to law[M]. Oxford: Hart publishing,1999:Table B1. [42] MICHELSON E. Climbing the dispute pagoda:grievances and appeals to the official justice system in rural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72(3):459-485. [43] SANDEFUR R L.Access to civil justice and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equalit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0,34(1):339-358. [44] 李俊.社會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5 (06):128-135. [45] MORGAN P A. Risking relationships: understanding the litigation choices of sexually harassed women[J].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99,(33): 67-91. [46] QUINN B A. The paradox of complaining: law, humor, and harassment in the everyday work world [J]. Law & social inquiry, 2000, 25 (4): 1151-1185. [47] 沈明明,王裕华.中国农民经济纠纷解决偏好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03):120-130. [48] SPIER K E. Chapter 4 litigation[J]. Handbook of law & economics, 2007, 1(7):259-342. [49] 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M].梁坤,邢朝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3-228. [50] 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1] PRIEST G L,KLEIN B. The selection of disputes for litigation[J].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4,13(1): 1-55. [52] NIELSEN L B,NELSEN R L ,LANCASTER R.Individual justice or collective legal mobilizatio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itigation in the post civil pights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010, 7(2):175-201. [53] EISENBERG T, HILL E T. Employment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an empirical comparison[EB/OL].(2003-05-26)[2022-08-20].https://ssrn.com/abstract=389780. [54] SHAVELL S. Law versus morality as eegulators of conduct[J]. American law & economics review, 2002, 4(2):227-257. (责任编辑:刘 艳)5CC7151E-9E9B-41D4-97C3-A6DB1721BA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