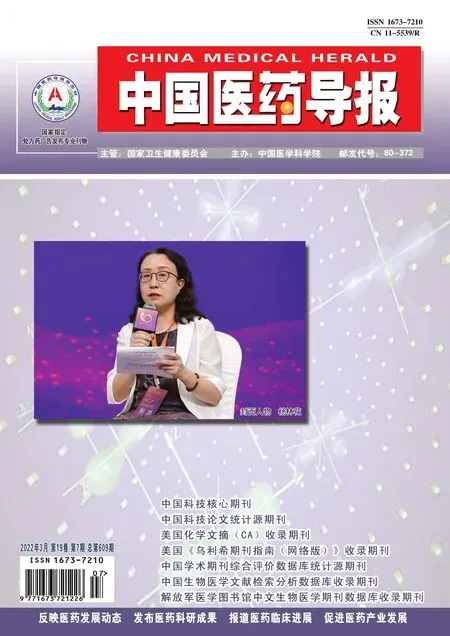阿片类物质成瘾相关情况的研究进展
刘 鹏 李 萍 杜洪霞 魏 明
西安医学院基础医学部药理学与毒理学教研室,陕西西安 710021
阿片是未完全成熟的罂粟果汁浆的干燥产物,应用历史悠久。来自古希腊的证据表明,阿片有多种使用方式,包括吸入、栓剂、外敷等。《本草纲目》中,记载了罂粟的种植、罂粟芽和种子的食用状况。阿片类物质是指任何天然的、半合成的或是合成的,能使机体产生类似于吗啡效应的一类物质,包括天然的阿片、吗啡、可待因,半合成的如海洛因,全合成的如哌替啶、美沙酮等[1]。
1 阿片类物质的分类及其特性
阿片中含有二十多种生物碱,阿片类物质有许多分类方法。常用的分类方法见表1[1]。

表1 常见阿片类物质分类方法
2 阿片受体及其亚型
阿片受体是一组抑制性G 蛋白偶联受体,与生长抑素受体约40%相同,广泛分布于大脑、脊髓、外周神经元和消化道[2]。
在20 世纪50 年代,吗啡和相关阿片类药物通过与特定受体相互作用引起镇痛被提出。Martin 等[3]证明一系列阿片类药物在体内显示出不同的药理活性特征时,提供了多种阿片受体存在的证据。他们提出阿片类药物可以激活3 种不同类型的受体,称为μ、κ和σ,典型的激动剂为吗啡,酮环佐辛和N-烯丙基奥佐他滨(又称SKF10047)。而后续研究表明σ 受体不再被认为是阿片受体,因为其既不显示阿片类受体的立体选择性特征,也没有对阿片类拮抗剂的拮抗效应,然而术语“σ-受体”仍在使用,用以描述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复合物中苯环利定的结合位点[2]。随着第一个内源性阿片受体配体[甲硫氨酸]-脑啡肽和[亮氨酸]-脑啡肽的发现,δ-受体被鉴定出来[2]。后来,学者鉴定了编码“孤儿(orphan)”受体的cDNA,其与经典阿片受体具有高度同源性(>60%)[4],该受体被接受为阿片受体“家族”的成员,最初被称为类阿片受体。
阿片受体的术语经过了几次修订。最初,受体是由首先发现者定义,使用希腊字母μ、δ 和κ。随后,根据国际麻醉品研究会的建议,μ 阿片受体(mu opioid receptor,MOR)、δ 阿片受体(deta opioid receptor,DOR)、κ 阿片受体(kappa opioid receptor,KOR)和痛敏肽/孤啡肽受体(nociceptin/orphanin FQ receptor,NOR)的命名方式被接受。基于药理学数据,近年来提出了其他类型的新型但表征不佳的阿片受体:这些受体包括ε-、ι-、λ-和ζ-受体,不过他们所受到的关注度并不高。
MOR、DOR、KOR 亚型各自在大脑区域具有独特的效果和特定的分布[2]。下表列出了3 种经典的阿片受体的中枢定位、效应、内源性配基与激动药代表(表2)[5]。

表2 3 种经典的阿片受体
3 阿片滥用的现状及治疗手段
阿片类药物通常用于控制疼痛,减少咳嗽或缓解腹泻。然而,用药过程中常会产生依赖性或成瘾性。2021 年7 月份发布的《2020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180.1 万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3%,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及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社会负担[6]。
180.1万名现有吸毒人员中,滥用阿片类毒品73.4 万名,占现有吸毒人员总数的40.8%[6-7]。近年来,由于全球疫情防控带来的失业率上升,使更多的贫困和弱势人群转向吸毒或从事毒品犯罪活动,成瘾治疗一直作为国家公共卫生的主要课题之一[6]。
药物治疗可缓解戒断症状,减少对药物的渴求感,帮助患者保持停药状态。用于治疗阿片类成瘾者的药物可分为三类:完全激动剂、部分激动剂和拮抗剂[8]。美沙酮,是MOR 的完全激动剂,可减少使用者的戒断和渴求症状,可降低其复吸的可能性。部分激动剂如丁丙诺啡,作为美沙酮的替代品,使用丁丙诺啡的患者通常不会发生呼吸抑制和欣快感。纳洛酮和纳曲酮是靶向所有阿片受体亚型的拮抗剂。纳洛酮对MOR 的亲和力最高,用于对抗阿片类药物过量患者的呼吸、精神抑制。纳曲酮靶向MOR 和KOR,长期注射用纳曲酮用于减少海洛因的使用。上述药物治疗手段,与精神社会疗法联合,可以有效地对抗阿片成瘾。不幸的是,这些药物疗法有局限性,如依从性较差等。此外,现有的药物治疗不能改善成瘾的关键环节,如强大的条件性联想(如线索、应激、药物本身)引起的复吸[9]。对于药物成瘾的生物学机制认知已经成为了开发有针对性及有效性治疗手段的迫切要求。
4 阿片成瘾的遗传易感性
通常认为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两者共同决定阿片类药物依赖的发生[10]。了解阿片成瘾的易感基因对于开发潜在的新型治疗靶点至关重要,同时也可能揭示阿片成瘾风险的遗传学生物标志物,为临床实践提供帮助[10]。
编码内源性阿片系统组分的基因是用于阿片成瘾遗传学关联研究的天然候选基因。奖赏相关环路中,阿片受体参与调节多巴胺及血清素的释放,除此之外内源性阿片系统还与其他神经递质系统相互作用,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能、谷氨酸能和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系统。这些神经递质系统的组分包括多种受体、膜转运蛋白和生物合成酶。编码这些组分的基因中的变体可能导致阿片类药物的下游效应改变,致使成瘾倾向的改变;因此,许多研究已经分析了这些变体与阿片成瘾的潜在关联[11]。另一方面,随着药物治疗的开展,不同个体对于治疗的反应并不相同,这也与遗传因素有关。部分遗传关联研究已证明[12-16]的与阿片成瘾相关的基因及其变体如表3 所示。

表3 与阿片成瘾相关的基因及其变体
5 吗啡成瘾相关的重要脑区及神经环路
吗啡是阿片类物质,在吗啡依赖和戒断的背景下,已经确定了几个关键的神经解剖学基质,特别是皮质纹状体通路边缘亚通路内的相互连接。这些脑区对于吗啡成瘾的影响各有侧重而且并不孤立,常以神经环路的形式联合,参与吗啡成瘾的调控[17]。
5.1 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
VTA 位于中脑底部中线附近,其内的神经元投射到大脑诸多区域,作为投射到皮质和边缘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的主要来源,在成瘾的认知学习和动机奖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8]。Van Ree 和de Wied 首次证明VTA 内给予阿片类药物受体激动剂可以诱导大鼠的自我给药行为[19]。VTA 富含MOR,并且VTA 内注射MOR 拮抗剂可显着降低吗啡诱导的条件性位置偏爱(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CPP)[20]。VTA 向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的GABA 能中型多棘神经元(medium spiny neurons,MSNs)发送密集的多巴胺能投射。而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可激活VTA 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导致其释放至NAc 的多巴胺增多,这在阿片类药物奖赏中起重要作用[20]。VTA 向其他脑区输出多巴胺能神经投射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吻内侧被盖核(rostromedial tegmental nucleus,RMTg)和NAc 等脑区的GABA 能神经投射,这些投射参与VTA 内多巴胺能神经元活动的调节[20]。在急性吗啡给药及戒断期间,大鼠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通过去除来自RMTg 的GABA 能抑制而被激活[20],而光遗传学方法刺激小鼠VTA 内的GABA 能输入则可以明显抑制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活动,并诱导条件性位置厌恶[21]。然而,GABA 能神经输入对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影响及如何调节吗啡依赖状态仍有待确定。
5.2 NAc
NAc 是基底前脑延伸到下丘脑视前区的区域,其含有与边缘系统和下丘脑等脑区的广泛联系,是成瘾药物的主要作用目标[22]。NAc 分为两个主要功能区域:NAc 壳(NAc shell,NAcs)和NAc 核(NAc core,NAcc),都涉及药物成瘾和药物记忆重建,但他们在这些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22]。例如,有研究报道,慢性吗啡暴露会引起NAc 内树突棘密度的改变,特别是在NAcs 中[23]。吗啡CPP 戒断1 周后,NAcs 中神经元的兴奋性增加,但NAcc 中没有[24]。NAc 中的MOR主要表达于多巴胺D1 型神经元,参与调节吗啡的奖赏效应及觅药行为[17]。NAc 中的神经元主要是MSNs,其主要包含D1 型及或D2 型多巴胺受体;NAc 其余细胞还含一些胆碱能和GABA 能中间神经元[17]。CPP形成后NAc 内注射D1 型和D2 型拮抗剂缩短了消退期,表明在消退期,NAc 内多巴胺受体的存在对维持吗啡奖赏特性起着重要作用[25]。
5.3 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PFC)
PFC 是位于前额叶的皮质区域,在动机相关记忆的处理中很重要,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与吗啡相关的联想记忆的表达相关联[24]。已有的研究表明,阻断PFC 的活性会降低吗啡的奖赏效果,并且在吗啡戒断期PFC 内的锥体神经元的兴奋性降低[24]。PFC 中的神经元也表达相当数量的MOR,可作为吗啡的直接靶标,PFC 内的多巴胺受体对吗啡成瘾有着调节作用,其内的D1 受体激活会阻止了吗啡奖赏效应的增强,并且阻止了恐惧记忆的回忆,而D4 受体激活的效应则与之相反[26]。PFC 与VTA 和NAc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构成了中脑皮质边缘多巴胺通路的神经基础[17]。PFC的神经元投射到VTA 内的多巴胺能和GABA 能神经元,并双向调节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活动[17]。VTA 向PFC 发送多巴胺能投射,而PFC 也向VTA 和NAc 发送谷氨酸能投射,一些研究表明VTA-PFC 环路涉及吗啡奖赏作用[17]。例如,PFC 和VTA 之间的谷氨酸能系统在谷氨酸释放和吗啡成瘾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PFC 的毁损可导致VTA 中谷氨酸释放的下降[27]。
5.4 海马(hippocampus,HIP)
HIP 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因其在学习和记忆形成中的作用而闻名,在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信息的巩固及导航的空间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28]。早期的研究多关注HIP 在记忆过程中的相关机制作用,而并非其成瘾功能。事实上,HIP 与成瘾相关记忆和药物奖赏体验的形成有着深刻联系,并且与许多涉及成瘾的大脑区域有交互联系,例如杏仁核、PFC、VTA 和NAc 等[17]。HIP 内的多巴胺受体参与吗啡成瘾记忆的唤醒,对于已建立吗啡CPP 的大鼠,其HIP 的齿状回内注射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则可减低CPP 的复吸点燃[29]。HIP 内表观遗传学相关的转录调控机制也被认为参与吗啡成瘾,如在吗啡自我给药大鼠模型中,在HIP 的CA1区内一种新DNA 甲基转移酶3a(DNA methyltransferase 3a,DNMT3a)存在表达上调,而于CA1 区注射其抑制剂或特异性敲减DNMT3a 则可破坏吗啡自我给药模型的建立[30]。有证据表明,重复的成瘾性药物暴露可以导致HIP 突触可塑性的改变,这可能在药物-环境关联学习记忆中起关键作用[17,31]。重复吗啡暴露会增强HIP 的CA1 区长时程增强诱导并阻碍长时程抑制诱导,并且阻止该脑区的胶质细胞则可逆转上述改变[31]。
6 展望
阿片类物质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是严重的医学和社会问题。其成瘾的机制复杂,涉及诸多基因和脑区的异常改变,现有的治疗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成瘾者对药物的渴求、缓解戒断症状,然而通常不能达到根除的效果。阿片类物质成瘾在相关脑区内及脑区间的神经传递系统中引起了显著变化,这可能成为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潜在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