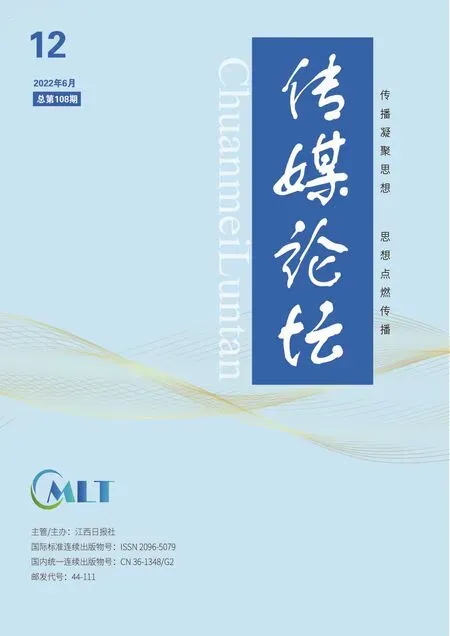主流媒体共情传播的情境构建
黄晓辉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媒体技术应用,丰富了新闻报道形式,也拓展了新的传播空间。主流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通过全媒体表达,甚至运用多维信息技术,营造沉浸式“新闻现场”,在满足用户信息需要的同时,与其产生“破防”“泪目”或“震惊”“愤怒”的共情体验,进而实现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和价值认同。因此,主流媒体如何构建共情传播情境,加强新闻报道的共情传播张力,对建设客观公正、理性自由的传播生态具有积极意义。
一、共情传播的概念
共情(empathy,心理学术语),源于移情、同情、同理等概念,包括怜悯与恻隐的同情、感同身受与设身处地的移情、认知判断与感知模仿的同理等情感体验和心理过程。共情传播,古已有之。俗语有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比如《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生动讲述了触龙通过父母之爱的共情,阐释“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最终劝谏赵太后的故事。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媒介真实对社会环境呈现逼真镜像,使“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境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1]越来越频繁和普遍。这个过程从共情传播的参与个体来说, 即从他人的立场出发理解他人内在状态和情绪体验”的认知情感状态,和“理解和分享他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做出反应”的能力[2]。综上,本文将“共情传播”界定为媒体通过新闻报道与传播对象之间产生正向情感联系和共鸣的互动过程。
二、共情传播的情境特点
作为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的主流媒体传播策略, 共情传播在传播媒介、传播关系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以下变化和特点。
(一)感官和情感的“人的延伸”
通过对口头言说、拼音文字和印刷,以及电子、音像等媒介的技术特性的研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中,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包括任何使人体和感官延伸的技术”等观点,揭示媒介对人的感官乃至人的塑造作用——受众通过接触媒介,获得信息、知识和观点等,正如交通工具是脚的“延伸”,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获得了新的人生体验。如果将媒介限定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 我们理解人与主流媒体的关系——接触产生延伸,延伸产生感知,感知生产环境。从移动新媒体的媒介特点来看,首先,音容并茂、形神兼备等全息内容扑面而来之时,势必比需要更大主观意愿参与的单一媒介,更容易投入注意力并唤起共情,获得“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体验。其次,实时传播的直播技术,为大众构筑了“时空同在”的媒介环境,使短时间内更大范围人群的“感同身受”成为可能。第三,新媒体的交互分享功能,使用户在个性化生存中通过信息分享和传播行为, 通过共情传播寻找“同伴”,获得网络虚拟世界的自我身份确认。
(二)“听讲者”转为“对话者”
从微博博主到短视频平台UP主,新媒体时代,“任何受众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递者,他们利用摄像机和相关软件以及在互联网拍摄、制作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上传至网络,与网友共同分享信息甚至反过来影响着新闻事件的发生。[3]”传播关系从大众媒体向受众的单向度,走向了“受”众不“受”的网状传播,即“传播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传统的受众角色——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消费者、目标对象将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搜索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等诸多角色中的任何一个[4]。”新媒体用户不再是单纯被动的内容接受者——他们是围观者、转发者、评论者,甚至是新闻生产或新闻事件发展进程的推动者、参与者。这一角色的改变,使他们与媒体的传播关系,从“听讲者”转为“对话者”。新闻不再是讲授,它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但具有更大上升空间的与受众的对话。大众媒体需要让对话更加有效,就需要尊重新媒体用户的主动性和“表达权”,通过构建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促进共情传播行为的发生。
(三)共情需要的“再中心化”
今天人们将更多时间用来刷朋友圈、拍抖音、上直播。内容的供给已不是大众媒体的独有权利。碎片式的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日益发展,使信息的传播权力由媒体机构转移到新媒体使用者,内容的分发从曾经的编辑主导变为今天的“千人千面”的算法推荐。这种“去中心化”的机制,使内容生产门槛变低,内容分发效率变高。同时也因其专业化程度不够、社会责任感不强,出现消解大众注意力的现象。当新媒体用户想打破 “信息茧房”的桎梏,大众媒体则需要聚焦公众“无处安放”甚至“随意安放”的共情需要,充分发挥专业权威优势,抓住社交媒体平台分发特点,利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平台抢占先机,及时、全面、客观地阐述事实真相,与大众共情,吸引网友关注、分享,通过更具深刻价值的内容,实现“再中心化”,重建权威诚信形象,引领公众的情绪和认知导向正确的方向。
三、共情传播的情境张力
“张力”原为自然科学术语。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一般被用来表现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既彼此对立、冲突,又相互补充、吸引的一种紧张关系。从共情传播的过程和效果来说,包括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沟通和理解的意愿等内在条件,传播者、议程内容与表达、媒介之间共同存在的方式等,是产生传播张力的主要元素。共情的发生通常需要一个沉浸式的心理环境或行为情境。共情传播情境主要有客观情境、主观情境和关系情境。
(一)客观情境:“客观性”与“情感性”
在共情传播过程中,报道对象、传播对象的客观性,包括两者的事实信息,也包括情绪情感等客观精神状态。传播者需要通过新闻生产过程,发挥媒介的联通作用,在客观情境的传播互动中,实现新闻媒体的信息传递、人文关怀、精神重塑、情感抚慰等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传播者一定要明白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传播对象的作用和意义。比如,新闻事件发生时的日期、天气和新闻人物的个人信息等,或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等。新闻媒体要具有强烈的受众意识和准确的受众接受偏好判断,在遵从与该事件相关的一系列客观规律下,采集最全面的原始信息,采用最为公正、平衡、使意见与事件相分离的手法,来做到最大限度的客观。共情传播的客观情境张力,在于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及其对传播对象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也应关注“情感性”在客观情境张力中的作用。这里的“情感性”,需要与“主观性”加以区别。在此,是指对报道对象真实情感的客观记录和传递,于新闻媒体的立场、观点无关。即新闻媒体将事件中人物的情感反应或者情感要素,作为新闻报道素材,以第三人的叙事视角记录并传递或悲或喜的情感,形塑了受众对于特定事件和具体人物的共情认知。
(二)主观情境:“共享表征”的选择与表达
“要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影视艺术如是,新闻传播也如是。影视艺术通过剧情、表演、背景和蒙太奇手法,为观众营造共情传播的主观情境。新闻媒体则需要依靠能够引发传播对象主观上的关注、参与的内容和议程。心理学将其称之为“共享表征”(shared representation),即人们对于自己实施过的动作和体验过的情绪会产生一个心理表征,而知觉到他人实施同样的动作和体验同样情绪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心理表征[5]。在共情传播中,如何以中介物桥接不同的传播主体以引发其“共享表征”,是实现彼此“心通”的关键环节。所谓中介物是指引发传播主体产生相同或接近情感态度的客观事物,它可以使传播双方见之动心,会之起意,触之生情,有效促成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是“心通”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也是共情传播中的“决定性符号”。中介事物越是恰当,越被双方所共同认可,就越容易在传播主体间产生“共享表征”,共情传播的进展也就越顺利,主观情境张力亦会越强。反之,共情传播效果则会效果甚微,甚至起反作用,产生反感和排斥情绪。
(三)关系情境:用户意识与传播策略的调适
媒介内容生产的根基是建立在社会化关系基础之上的。“从关系的角度来看, 整个社交平台不断演进的过程,可能就是关系情境和关系模式演进的过程[6]。”在新媒体网络传播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边界模糊,甚至互相融合。但不论媒体技术如何演进,人类作为情感动物,相较身份圈层、知识储备、思考能力等传播效果因素,朴素的情感更具有广泛性、共通性和传播性。在海量信息与受众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紧张关系中,媒体诉诸情感的报道往往更能获得受众注意力的停留与聚焦,并进而产生跟评、转发和点赞等二次传播行为。主流媒体的关系情境张力大小,取决于与用户贴近性的强弱。根据舆论引导的需要,主流媒体动态调适叙事话语和传播策略,客观、适当地融入报道对象的情感元素,甚至是记者作为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的个人情感,让新闻报道更具人文温度,使共情传播产生理性共鸣和亲社会行为。
四、共情传播的情境构建
传受关系的理想状态是成为朋友和伙伴,在互动的情境中共同参与完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阐释。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客体“感同身受”,需要“换位思考”的共生状态和平等传播关系、人人关心的具有人本价值和公共意义的事件和议程、共通共鸣的情感卷入空间等传播情境构建。主流媒体的共情传播情境构建,结合新闻报道中的议程设置、叙事范式、表达方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共情议程:用户思维在新闻报道的投射
“共情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1]。”共情议程设置需要密切关联社会生活,从某一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事件中表达、传递普世情感。公众的情感在新闻报道的调动下形成情感共振,集体情感对个体情感的吸引和同化使个体情感得到表达并找到宿主。在议程设置和共情传播过程中,要注意“反向议程设置”情况和发展。反向议程设置是指新媒体用户热烈讨论的话题和观点,与主流媒体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时,在“传者本位”惯性上,要加强用户意识,与“自下而上”的受众议程设置相结合。
以人民日报客户端、新湖南客户端等主流媒体关于袁隆平逝世前后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在对其光辉一生的回顾报道,侧重于讲述袁隆平坚守初心、矢志报国的“执”,不被理解、成千上万次试验失败的“难”,提高水稻单产、解决吃饱饭问题的“功”,载誉无数,却把“下田是头等大事”的“朴”。特别是通过“街边小店理发16年”、90岁高龄“说英文”“背乘法口诀” 等, 展示一位科学家对生活的热爱。这样将议程聚焦于袁隆平的伟大与平凡,让受众走近报道对象,感知更为立体的血肉人物,通过“父爱”“爷爷的爱”等情感,在事件人物与受众、报道与受众之间产生情感共振。特别是将网友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留言评论融入报道中,以反向议程设置来推动“精准共情”的实现,激发受众“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的同感与共鸣,“成风化人”的传播效果则随之形成。
(二)共情叙事:同一性身份的群体画像
“共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感染和投射,即个体的情感状态引发另一个体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情感状态,使之发生作用的是个体直接感染性的情绪刺激。在追思袁隆平院士的报道中,通过湘雅医院外、杂交水稻中心、悼念厅等场景,聚合前来参加追悼的人物群像,唤起更广泛受众的不舍、敬佩等情绪。这一在有限的篇幅内集中予以传播对象强大而丰富的信息量的叙事范式, 包括人物的处境、个体心理和情绪、与核心人物的关系和事件等,营造同一情境笼罩之下的相似情绪体验,唤起情感共鸣。
在新媒体报道中, 新闻媒体为了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常在跟踪报道中,引用网友对某一新闻事件的互动留言等。因为作为读者的身份同一性,新闻报道与“镜中我”相互映照,使持有的某种情绪和观点更容易被网友接受,形成极具感染性的共情张力。
(三)共情互动:新闻平衡的积极理性表达
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其采访报道的出发点必须是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它所唤醒的、传播的情绪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能够发挥“社会阀门”作用,推动问题解决的。在袁隆平逝世报道中,虽然有哀伤、悲痛的情绪,但通过“无以为报,光盘致敬”“听着您故事的孩童长大了,我们会顶起国家的未来”“我好像和他有一面之缘,在课本上,在饭桌上,在人间里”等直接引述,情感予以延伸,引导青少年追科技之星、知识分子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传达严肃意义需要严肃的内容,是主流媒体的优势和权威性所在。新闻报道要坚守真实性,从人、事、物、细节等诸多方面还原真实、靠近真相,靠理性把握新闻的平衡。不能如同监控摄像头一样站在一个高高的点上,远距离俯视事件。如央视对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直播时, 当记者看到可能是遇难者身份证件时, 马上用手遮挡,并提醒摄像“这个不用给特写”。媒体通过类似的“传者本位”表达积极情感,保护受害者避免二次伤害,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过度负面信息带来的负面情绪。
五、结语
当下,社交媒体中的新闻生产出现了主观化、夸张化、故事化叙述以及拟人化等多种表达方式,情感作为引导新闻舆论的因素被较多地融入其中。我们不能将共情传播片面理解为,只要是情感性信息的传递或情感信息越多就一定产生共情。真实、客观是新闻的生命,是媒体公信力的源头,也是传播对象共情的基点。共情传播作为报道策略和手法,是基于传播社会效果的综合考量,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赋能共情传播,还要注意避免非理性情绪的反噬。人类的传播行为和过程因传播对象、传播环境和效果诉求等,通常具有话语性和表演性。因此探索主流媒体共情传播的实践,对实现完美交流的可能尤为重要,需要我们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