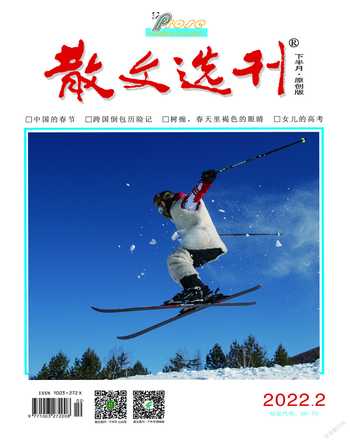家乡的水井
凌奉云
老家有口井,不知诞生于何年,只有井壁上爬满的苔藓、勒痕和那被岁月磨得圆润平整、八面玲珑的井沿石才懂得它的历史;它本来没有名字,因为位于“垄中央”,所以村民习惯叫它“垄里井眼”。
水井是原始的,井水是清澈的。当你站在井湄,探身井口,自己的影子便倒映在水面,比镜子里的你显得更加年轻、真实,我想那应是原始的东西映衬了真实的自我。
老家的井水清澈而甘甜,你若舀出井水,一股薄荷般清新湿润的水香便沁入心脾,让人立马神清气爽;劳作归来的农夫,第一件事便是舀上一瓢井水,喝上几大口,精神便为之一振;如果炎炎夏日,用井水浸泡一些瓜果,那味道更是绝顶的香甜。该井水还非同寻常,也不知是村里人的身体棒还是井水的品质好,喝了刚刚从井里打上来的生水,从来没有人闹过肚子,哪怕再吃几块肥肉也不会有事。
老家的井水温暖中带着清凉,由于井水来自地下岩层深处,因此,常年保持恒温。冰封的寒冬,井水温热如故;喷火的炎夏,井水清凉依然。记得有年三伏天,收割一个上午稻子的我,疲憊不堪,焦渴难耐,来到井边打了一小桶井水,把一部分倒入盆中;赶紧洗了个脸,擦了擦身,一身的燥热随之散去;然后迫不及待地把余下的小半桶水,像给抽水机加引水似的,咕咚咕咚灌了下去,一股透彻心扉的清凉瞬间传遍全身,暑气尽消,困乏全无。然后坐在井边的槐树下,一股凉风吹来,透心凉快,爽得几乎窒息。不知不觉便将我带入了甜蜜的梦乡,那感觉好像到了天堂。
“垄里井眼”什么都好,可惜就是离家有点远,且是三个生产队共饮一井水。当年排队取水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只见男女老少,或挑着桶、或抬着罐、或提着壶,摩肩接踵,排成一条长龙,看不到头,望不见尾;不时有新来的,老远就扯开嗓门,与队伍中的人大声招呼、开开玩笑并自觉排队;要是哪家有什么急事,也可插队优先。趁着等水空闲,有的织起了毛衣,有的唱起了山歌,有的干脆席地而坐,在井旁拉起了家常。女人们多说些家务事,男人们则议些大事,如东家建房屋谁去帮工,西家办喜事,谁来凑份子,这种帮助都是无偿的,凑份子都是自愿的,久而久之,“垄里井眼”就成了一个村里的新闻中心、议事场所,村里人一天不去“打卡”,心里就堵得慌。
取了井水之后,主要靠挑着回家,挑水便成了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家务,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劳动技能。而挑水是项技术活,不但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小时候我非常羡慕大人们挑水。他们挑着盛满井水的水桶,沿着阡陌纵横的田埂、和着欢快动感的节拍走得又快又稳,水桶里的水就像黏住了一样,一点也淌不出来,真是胜似闲庭信步;那哪里是在干活,分明是模特在T台走秀,吱吱的扁担声、踢踏的脚步声、咣咣的淌水声,便成了它的伴奏曲。记得有一次,父亲看我干活很累,要我给抢收抢种的乡亲挑水解渴。我以为拣了一份轻松的活,没想到挑水的路远、路窄、路况差,加之我又缺少挑水的经验,以致水桶左右摇摆,井水也随之淌出桶外,满满的一担水,到达目的地时却不足一桶,挑了一天水连喝水的嘴都没供上,真是费力不讨好啊。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脸红。那个年代,一切均靠手工劳作,除了繁重的农活,还有像挑水这样做不完的家务,因此,有时我们想喝口井水都成了奢望,那些缺劳力的家庭便干脆喝起了塘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伯父退休回家,看到有的村民还在喝着塘水,非常心痛,便组织大家在门前大塘尾巴头打了一口井,“塘里井眼”虽然没有“垄里井眼”的水质好,但比起塘水来卫生干净,比起“垄里井眼”更显得慷慨富足,一年四季泉水汩汩,即使大旱之年也保持着不变的水位。村里人洗衣、洗菜、做饭、喂牲口等,都离不开它,只是偶尔在“垄里井眼”挑挑水打打牙祭。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压水井的兴起,取代了传统的挑水方式,几乎每家都用上了它,只要呼嗒呼嗒地压几下,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可父亲却说,这铁家伙冒出来的水不太正宗,有股铁腥味,还坚持从“塘里井眼”挑了一段时间的水,但最后我们兄妹均外出工作,他也慢慢地适应了。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家启动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家乡也建起了水塔,安装了管道,足不出户就能用上卫生洁净的自来水,于是,水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