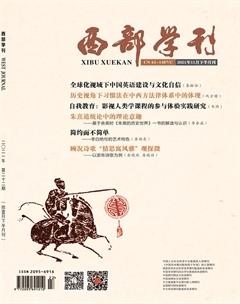论朱、陆学说的政治分野与阳明心学的调和
摘要: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顺序存有不同的主张,两种学说的差异不仅使得此后的王朝统治者对二者采取了迥乎不同的尊抑态度,同时也使其各自的弊端在人们的理论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显露,而这也恰恰成为了阳明心学诞生的滥觞。一方面,王阳明对陆学中不合政权要求的部分做了淡化处理,从而可以为王朝统治者的统治提供必要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在精神层面上将行为标的与成圣主轴确定为自身,将对王朝统治者的效忠只作为自心道德的物质显现。正是在对朱、陆两种政治倾向的调和之中,阳明心学映出其自身的理论光彩,从而为后世提供了极具思想价值的龟镜与借鉴。
关键词:朱熹;陆九渊;阳明心学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157-04
虽然朱熹和陆九渊①二人皆是以“成圣”为鹄,但在求道先后顺序及落脚点等问题上二者仍有分歧。正如秦家懿所指出的:朱陆二者之间的分歧,在于“进学或修身的先后重要性”[1],亦即二者对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先后顺序存有各自的主张。与朱子理学首重“道问学”不同,陆九渊坚持将“尊德性”置于“道问学”之先,并由此阐述了其“先立乎其大者”的心学思想。如高全喜所言,“陆九渊的心学自有一番超迈独绝的雄姿。这种动的充满生命力的雄姿,与朱熹的静的凝含生命力的风范,构成了理学的两种景致”[2]。可是,在历经宋元两代发展后,朱熹理学获取了此后王朝统治者的承认与支持,并逐渐取得了陆学无可企及的官学地位。由此可知,朱学独尊地位的取得绝非单纯地由于其理论优势,同时还应当与王朝统治者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
一、朱熹的正统理论与其内在矛盾
朱熹所主张的问道顺序同陆九渊之间看似只有先后顺序的差别,但其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却如同天壤。要而言之,相较于陆学,朱学对王朝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不同于陆学以一种弱政治化的个人存养为修学之始,朱熹对道问学的推重无疑为统治者留出了更为充分的腾挪空间,亦即在学子们道问学的过程中,王朝统治者可以借助掌控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来影响士人们的思想塑造,从而维护其自身统治。李锋指出朱熹理学“由于对外在的天理的普遍必然性的强调,往往使道德主体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以天理的宰制勾销了自我的选择
和决定”,他由此认为这种压制会使得人们丧失其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立法”功能[3]。而陆九渊先“尊德性”的心学理论则很难给统治者留下施加影响的机会,故而王朝统治者必然会对朱熹推崇备至,对陆学则刻意予以贬斥或忽视。
其次,朱子理學自身的理论特色天然地有利于王朝统治者的统治。因为在“人欲”向“天理”的绝对转圜中,统治者的圭臬作用自然要被肯定与强化,由此朱子理学便赋予了王朝统治者更多的权威与统治合法性。朱熹在注解其最为重视的《大学》时,对其中“大畏民志,此畏知本”一句给出的解释是“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4],而在其所著的《诗集传》中,又对《召南·江有汜》一诗引用了“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盖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尽其道而已矣”[5]的前人之注,这些解释无疑是在理论上有利于维护彼时社会的纲常伦理和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最后,由其确立四书以确定子思、孟子地位,并提出了“尧舜—孔曾子孟—程朱”的道统传承可知,其对道统颇为重视。需要予以承认的是,宋代儒家道统论的确立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时代价值。朱汉民认为,宋代士大夫群体“以《四书》学的建构和儒家道统论的重建完成了儒学复兴的历史任务”[6]这种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就王朝统治者的角度而言,这种道统论的确立对其统治本身也不无裨益,因为这种“祖述尧舜”式的道统论无疑会使得人们对圣贤之教抱有更大的服从心理,而王朝统治者可以通过对圣人的绝对尊奉来掌握话语权,并由此将人们对圣人采取的畏惧态度嫁接于自身。
但这些并不能够表明朱熹的学说便是完全有利于王朝统治者长久统治的,其学说对于王朝统治者最大的隐患或许就是道心与人心的差异在统治后期会转化为政权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葛兆光曾指出,程朱理学造成了一种“肯定超越与承认现实、肯定天理和确认生活”之间的紧张,当这种紧张以一种官方且教条的面目出现时,便“更可能窒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活泼想象和自由思索。”[7]换言之,朱熹将道心与人心对立起来,又难免不将王权与道心、被统治者与人心联结,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便有了转化为官方与民间摩擦的可能,这种对立是其理论是本身固有且无可避免的,而随着其王朝正统官学地位的持续巩固,其工具性价值也会不断地被王朝统治者依据其自身的需要而加以发掘和利用,其理论学说便会面临被有目的地阐释甚而是被篡改的处境,此时其学说所蕴含的那种对立便会因被统治者心中厌倦情绪的增强而愈加显现出来,原本借此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政权便必然会面对较为严重的统治危机。
二、陆学的非官方地位及其积极意义
宋儒虽然旨在崇儒而贬斥佛老,但事实上又多受佛道之教的影响。萧公权曾指出“理学家之哲学思想,以受佛学之冲击与道教之影响,融会调和,遂成新颖严密之系统,开中国哲学史之新纪元”[8],而佛道二氏的理论特色又尤以陆学取用较多,其“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9]551的心学主张很容易便会使人们联想到禅宗“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10]这一禅宗的印心之语。因此其陆学便具有较朱学更为强烈的超越意识。
这种超越意识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自其将本体归之于内在的澄明之心而非外在的绝对规律这一理论特色。陆九渊所遵循的本就不是朱熹那种借由“格物致知”来不断向外体悟宇宙中至上的绝对规律并加以执持与应用从而成为圣贤的路径,而是类似于禅宗那种不断向内淳养心性,从而显明人人皆有的圣贤之心从而成为圣贤的方法。这种意识虽然会有助于个人心灵的超脱,但其“内向”的理论方法难免会使得现实的政治世界遭到轻视,其就现实政治领域而言有些粗砺的理论并不能为彼时的王朝统治者提供急需的统治合法性支持。张立文就曾明确提出,陆学之所以趋于衰微的重要原因便是“统治者并没有体认到陆学有补于治道而加以倡导”,而“有补治道”正是宋理宗时期“朱学之所以兴盛的实质”[11],这或许便是陆学非官方地位的缘由。
但陆学无疑也有朱学所不具备的积极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不会存在朱熹那种将作为天道代理人的王朝统治者与代表人欲的个体相对立的情况。陆九渊曾有言“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听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为也”[9]463,这或许便是其学说有别于朱子理学的魅力所在。陆学达成了这样一种肯定,亦即无论是愚夫愚妇,还是博学鸿儒,都能且只能依其诸善具足的本心而非外在的绝对规律才具有成圣的可能性,而当一个人做了有悖礼法之事,所违背的不是如朱熹所言的外在规律,而是戕害了其自身本来仁义具足的纯和心性。也正是由这一角度出发,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才首重“尊德性”,并对朱子理学提出了“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9]463的批驳。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对于统治者而言,陆九渊理论之所以难以被接受不是在于其对德性本身的尊崇,而是其先“尊德性”主张很容易将现实政府所需求的存在理由悬置在不可知的未来之中,而这是存在于当时的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三、阳明心学对朱陆二氏学说的调和
鹅湖之会②并未能使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得到双方所乐见的调和,而随着时间的淘澄,明代朱熹理学的理论特色受到了王朝统治者的青睐和绝对推崇,这也可谓是一种必然。但随着彼时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滋长又使得曾经将上层人士伦理道德引入民众生活世界的程朱理学③显现出愈加僵化的态势,故而许多学者对陆学给予了同情,不过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陆学的超脱意识使其不可能直接被统治者所宽容与信赖,这两种学说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淬炼来使矛盾得以调和。
需要提及的是,即便只将眼光限制于有明一代,这种调和理论的提出也并非肇始于王阳明④。冈田武彦提到早在明初,与宋濂同为《元史》编纂总裁的王祎便提出了“惟合朱陆之异,则学术之真有证矣”的见解,认为朱、陆二者的学说不可偏废[12]。不过,这一调和又确是在王阳明的手中得以真正实现的。在经历了数年屯蹇之后,王阳明终于在任职龙场驿丞期间领悟到了“心即理也”的道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这一理论进行一种简单的阐释,亦即朱熹所主张的那种需要通过“道问学”,即格物或诉诸圣贤之书等方式所汲汲寻求的天理,并非外在于此心而自成一个绝对定律,而是经由锻炼除去渣滓之后显现出的自心本身,因此,所谓的“致知”,也并非是致心外之“知”,而是达致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13]中为人们自身具足的良知。由此而言,阳明心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被视为朱陆二氏之争的调和的。钱穆就曾指出:“阳明虽讲心理合一,教人从心上下功夫,但他的议论,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派。”[14]阳明心学在保留朱陆二者优点同时又对二者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弥补,而这种调和也在政治上起到了如下效应:
一方面,王阳明对陆学中不合政权要求的部分做了淡化处理,从而可以为王朝统治者的统治提供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且这种对王朝统治者的效忠不是如同陆九渊那种“支票式的”效忠,而是一种当下可为且应为的效忠,甚至指出了这种效忠是个人成圣的必要基础,人们不需要等到心灵明彻之后才采取行动,而是应当以忠君等方式作为修心手段。例如,他曾指出“知臣之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15]220,而当有属官请教如何处理案牍公事的烦扰与为学之间的关系时,王阳明又鼓励他“从官司上为学”,并告诫这位求学者“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15]389。事实上,王阳明一生的事功也为这一主张做了最生动的注脚。
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在精神层面上将行为标的与成圣主轴确定为自身,而将对王朝统治者的效忠只作为自心道德的物质显现,也即是说,阳明心学在实践上虽是有忠孝色彩的,但究其内核则是自在自为的。这又关照了人们日渐诉求的個性独立需要,正如杨国荣所指出的,程朱一系“是通过化心为性达到心合乎理,而不是由心颁布道德律,换言之,理入主于心压倒了心的自主性”,而王学“以心为体”表现了不同于程朱之学的品格[16]。
就以上两个方面而言,王阳明的精金之喻可谓是该种调和其最好的凝练,他通过“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的譬喻巧妙地将人人皆可为圣贤同古代王朝森严的等级差别结合起来,在关照现实政治,维护基本王朝等级制度的同时,又赋予所有人以同样的人格尊严与成圣可能性,从而意图达到“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15]240的理想政治图景。王阳明的这种调和可谓是哲智的,在现实世界中将人的自为转向政治的效忠,这便维系了政治的存续,消解了陆九渊心学所隐含着的消融政治的危险;而当自身修为由朱熹那种道心规制人心的外部施压转向心学式的个人自觉时,朱熹理学由对圣人之教的热忱崇拜导致的对个人价值的压抑也得以缓和,人们的思想之树也因此得以相对自在的舒展。
结语
阳明心学是适时的,因为他为彼时许多时代的困惑者提供了脱身于朱、陆之争的理路,正如其弟子徐爱在《传习录》序言中所说:“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愈近而造之愈益无穷”[15]6。这种称赞无疑是闻其道后发自内心的欣喜与景仰。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亦对王阳明持有盛赞,他认为其学说“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17]。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阳明心学也是超前的,因为其时王朝统治者及此后的清王朝都无法为学说的展演提供充分的现实空间。中国如今在相当多的领域都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而在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也会存在着许多难题需要解答,无论是公民道德的培养,还是政府治理与个人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王阳明的这种对朱、陆学说的调和可以为现代政治提供丰富的启示与借鉴。
注释:
①朱熹和陆九渊: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陆九渊(1139—1193年)南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字子静,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主“心即理”说。他认为要认识宇宙本来面目,只要认识本心。其学术思想,为明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②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后比喻具有开创性的辩论会。
③程朱理学:亦称为“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其由北宋时期程颢与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多人传承,到南宋时期朱熹集为大成。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
④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年),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汉族。明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王守仁平定思田、诸瑶叛乱,剿灭南赣盗贼,创立“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后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其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
参考文献:
[1] 秦家懿.王陽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2] 高全喜.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10.
[3] 李锋.朱熹政治哲学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09.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9.
[5] 朱熹.诗集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9:15.
[6] 朱汉民.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J].中国哲学,2018(10).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68-269.
[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96.
[9] 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2020.
[10] 普济辑.五灯会元(上)[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71.
[11] 张立文.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97-398.
[12] 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22.
[13] 孟子.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230.
[14] 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67.
[15] 王守仁.传习录[M].北京:中华书局,2020.
[16] 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60.
[17]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6-7.
作者简介:孙浩铭(1997—),男,汉族,辽宁辽阳人,单位为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