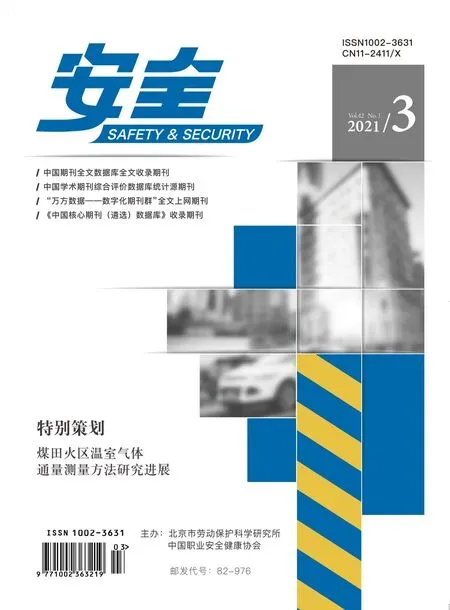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问题及对策
胡 成副研究员 李露凝 刘梦航 李 强教授
(1.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室,北京 100054;2.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0 引言
入境旅游是我国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境旅游人数的持续攀升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通报,2015-2019年,入境旅游人数分别为1.34、1.38、1.39、1.41和1.45亿人次,分别增长3.5%、0.8%、1.2%和2.9%,呈逐年增长态势。入境旅游人数的统计既包括外国人,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然而,我国的入境旅游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有3次大的事件导致国内入境旅游人数大幅下降,分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导致入境签证持续收紧,使得入境旅游人数呈现断崖式下跌,可以将其列为第四大影响事件。除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外,旅游景区的涉外旅游突发事件也会对入境旅游者造成很大影响,一旦处理不力甚至使国家旅游形象受损。因此,加强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尤为必要。
我国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晚。2003年非典疫情加速国家应急管理综合治理模式的转变,2005年出台《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13年通过我国第一部《旅游法》,2016年通过《旅游安全管理办法》,“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健全旅游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一案三制”保障体系。因此,有必要按照从特殊到普遍的基本原则,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发现我国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相应的解决对策。
本文以1990年以来比较典型的3起入境旅游突发事件为例,包括1994年“3.31”浙江千岛湖特大杀人劫财毁船事件、2008奥运期间“8.9”北京鼓楼杀人事件、2019年“4.29”北京故宫穆斯林跪拜事件,在分析特定事件应急管理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探讨入境旅游背景发生变化下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
1 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
参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考虑财产损失以及国家旅游安全形象和入境者身份因素,可将入境旅游涉外突发事件定义为: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而发生的重大入境游客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事件。
1.1 “3.31”浙江千岛湖特大杀人劫财毁船事件
1.1.1 事件经过
1994年3月31日,浙江千岛湖发生特大杀人劫财毁船事件,共造成33人死亡,其中台胞旅客24名(其中女性13名,有5对是夫妇)。经查明,吴黎宏等3人为了在湖上抢劫游客钱财,驾驶摩托艇尾随“海瑞号”游船,跳上游船后先用枪顶住船老大,把驾驶舱控制起来,然后冲入游客集中的中舱,使用猎枪和斧头恐吓游客交出钱财,然后驱使游客进入底舱,并在游船驶入黄泥岭水域后撤除底舱唯一铁梯,先后采取放水、炸药炸船、枪击和汽油纵火方式侵害游客安全,最后底舱起火导致游客、导游及船员共33人全部被害。
1.1.2 经验教训
(1)新闻封锁方式导致宣传阵地丢失。我国当时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注重集中统一,习惯于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而台湾地区相对强调新闻自由,重视即时反映,追踪报导。惨案发生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封锁新闻方式,海外媒体及港台媒体先入为主,不顾事实真相,炮制了大量“推测性新闻”,一次偶发性的突发事件被描绘成政治事件,海峡两岸关系陡然紧张。
(2)旅游安全管理混乱,缺乏预警措施。据报道,当晚8时游船没有按时靠岸,管理部门想当然认为该船可能停靠别的港口,没有向上级协调确认海瑞号异常情况,更没有报警,贻误救援时间。
(3)隐瞒刑事案件事实,对外宣称是游船意外失火事故,造成后期善后被动。现场勘查发现,底舱铁梯失踪、柴油船上出现汽油桶、底舱出现近百个拇指大小孔洞、底舱出现民用炸药包、死者尸体只有一半炭化、个别尸体手臂断裂骨折、柴油船体完全烧毁、游客财物全部失踪、全部人员包括船员都来不及逃生、不跳水反而集中到底舱自寻死路,种种迹象都指向刑事案件。但当地政府为息事宁人,准备采取意外事故加赔偿的方式解决善后事宜,反而导致后期被动。
1.2 “8.9”北京鼓楼杀人事件
1.2.1 事件经过
奥运会开幕式第二天,2008年8月9日中午12时20分许,浙江男子唐永明在东城区鼓楼城楼二楼上突然持械袭击3名游客,致1人死亡2人受伤。行凶男子随后跳楼,当场死亡。警方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警方确认,死者为美籍男性游客,一名伤者为美籍女性游客,二人均持旅游签证入境,这2名美国游客是美国男排一位教练的亲属。另一名伤者为中国籍女导游。
经查,行凶男子唐永明47岁,浙江省杭州市人,生于1961年3月4日,2003年与妻子离异,原为杭州某厂职工,辞职后于2006年将其在杭州的住房转卖,无固定居所,无固定工作。2008年8月1日,唐永明离开杭州前往北京。浙江省公安机关经过认真查证,初步认定唐永明在北京东城区鼓楼持械行凶系对生活失去信心,迁怒于社会而产生的个人极端行为。
1.2.2 经验教训
(1)事件耗费了大量外交资源。遇袭事件发生后,引起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外交部、北京奥组委以及中国卫生部多位主要领导参与应对。
(2)事件给欢乐祥和的奥运活动蒙上阴影,使得奥运整体环境的安全形象大大降低。
(3)景区安全防范措施仍存在很大漏洞。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尤其是地标性建筑,没有对刀具等危险性物品进行筛查防范,也没有配备相应的安检人员和设备。鼓楼伤人案件提醒有关部门注意加强旅游组织工作,在景区入口设置反恐安检设施,进一步加强旅游安全。
(4)事件后期处置披露不足,引发中国女导游不治身亡的谣言。在救助期间,中国女导游先在积水潭医院进行包扎处理,后转中日友好医院。但因相关处置的披露不足,没有及时回应社会关注,造成谣言产生,引发新的社会舆情事件。
1.3 “4.29”北京故宫穆斯林跪拜事件
1.3.1 事件经过
2019年4月29日,外国来京穆斯林游客在故宫游玩时,在广场上跪拜进行祈祷活动,造成现场群众围观,并引起网络关注,形成网络舆情事件。现场群众和网民对故宫中的跪拜行为表示难以接受,该行为甚至涉及违法,激起众多网友批判。
1.3.2 经验教训
(1)旅游服务人员缺乏底线思维,对相应的法律不熟悉。《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并且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显然故宫属于非宗教场所,因此故宫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穆斯林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到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例如清真寺。
(2)旅游景区对导游等第三方疏于监管。故宫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区之一,旅游安全形象影响范围极大。故宫内部对于自身人员的服务培训比较重视,但是对大量外来带客导游及外宾接待人员则疏于监管。导游和外宾接待人员以服务为主,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对于此类跪拜事件的敏感性不足。
(3)应急管理体系缺乏系统性,应急预案的场景缺乏针对性。大部分应急预案关注常规的火灾、大人流、食品安全、刑事犯罪等事件,这些事件属于容易形成人员直接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应急场景,但对涉及民族、宗教、外国人等事件则缺乏专项规定,相应的应急演练和培训更是无从谈起。
2 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形势
国家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对入境旅游群体虽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相关应急管理体系仍不完善,导致在相关事件的应急处置中仍然出现很多问题,甚至产生重大涉外政治影响。
2.1 国家旅游安全环境仍然严峻
近十几年,国家安全面临“疆独”“藏独”“台独”和“港独”多种威胁,发生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此外,国内极端上访事件也常有发生,极端上访者为造成影响效果,也可能会选择外国人作案,这些因素都对入境旅游安全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
涉外突发事件信息敏感,社会影响大,容易产生“连锁效应”和“放大效应”,给国家安全形象和旅游形象带来很大损失。从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看,大部分后果不属于严重类别,有些甚至没有直接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但仍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相关事件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最终形成重大社会舆情事件。
2.2 入境游客的旅游形式已发生重大变化
(1)自由行渐成主流,出现监管空白。在国内开放入境游初始阶段,旅游形式以旅行社组团为主。在近10年,自驾游、自助游等旅游形式日益广泛,传统跟团游的比例逐年下降。
(2)探险极限等危险性旅游活动兴起,风险控制状态难以把控。外国人来华从事无人区徒步、潜水、登山、探洞、漂流、蹦极、热气球、滑翔机驾驶等探险极限类旅游活动较多,有些活动本身的风险性较高,景区在实际运行中出于节约成本或者疏于维护导致旅游活动安全条件不足,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较大。
3 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问题
3.1 旅游部门牵总协调缺位,旅游监管信息不畅通
(1)旅游监管主体多,协调难度大。发生突发事件后,旅游经营者要承担旅游安全主体责任进行及时救助。相关的处置、指导、协调、监管工作还涉及大量机构,包括公安、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景区主管部门、旅游活动主办部门及外事部门等机构,此外还需要通知涉事国家驻华使馆或领事机构。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时,现场人员需要面临多种主体,很难厘清众多机构之间的管理职责,甚至可能出现多人负责反而无人负责的情况。
(2)对旅游经营者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监察不到位。旅游经营者承担突发事件处置主体责任,但实际监察情况并不乐观。以旅游景区为例,景区一般委托给企业经营,或者由政府成立景区管委会经营。景区的上级主管部门常出现委托管理的情况,很难掌握景区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更无从对导游等第三方进行延伸监管。
(3)旅游部门牵总协调缺位,旅游信息碎片化。旅游行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环节,旅游信息很难整合,信息孤岛多,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作为旅游市场的行业监管部门,文旅部门在旅游安全上的指导作用不明显,尤其是在旅游景区多主体安全监管现状中处于边缘位置,无法发挥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赋予的牵总协调作用。
此外,在自由行散客化背景下,旅游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领域仍然以旅行社覆盖的团体为主,对非团体游的游客安全缺乏监管,相关的游客信息无法及时准确收集,旅游安全和应急救助服务也无法有效提供。
3.2 旅游经营者应急准备不足
(1)危机意识普遍不强。相对国内游和出境游,入境游游客总数相对较低,发生伤亡事故的频数也较低,这导致旅游经营者的经验不足,危机意识也较低。
(2)预测预防漏洞较多。旅游经营者尤其是旅游景区企业,在安全投入上还存在不足,应急队伍不健全,监测预警设施不完备,安检能力有缺陷,应急引导系统不完善,容易留下风险隐患。
(3)应急预案缺少场景和具体规程。许多应急预案中只规定了总体流程,相关分类应急场景不清晰,缺少进一步的操作规程、应急指南编制,无法具体指导应急岗位进行实际操作。
(4)应急演练培训不足。涉外旅游突发事件处置部门和人员缺少针对性的应急管理培训,不熟悉相应的应急处置、外语交流、信息报告和新闻发布等环节,无法形成必要的涉外事件应急准备能力。
3.3 涉外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尺度难以把握
突发事件的宣传在舆情事件中的作用极大,封闭消息、夸大宣传甚至正常的报道都有可能造成社会舆情事件。
涉外事件处置一般秉持多做少说或者做了不说原则,常导致信息不能及时如实披露。突发事件信息流动呈现单向流动模式,进入公安或者外事部门后就很难向其他涉及单位和部门传递。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可能引发谣言,采取“捂、盖”等方式甚至会造成次生和衍生舆情事件,形成国际舆论的被动局面。在北京市一项调查中,中外籍人士普遍认为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透明”。
宣传中还存在不连贯问题,在事发初期发了通稿,而后的应急处置及善后情况都没有进行跟踪报道和主动宣传,也为谣言提供了孳生环境。
3.4 语言不通仍是突发事件处置中的最大困难
外国人除却国籍和社会风俗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语言,导致其可能忽略安全风险提示,从而进入高风险区域或从事高风险活动,增加了伤害事故的可能性。语言不通使得突发事件现场处置中出现很大的沟通问题,对外联络困难,救助处置人员也可能无法及时有效了解游客信息,不容易达成处置意见共识,影响处置效果,可能造成伤亡后果加大。
4 应对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对策
进一步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和入境游客旅游行为特点,不断加强旅游行业安全,构建旅游行政部门牵头的入境旅游全环节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入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1)加强旅游行政部门的牵总协调作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这是新时代应急管理的基本要求。要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在旅游行业建立“旅游牵总、企业主体,专业处置、行业主管”的应急管理体系。
旅游行业监管部门除了“指导”安全外,要逐渐担负起旅游全行业链条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牵总”角色,为旅游景区等旅游经营者提供安全和应急管理规划、统计、监管、应急处置等服务,承担起“旅游行业应急办”的角色。
处置涉外突发事件时,在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下,文旅部门牵头组织应急协调工作,并在发生重大事件或需驻外使领馆支持时向外事办公室报告。
(2)补足旅游景区涉外事件先期处置能力。旅游景区是处置涉外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处在先期处置第一线。要建立健全涉外突发事件专项预案,将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纳入定期培训演练,搭建完整的涉外事件应急处置流程,提升涉外沟通、应急、救助等应急能力。
(3)综合研判次生衍生风险,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研究涉外事件可能造成的次生和衍生风险,分析其可能对其他行业其他部门造成的影响,为跨领域跨行业风险防控提供依据。
宣传媒介方面,需要考虑宣传主体和宣传面。“政府公告”要及时发布,及时平息社会谣传。社会主流新闻媒体要发挥其宣传面大的优势,对大众进行广而告之。除常规新闻媒体外,还需要考虑微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工具,将这些网民获取信息的主流媒体形式基本覆盖到,尽量降低社会舆情事件发酵的可能性。
(4)利用大数据技术,填补散客管理信息空白。除常规的住宿实名登记措施外,采取实名预约、WiFi探针覆盖、手机定位、人脸识别、社交位置打卡等综合措施来解决散客的监管信息缺失问题,可有效支撑入境旅游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5 结论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容易受到国家安全环境以及重大安全事件的影响,涉外突发事件处置始终受到旅游景区和旅游安全监管部门的重视。目前,国内旅游安全环境仍然严峻,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关事件的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健全,需要加以改进。
(1)国内典型案例表明,涉外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存在多种问题,不仅造成直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常引发社会舆情事件,造成国家旅游安全形象的损失,进而导致入境游客人数下降。
(2)目前入境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健全,主要问题包括:监管主体多,协调难度大,旅游部门没有发挥牵总协调作用,监管信息不畅通;旅游经营者主体责任实施不到位、危机意识不强,应急准备不足;涉外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尺度难以把握,容易丢失宣传阵地引发舆情事件,此外,语言不通顽疾仍然存在。
(3)加强入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需要适应国家应急管理体系调整,进一步加强旅游行政部门的牵总协调作用,实现全环节应急管理;补足旅游景区涉外事件先期处置的能力建设;综合研判次生衍生风险,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散客管理。
考虑到入境旅游受害主体的特殊性和后果影响的敏感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入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深入探讨这种复合型突发事件的多主体、多专项和综合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