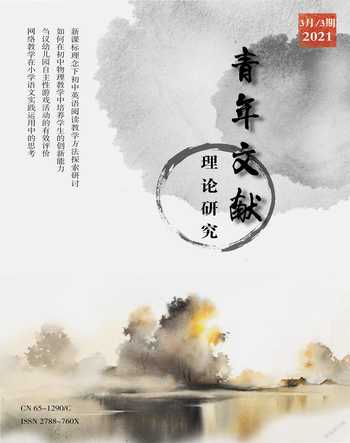生命困境下的自我救赎
【摘要】本文以柳宗元永州时期所作诗歌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诗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流动的情感意蕴,将永州时期的诗歌主题归为宦海沉浮下的不遇之诉、高山流水间的排忧之意以及苍茫天地间的佛理之机三大类,借此洞悉诗人的心灵世界,剖析诗歌的创作心理,以便明晰永州时期柳宗元诗歌的精神实质及其特有艺术成就。
【关键词】柳宗元;贬谪;山水;佛理
永贞元年,德宗李适病故,顺宗李诵即位,李诵任用心腹王叔文、王伾等人推行新政。柳宗元、刘禹锡因才华出众,在交游时深得二王赏识,借着后起之秀的光芒成为新政核心人物,当时一度出现“二王、刘、柳”的说法。宪宗即位后,二王集团的势力土崩瓦解,王叔文、王伾被贬,九月,柳宗元等七人贬为远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柳宗元等七人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永州司马。至此,柳宗元走入了一场生命的困境。在仕途最为辉煌的人生节点,却迎来了生命中最为惨重的打击,这种人生境遇的巨大落差,强烈地冲击着他的精神。他知晓自古人臣共同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已无法全部实现,转而便开始大量的创作文学作品,来实现三不朽中并非遥不可及的“立言”。仕途人生的困顿,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他的挣扎与无奈,孤高与抗争都寄托在文字中,表达在诗文里。在柳宗元坎坷的一生中,永贞革新是为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自此时起,“陈力希诸侯”的信念遭受重创,他转而投向自然,在山水间寻求澄心似静的寄托。
一、宦海沉浮下的不遇之诉
柳宗元的祖上在北朝时是著名的门阀士族,在当时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自己也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1可见柳氏门楣兴盛,家中多人曾为朝廷大官。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说:“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高祖讳楷,隋刺济、房、兰、廊四州。曾伯祖讳奭,字子燕,唐中书令。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祖讳从裕,沧州清池令。”2可见柳氏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作为世家大族的后代,柳宗元秉持着自己对于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之心,在永贞革新这场政治变革里践行着自己参政的心愿。
柳宗元早在《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一文中就提到诗歌“疏泄忧郁”的功用:“长吟哀歌,舒泄幽郁,因取笔以书。”3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是一首赠答诗,同时更是一首佳作,诗人借它诉说着自己如今受人钳制的“不自由”境况: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萧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4
这首小诗曾被列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从题目中可以知道是曹侍御在路过象县时作诗寄给柳宗元,这首诗是柳宗元的回诗。前两句写了曹侍御的生活环境,破额山前是美玉一般的江水缓缓流淌,而曹侍御本人则在“木兰舟”之上。诗人用“碧玉流”“木兰舟”这般美好的词汇刻画出友人清幽雅洁的生活环境,“春风无限萧湘意”一句,在春风潇湘的无限曼妙里诗人真正的“意”却又朦胧迷离,有待揣摩。但确定的是诗人接到友人来信时如沐春风的喜悦以及对友人的思念。最后一句点明诗人的心绪,方为此唱和诗的深层情感承载。“欲采蘋花不自由”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在春风和暖,百花竞开放的时光里,诗人却连“采蘋花”以亲近自然排解心绪的自由都没有,这一句的确是身陷困境后忧伤心绪的表达。全诗无一愁字,无一怨字,只说“欲采蘋花不自由”,但结合诗人被贬的遭遇以及遭受的诽谤,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诗人的由此而引发的万千愁绪。
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吕温卒。曾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吕温因赞同革新派主张被贬,而后死于贬所。当时身处朗州的刘禹锡作诗吊唁,柳宗元在永州也作诗《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进行哀悼: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罄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5
首联以奇峭突兀之笔写吕温的摧折带来的震撼,“天柱”一词的运用,既形象地显示出吕温生前顶天立地、高入云霄的奇伟风貌,又着意强调这一国之栋梁的逝世将使当朝受到巨大的损失,紧接着又用“士林憔悴泣相逢”传达出他的死讯给广大士人带来的巨大悲痛,柳宗元作为逐臣之一,在吕温的遭遇里看到的是同样不幸的自己。颔联是对吕温报国无门的现实深表遗憾,未能为国家中兴事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以及博得功名,只能深致悲慨以文章,像吕温这样一个志在使国家中兴的革新才人,徒有文章传世而未建功业,也像极了自己当下困苦不遇的处境,颈联转写吕温身后的凄凉,但也暗示出他生前的为官清廉并多执善政。尾联扣题内“兼寄”,借陈登的典故表达对吕温不幸摧折的痛惜。此诗借哭吊吕温,同时倾诉众人包括自己壮志未酬身遭贬的遗憾与不甘。
柳宗元还有一些寓言题材的诗歌,以曲折委婉的讽刺方式抒发不遇之诉。《行路难》三首,第一首取材于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的故事。革新派成员在革新后所遭受的摧残与力尽道渴死的夸父有相似之处,而诗中所讽刺的平庸无为却因寿而终的群体便是朝中保守派的缩影,足以见得柳宗元借此诗既有对革新派不公之命的控诉亦有对保守派苟且偷生的鄙夷。第二首写掌山林的官吏,砍伐林木却无以致用以至于搁置的林木被山火毁于一旦,最终只剩下“匠石狼顾相仇怨”。诗人将被搁置的良木用与被弃用的良臣相联系,既是对自我遭际的感伤,更是对专制制度肆意扼杀人才的批判,同時其中也不乏诗人对社会未来人才缺失的忧虑。第三首着重写了兽炭的命运。诗中对贵贱易位、世事无常的描写,不仅是写自己由人生顶峰到低谷的沉沦,更是对人生世事的体悟。这三首诗歌形象生动,对比鲜明,在强烈的讽刺中掺杂些许时运不济的无奈叹息。《笼鹰词》与《跂乌词》借动物的形象比拟困境中的自己,前者以苍鹰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比喻自己诗人在官场的盛衰之遇,诗末处苍鹰永不屈服的精神与昂扬的斗志又是柳宗元初次遭贬后豪情仍未灭的暗示,可见他依然胸有壮志,渴望朝廷的复用。
二、高山流水间的排忧之意
永贞元年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心中的忧闷无人可诉,而永州的荒山野水则成为他情感寄托的平台。柳宗元创作山水诗的初衷是借青山绿水的潋滟去排解仕途失意的幽怨,例如作于贬谪永州之初的《构法华寺西亭》。这首诗如同一篇小型游记,有缘起,有过程,有景致刻画,有情感抒发,而又浑然一体。诗人从贬谪写起,被贬南荒身世仓皇,却又猝然与本地险山恶水相遇,这奠定了本诗的基调。登高远望,发现法华寺西面景致甚佳,遂起游赏之兴。伐山开道,登上顶峰,建造西亭,仿佛身在云间一般。诗人对景致的描绘极见功力,如“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远眺山峦,如同齐聚亭前,澄江绕清湾而流,似乎相拥而抱;又如“菡萏溢嘉色,赏笞遗清斑”,荷花散发着悦目的色彩,赏笞挺拔,竹子上斑斑点点。面对如此景致,诗人感到精神舒展,情志惬意,暂忘了贬谪带来的苦闷。但这仅仅是短暂的欢愉,“离念”立马重新占据诗人的心胸,南瞻北望,既不能回归故里,又无法融入蛮夷之间。诗人不得不安慰自己,放下这些纷繁的念头,好好享受这片刻的悠闲。其余诗作中亦有这样的表达: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愿言怀名淄,东峰旦夕仰。始欣云雨霁,尤悦草木长。”6(《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7(《构法西寺西亭》)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遨游。”8(《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9(《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
“追游疑所爱,且复舒吾情。”10(《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曹。”11(《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当柳宗元失足于一场政治漩涡后,眼前的高山流水便成为他寄托情感的平台。他揣着漫漫长夜郁结的隐忧入于山林水木,望于山水中复舒吾情,这便是他对自然的态度,自然是人情感的归宿,只有在自然中或许才能找到吾心安处,在这份心安中收获了天与人的短暂交汇。
其实被贬前期的柳宗元,纵情山水不过是企图利用高山流水的开阔来驱遣内心的郁郁不得志,并非是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将注意力转入山水之间,是他强求宽解,排遣心境的一种手段。柳宗元初贬永州时,常驻心中的是被再次复用的期待,永州的山水于他来说不过是排遣心中不甘与愤懑的凭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自然山水作为畅情舒性的场所的这种功利性慢慢淡化了,取而代之的心态是以高山流水为真正的知音,例如《溪居》一诗。此时柳宗元筑室愚溪之畔,从诗题“溪居”来看,他所居之地该是清溪环绕,充满自然之趣,“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一句诗人说自己清晨在田间翻除杂草,傍晚便泛舟溪石,诗人想象的自我此刻与身旁的山水浑融一体,没有物欲世界里的烦恼掺杂其中,是诗人生活的客观展示,诗人深入山水间,在自然中觅得解脱,是这样的世外之境为诗人重建心灵秩序提供了多样化思路。
三、苍茫天地间的佛理之机
禅宗思想长期以来的耳濡目染,对柳宗元的贬斥心态与山水情怀同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类诗歌中柳宗元利用自己写景话物的高超技巧,在山水风物的变化中觅得禅意,了悟禅心。以《芙蓉亭》为例:“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由花的神秘变化自然联想到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如何这般匠心独运,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妙的风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此句是柳宗元参透玄机后的感悟,既然世事的本质已是万物归空,那自己何不沉醉在自然的美好中,将尘世繁杂抛掷脑后,尽情享受一花一世界里的安然。另有一些诗歌,从意境本身来说,便是禅境的再现,其中《渔翁》和《江雪》兩首最受世人推重。首先是《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12这首诗集中笔墨描写头天傍晚至第二天清晨的景象,渔翁夜宿西岩,有晨起炊饭,有烟销日出,还有棹船摇橹之声,这一幕幕的声、色、景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一幅绵长悠远之景。破晓之时尚能通过“燃
楚竹”寻到渔翁踪迹,日出之后却遍寻无迹,只有山水之间的一声“欸乃”才能隐隐约约窥见其形迹,这不是诗人刻意的追寻,而是自然无心的呈现,渔翁看似无迹可寻,实际上其迹就在自然之中,不须刻意索求。这与诗人那些带有浓厚贬谪色彩的山水诗不同,诗人没有用“以我观物”的方式,使自然山水“著我之色彩”,映照“我”的性情,而是“以物观物”,不仅作为主体的“我”有性,山水自然亦各自有性,所以能任自然山水的自然呈现,在诗中最后一句所说的“岩上
无心云相逐”,这是一种“无心”而成的状态。此诗中,他并未把外界世俗所致的郁结之思着色于山水,反而将寻常生活的描写变成了一首无色无相,潇然自得的心灵欢歌。
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江雪》,更是以禅入诗的力作: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13
柳宗元诗中的“千山鸟飞绝”,“绝”和“灭”是诗人主观感悟中的一个清寂世界,攘攘于外,静谧于心罢了。远去庙台,身处江湖,他有心一斩世间俗智,遁身物我两虚的佛空妙境,保持一方属于自己的偷悦和宁静。于是,便有了这空空茫茫的两句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诗的前两句巧妙组合,在一个空茫的世界里仍不乏灵动生机的痕迹。“蓑笠翁”是诗的主体,是诗的生气,使得空寂的自然之境顿时获得了生动。诗人以“独钓”一词,将一个桀骜执着的“蓑笠翁”跃然纸上,在精心营造的气象中又拓出一个了悟的世界,尽写了孜孜不倦于自我修养者的追求。在“独钓”的世界里,佛禅意趣与诗人上下求索的主体精神完美结合,孤高清傲的诗人存在于寂寥空茫的天地间,从而营造出独特的诗意境界。
在人生的上半场,柳宗元面对不公也曾有过不甘与失落,可他毕竟饱读诗书,具有达观的智识,在与山水作伴的过程中努力排除忧患之绪,同时借助于对佛理的深刻领悟不放弃执着济世的本心,这一切的挣扎与收获都寄托在永州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读者便可借此品味他凝聚了生命灵气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著.刘振鹏主编.柳宗元文集(第一册).辽宁:辽海出版社,2010:111.
2.柳宗元集校点组编:《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1.
3.[唐]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柳宗元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72.
作者简介:程曦,女,汉族,1997年生, 籍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硕士研究生在读 学校:陕西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