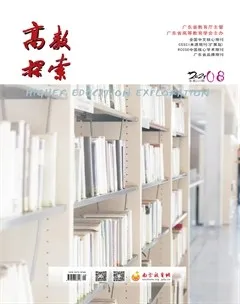英国一流大学的智库治理策略及其观照
张庆晓 王小元 黄炳超



摘 要:作为公认的英国一流大学智库,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在其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权责明晰的扁平式治理结构、透明多元的资金筹资渠道,注重学科协同的国际化议题研究,并建立了科学合理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和灵活多样的智库成果营销方式等。借鉴该智库的建设经验,我国一流大学智库应实施分类管理,构建大学智库的法人实体化运行结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拓宽大学智库的资金筹资渠道;推进智库、学科的融合发展,开拓国际化研究领域;重视人才培养,健全一流人才的培养机制;重视智库营销,建立智库成果的传播渠道。
关键词: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智库治理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2014年,教育部颁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下简称《推进计划》),要求从7个方面推进高校智库建设。201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除此外,2015年,教育部还出台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文件明确要求各地高校深刻认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意义,积极推进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由此,我国进入了全新的智库发展时代。据《全球智库报告》(2019)显示,我国拥有507家智库,6家高校智库上榜“2019全球最佳高校智库94强”,但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入围高校智库的前十。在我国,一流大学的智库建设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一流大学智库多属年轻智库,研究成果尚未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实质影响,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政策建议含金量不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不高。鉴于此,为了对我国一流大学智库建设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议,让一流大学智库更好地服务国家、政府及社会需要,我们有必要考察国外一流大学智库治理的现状,总结其先进经验,概括其特点,进而为我国一流大学智库治理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一、世界一流大学智库——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
英国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也是欧洲现代智库的发源地,大学智库是其国家智库体系的核心部分。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苏塞克斯大学世界排名為第146名,英国排名为第38位。根据英国2014年卓越研究框架的指标显示,苏塞克斯大学超过75%的研究活动被归类为世界领先或国际一流,属于英国一流大学。[1]据《全球智库报告》(2019)的分榜单“高校智库”排行榜显示,英国有3家高校智库进入前十,与美国高校智库占据前十位的数量相同,说明英国高校智库的实力不容小觑。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在世界“高校智库”排行榜的排名为第3位。[2]从已有文献资料来看,仅有4篇与苏塞克斯大学相关的文献,其中只有1989年的1篇文献是简单描述苏塞克斯发展研究院的[3]。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大学智库治理的典范,是值得学习、研究的对象。
苏塞克斯发展研究院与苏塞克斯大学联系密切,在了解发展研究院之前,有必要对苏塞克斯大学进行分析。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英国于20世纪60年开始兴建了一批“平板玻璃大学”(Plate Glass University),如苏塞克斯大学、约克大学、巴斯大学、肯特大学等,共计有10所。苏塞克斯大学成立于1961年,是第一所“平板玻璃大学”,该类型大学的显著特点是政府负担大学的运行经费,大学可自主决定课程设置和机构设置。苏塞克斯大学是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成绩斐然,并有7个学科位列全球前一百,分别是社会学(Sociology)、人类学(Anthropology)、政治学(Politics)、传播与媒体研究(Communication & Media Studies)、历史学(History)、英语语言文学(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地理学(Geography)。[4]
1966年,发展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成立,它以苏塞克斯大学为依托基地,集研究、教学、国际交流于一体,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但其管理和财政是完全独立的。“发展”一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事务密切联系,并且“发展”不只局限于一国的发展,更是将世界的发展也考虑进去。教育问题也是范畴之一。发展研究院的根本愿景是努力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和不公平,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安全、愉悦的生活,保证世界的平等性和可持续发展。其发展目标有四:(1)为减少不平等,加速可持续发展并建立包容性、安全的社会做出贡献;(2)在所做的所有工作中都融入卓越的追求;(3)在全球发展框架内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工作;(4)创建一个在财务和组织上都蒸蒸日上并实现其价值观的研究院。
从创建之初,研究院就坚持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坚信广泛的社会变革以及应对未来的挑战都需要前沿研究、可靠的证据及广博的知识。在阐述如何实现愿景时,研究院强调要加强与合作伙伴的沟通、合作,通过提供和动员高质量的研究和知识来指导政策和实践,并通过享誉全球的研究生学位,博士学位研究和专业发展服务来实现研究院的愿景和目标。目前,研究院有200余名员工和300多名学生,有310家合作伙伴和3300名校友,这些人员组成了庞大的组织网络。
二、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的治理策略
(一)权责明晰的扁平式治理结构
尽管英国的智库与政府部门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大学智库必须采用科层制的治理结构。相反,大学智库应采用适合自身活动特点、适合专业知识组织属性特点的扁平式治理结构。发轫于19世纪的的科层制,其典型特点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那样,“强调集权,重视指挥和各类规章制度,但封闭、僵化、效率低下的弊端已经使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转”。[5]如果将科层制治理方式强加给大学智库,必然会引发“专业—科层”的激烈矛盾,最终影响智库的治理效率。大学智库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莫过于各类人才,保障人才的生机和活力的最佳方式就是“专业自治”,因为“专业自治”最大程度的肯定了人才的异质性和竞争性。因此,大学智库的治理结构必须从科层制转向扁平式的治理结构。
董事会是发展研究院重要的治理机构。董事会成员不超过16人,其中包括苏塞克斯大学副校长(依职权)、主任(依职权)、研究院两名研究员、研究员一名员工(不包括研究员、荣誉研究员和访问研究员),成员多是由英国及海外人士组成的擅长研究政策的专家。目前,董事会成员为14人,董事会主席为乔纳森·基德(Jonathan Kydd)。按照规定,董事会每年举行3次会议,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为促进内部的沟通效率,董事会还下设4个小组委员会(如表1)。
每年举行两次会议,负责研究院的学生研究状况和表现,向董事会保证机制和制度有效地为研究、教学和知识活动提供保障,审议董事会在实现相关战略目标和关键主题方面的进展。
此外,发展研究院的日常工作室由主任及其领导的战略领导小组负责(Strategic Leadership Group)负责。战略领导小组是发展研究院的行政决策机构,负责机构的日常管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其小组成员是研究院的主要管理人员(如表2)。
综上可以看出,发展研究院实行的是“董事会+战略领导小组”的扁平式的组织治理结构(如图1所示)。该结构的特点是将专业知识团队视为扁平化组织内部组织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权力运行方式,减少管理的纵向层次,打破了组织原有的等级森严的界限,强化职能部门的横向沟通,充分释放知识、人才、资源等各要素的活力,最终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该组织模式可以根据实时研究需求及时整合资源,灵活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管理失误,在上述治理结构的影响下,研究院不仅解决了削减公共开支的要求,保障了员工的学术素养,也加强了学术人员之间的合作精神,使他们必须严格执行既定研究计划,保障研究质量。
(二)透明、多元的筹资渠道
智库作为人才与资本密集的组织,它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雄厚而多元的资金保障。根据发展研究院2018年度财务报告,发展研究院在这一年度中获得了2310万英镑的资金收入,与2017年度的资金收入持平。[6]发展研究院筹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政府资助、各类机构的资助、基金会资助及支持者的捐款。政府资助方面,在原英国外交部海外发展署基础上于1997年成立的英国国际发展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是發展研究院最大的政府资助部门,该部门是在一个部级机构,它的工作宗旨是积极应对当今时代的全球挑战,包括贫穷和疾病,大规模移徙,不安全和冲突等,并通过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全球减贫,促进可持续发展。[7]可以看出,英国国际发展部与发展研究院的工作目标有较大关联度,这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支撑。此外,各类机构资助的捐资也是发展研究院筹资的重要渠道之一。根据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5-2016年度占比最大的五个捐助者的数据,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ESRC)作为英国七大研究理事会之一,是发展研究院的第二大捐资机构。该理事会是英国领先的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培训机构,其大部分运行资金来自于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此外,联合国(UN)、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荷兰人道主义发展中国家合作研究院(HumanistischInstituutvoorOntwikkelingssamenwerking, Hivos)、国际粮食政策研究院(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等也为发展研究院提供了资金支持。基金会作为一种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对英国社会的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2019年度捐赠超过5000美金的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发展研究院争取到了诸多基金会的支持,如亚欧基金会(Asia Europe Foundation )、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等。此外,发展研究院的支持者也会进行个人捐赠,捐赠者可以直接在线捐款(包括一次性捐款和定期款款),也可以在网站下载捐款表格,将其与支票一起邮寄到筹款和发展办公室。研究院也特别欢迎个人的小额捐赠,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发展研究院影响力的扩大和受众的普及。
在英国,为了避免因捐赠者(机构)的捐资额度影响研究的中立性问题,大部分智库都制定了详细的捐资制度,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就规定每个企业捐赠者每年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8]发展研究院也不例外,对捐赠资金透明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接受(或拒绝)资助和捐赠的指标参数和原则,如研究院不接受完全匿名的资助(捐赠者在得到保密承诺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提供其身份信息);只有在资助道德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接受第三方提供的资金;要求充分披露潜在出资者与研究所工作人员之间的任何已知联系;通过注册获得学术奖学金的学生,必须接受学院的监督等。此外,发展研究院还规定,奖学基金(Scholarship Fund)的资助只能用于支持优秀的申请者在发展研究院学习。得益于发展研究院对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承诺,在对全球智库金融透明度的全球评级中,透明度(Transparify)组织①连续三年给发展研究院颁发了最高的五星透明度评级。
(三)学科协同的国际化议题研究思路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受历史传统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比较重视古典人文教育,呈现“重文轻理”的特点,学科结构严重失衡。20世纪80年代之后,受世界经济知识化、全球化的影响,英国政府开始转变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强化跨学科培养和综合教育,注重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9]苏塞克斯大学作为新大学的代表,在学科协同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教学上,它通过设置“学群”来安排课程。全校一共有两大一级学群:人文社会学学群和理工科学群,前者由亚非研究学群、欧洲研究学群、英美研究学群、社会学学群等4个二级学群;后者由生物科学学群、化学和分子科学学群、数学和物力科学学群、工程学和应用科学学群等4个二级学群(如图2所示)。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以“学系”为单位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接受较宽阔的、全面的教育。苏塞克斯大学前名誉校长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教授指出,所有苏塞克斯的学生通过比较、联系和判断,能够获得比传统的单科课程甚至双科课程要广阔得多的教育。[10]
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群”教学模式为开展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在科学研究上,为了解决单个研究人员无法解决综合性问题的难题,苏塞克斯大学利用其雄厚多元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积淀搭建了跨学科研究平台,并基于多学科交叉的性质确立了6大跨学科研究主题:全球化转变(Global Transformations)、文化与遗产(Culture and Heritage)、环境与健康(Environment and Health)、安全与社会正义(Security and Social Justice)、数字媒体与社交媒体(Digital and Social Media)、心理与大脑(Mind and Brain)。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需要不同研究团队协同努力,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助于解决重大国际问题。
近年来,在政府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诉求下,智库成为“循证决策”的重要载体,成为现代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节。然而影响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同质性学科共同体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政策的需要,难以支撑智库从事的复杂性研究,积极询证不同决策群体的知识互补和构建跨学科群体决策机制成为获取高质量咨询建议的必然选择。发展研究院充分借鉴了苏塞克斯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并根据研究内容确立了10个不同的研究集群:企业,市场与国家(Business, Markets and the State)、城市(Ctiy)、数字技术(Digital and Technology)、治理(Governance)、健康与卫生(Health and Nutrition)、知识,影响与政策(Knowledge, Impact and Policy)、参与,包容与社会变革(Participation, Inclusion and Social Change)、权力与大众政治(Power and Popular Politics)、资源政治与环境变化(Resourc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和农村未来(Rural Futures)(如表3所示)。研究集群都由研究院的领军人物主持,同时还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共同研讨,以期得出最优质的智库成果。
以企业、市场与国家的研究集群为例,该研究集群的日常研究议题集中于六个主题领域,分别是工作、企业发展、贸易、金融、替代经济和食品与营养,这对于经济体系实现包容性发展至关重要。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采用了如政治经济学、价值链分析和市场体系方法等多种学科理论观点,来分析企业活动,包括与国家的互动,对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重大影响,由此产生了新的研究证据,并填补了该领域的知识空白。该研究集群最新的研究发现,企业,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世界各地的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现实。正如最近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中所看到的那样,从疫情爆发中企业和市场如何相互塑造,以转型或回归形式进行重建的可能性取决于各州。例如,全球医疗用品争夺战暴露了市场力量的局限,政府和企业已经控制了跨国价值链。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被挤出供应链,社会将需要新的合作模式。除了研究集群的研发模式外,发展研究院还成立了若干研究中心来解决区域性、全球性问题,如商业和发展中心(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Centre)、发展影响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Impact)、新兴力量与全球发展中心(Centre fo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国际税收改革与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ax and Development)、社会&技术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途径中心(Socail,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athways to Sustainability Centre)、卫生学习中心(Health Learning Centre)、社会保护中心(Social Protection Centre)等。
发展研究院通过采用研究集群与研究中心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展开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坚持国际化发展思路,围绕重大国际化问题展开研究,致力于推动学术知识的落地,反过来提升了研究人員的国际化问题研究能力,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意见。
(四)科学合理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
尽管在大学智库排行榜中,人才培养绩效并未列入考量大学智库排名的指标[11],但高校智库的发展离不开高端智库人才的支撑,世界一流大学智库均是将人才培养作为智库发展的重要使命,并将其作为与大学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究其原因,与国外学者对高校智库功能的研究所遵循的“知识——政策”分析框架密不可分,他们将智库功能定义为“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并提供政策咨询”。如此,大学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具备成熟的知识体系和较为完备的智库系统下,培养熟悉政策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等高端智库人才,就成为智库不可缺少的功能。大学智库的人才培养功能也是与其他类型智库区别的重要所在。
自1966年成立以来,发展研究院一直致力于为学习者提供一流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环境,提供全球范围内保障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行动和领导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发展研究院设置了学位项目,覆盖了从学士到博士等类别的学生培养,并将博士研究生学习视为核心业务。目前,发展研究院可提供9门文学硕士课程和1个充满活力的博士学位项目。总体来看,尽管每年申请入学的人数很多,但因发展研究院所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是围绕智库的研究主题的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申请者必然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入学,研究院人才培养的规模必然是相对较少的,而这也是与世界著名大学智库的人才培养规模较小的现状基本一致。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美国家的博士生规模逐步扩大,然而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却没有相应提升,博士生教育受到了民众的激烈批评和质疑[12]。发展研究院非常重视博士生培养,坚持“质量”思维,将博士生看作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围绕“质量”主题精细化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在招生选拔、课程设置、导师选择、科研训练、指导方式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完善的制度。在招生选拔环节,发展研究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有意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有具体的要求,包括硕士学位的学科背景、在发展中国家或与发展有关的工作经验、语言技能、每个部分不低于65分的雅思考试成绩和读博的研究计划书等。同时,发展研究院认为除国外考察研究外,学生只有将大部分时间留在研究院,才符合研究院和学生的最佳利益,因此研究院不接受申请者远程学习申请。在课程设置上,考虑到博士生在培养期间需要到世界各地开展研究,发展研究院坚持了跨学科的课程设置思路,主要为博士生提供国际发展研究课程,如发展研究、公共政策、商业与发展、全球化、性别与发展等。这些课程与发展研究院的研究主题、研究计划密切有关,是开展主题研究的基础。博士课程的检测标准是课程论文和与之相关的论文答辩。在导师选择方面,发展研究院采取的是“双导师”制。博士生在申请博士学位之初,就必须确定首选导师,并和导师做好相应的联系与沟通。在第二导师的选择上,学生可以提前联系,也可等入学后按照研究院的分配即可。在科研训练方面,发展研究院根据博士生的培养类型,规定全日制博士生的学习时长必须为3—4年,在职的学生学习时长至少为6年。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需要在发展研究院社区举办两场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是在第一年年末的研究大纲研讨会,主要是汇报实地考察前的计划概述;第二场研讨会是在博士第三年的中期,重点讨论研究的中期成果,包括论文中的研究成果和总体论据。博士论文的总字数不能超过8万,包括脚注和参考书目,但不包括任何附录。此外,博士生与发展研究院社区关系密切,并创建了一系列平台用来展示研究成果。如举办年度的“发展研究院博士生日”,对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和苏塞克斯大学开放。“研究与方法咖啡角”由博士生自己组织,每周举办一次,供博士生交流学习方法、开展研讨会、辩论会和非正式会议等。目前,发展研究院有大约50名博士生在亚洲、非洲、巴尔干、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从事课题研究工作。大学智库培养的博士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履行了培养高端智库人才的重任,对大学、社会和学生来讲是“三赢”。对于大学智库而言,“再生产机制的出现,促进了智库领域的扩张,提升了它在大学中的自治权和自我认证能力。”[13]
(五)灵活多样的智库成果营销方式
不同社会阶层对政策决策有不同的影响力。加尔东根据社会各阶层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将社会结构分成三个层次,即决策核心层、中心层和边缘层。[14]
决策核心层主要指政界领导层,他们拥有绝对的国家赋予的决策权;决策中心层主要指的是拥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机构,如高校、企业、媒体等;决策边缘层指的是社会大众。一流大学智库作为决策中心层重在通过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来影响决策核心层,为决策层提供智力支持,并获得决策权一定的资金支持,减轻运行压力。发展研究院作为一流大学智库,主要通过出版物、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政策简报、学术活动等向政策决策者、社会大众、新闻媒体等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发展研究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双月刊)是发展研究院最重要的出版物,旨在通过其全球学习伙伴关系为学术、实践和政策话语建立发展问题的对话框架。在发行上,除常规的纸质版发行方式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全世界的研究者,发展研究院为《公报》建立了专门的网站,提供了豐富的学术研究资源,读者可以在线获取近半个世纪的《公报》目录。除此外,发展研究院的出版物体现了“发展”的特色,如近期发现经常用肥皂洗手对防止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传播至关重要。为此,研究人员出版了《低资源设置洗手指南》(Handwashing Compendium for Low Resource Settings),被称为“一份有生命的文件”。[15]发展研究院的研究者也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传播影响力的方式,他们经常在《能源研究与社会科学》、《政治地理》等刊物发表相关的学术成果。激烈的观念交锋和竞争是智库兴旺和发展的标志。通过举办和组织公开演讲、圆桌会议、小组讨论等学术活动,为决策层和专家学者提供交流讨论的平台是发展研究院增强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如发展研究院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重,为此将举办“中国与全球发展系列研讨会”,并将研讨会的主题设定为:(1)Covid-19大流行和反大流行措施如何重塑全球发展,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治理?(2)Covid-19大流行对非洲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中非合作和三边合作的经验教训是什么?(3)后Covid-19时代的国际发展合作前景如何?Covid-19大流行给中英合作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需要进行哪些更改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除上述营销方式外,发展研究院为了让社会大众(决策边缘层)了解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允许研究者开设自己独立的社交账号,并就国际、国内的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广泛的全球网络和通讯渠道,发展研究院建立了除官方网站外的Facebook、Twitter账号,定期发布研究院动态,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除理论成果外,发展研究院非常重视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践成果,这是强化徇证政策的重要部分。在应对埃博拉疫情危机时,发展研究院迅速汇集相关专家,动用所有的知识储备,通过有针对性的人道主义工作,帮助挽救了西非数千人的生命,并告知当地政府、慈善机构和社区为未来流行病的发展如何做好准备。2017年,发展研究院因有效地应对埃博拉疫情获得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杰出国际影响奖”。发展研究院还通过与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 BRAC)合作,帮助孟加拉国其制定了长期发展计划,其中包括BRAC针对极度贫困的计划,该计划已帮助75万人脱离极度贫困状态。[16]值得称赞的是,发展研究院的工作论文、研究报告、政策简报等都可以免费在线下载。
三、发展研究院的治理策略对我国一流大学智库治理的启发
(一)分类管理,构建大学智库的法人实体化运行结构
虽然发展研究院是以苏塞克斯大学为依托的机构,但它是独立建制的实体机构,在财务和管理上完全自主。在我国,绝大多数大学智库没有法人资格,甚至一些大学智库只是“挂牌”机构,只是为了拥有新型智库的品牌,最终成为了国家新型智库建设资源的“收割机”,不断获取相关研究项目。更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11工程”高校智库和处于成熟期的高校智库是治理结构缺损的“重灾区”[17]。如果大学智库是“非法人单位”属性,会造成其缺乏独立的财务权和人事权,受制于母体(高校)的各种限制和控制,这就形成了我国大学智库治理结构上的“国家—高校—智库”的“三明治瓶颈”。[18]这种治理结构会造成国家(省市)出台的智库政策无法及时辐射到大学智库,造成政策资源的滞后、浪费等。
为解决一流大学智库治理“三明治瓶颈”的问题,要实施分类管理,将大学智库分为非营利性大学智库和营利性大学智库,坚持实体化运行,并健全大学智库法人治理机制。非营利性大学智库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院)所长负责机构的整体运行,同时保障职工的民主参与权力,并接受党支部或所在党支部的监督。营利性大学智库则需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包括明确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之间的权责和利益安排,并制定智库章程,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此外,我国应借鉴英国对非营利智库的管理经验,建设税收审查机制。发展研究院在英国的注册身份是慈善机构和担保有限公司。在英国,根据是否享有免税优惠将非营利组织分为慈善组织和非慈善组织,所以发展研究院属于非营利慈善组织。捐赠者(机构)对非慈善营利组织的捐赠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然而,对非慈善机构的捐赠就不享受税收优惠。[19]尽管,在英国的非营利慈善组具有免税资格,但也要接受税务部门对机构常规活动的审查,如发现有从事营利性的活动,则免去该组织的免税资格。从本质看,营利或非营利并不影响智库的独立性,但经过税收审定被认认定为非营利组织大学智库则享有减免税待遇,而营利性智库则要按照《公司法》依法纳税。
(二)实事求是,拓宽大学智库的资金筹资渠道
对任何组织来说,充足的资源是保障其正常运转的关键。充裕的资金是大学智库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有研究者发现,智库的资金持有量与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智库的资金持有量越大,影响力越大。[20]因此,世界著名大学智库的掌舵人均是将筹集资金作为任上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充足的资金可以为智库的政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让研究者无须为了节省资金而放弃实地调研和简化研究程序,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发展研究院每年会派博士生到世界各地进行实地调研,并撰写基于实地调研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强大的资金筹措渠道,可以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如果智库的运行主要依赖单一资金来源,将会无法控制研究者和投资者、智库和政府之间的张力,就会产生“有奶便是娘”的窘迫局面。与发展研究院多元化的筹资渠道相比,我国一流大学智库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模式极大地束缚了智库的发展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智库专家质疑中国智库是为政府“背书”的机构的证据。因此,我们应借鉴发展研究院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和资金管理方式,增强大学智库的财力,继而增强大学智库的影响力。
在考虑我国一流大学智库的筹资渠道时,我们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考虑我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大学智库的运行规律。目前,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大学智库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是大学智库资金的重要来源,不可能“一刀切”的对所有大学智库进行“断奶”。因此,在目前的国情下,大学智库仍然要不断争取政府的财政拨款,保证自身能够正常运行,同时为了避免“资金的路径依赖”,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公正性等,还需要积极探索其他筹资渠道。大学智库可以通过输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来争取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等社会性资助,也可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大学智库还可充分利用大学的校友资源,接受校友的捐赠;同时,大学智库可成立独立的智库运行基金,由专业机构对基金进行管理、运作,不断提升基金的收益,用于支持智库的日常运行。此外,政府对智库的经营性活动也要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等。
(三)智库、学科融合发展,开拓国际化研究领域
大学智库的发展离不开智库与学科的良性的互动关系。为了构建兩者的良性生态,发展研究院在教学和科研中充分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此过程中,智库得益于跨学科的教科研方法提高了政策产品的质量,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不同学科在研究中又相互影响,提升了学科的整体实力。在我国,一流大学智库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大学一些既有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向智库转型,但这种基于“学术型研究中心”来培育智库的方式大部分都不太成功;二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多学科汇聚,形成综合性智库。[21]这种方式往往是推动“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重点研究基地向智库转型,但具体成效还要看能智库这一载体能否克服协同主体之间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利益分配难题。据研究发现,在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中,由单一学科门类组建的中心数量占比超过一半;由两个及以上学科门类组建的中心多数由理学和工学学科组建。[22]说明,政府在大学智库治理中出现了“学科交叉偏离”的问题,与智库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支持协同的活跃度较低。为了解决大学智库与学科“错位”发展的问题,我们需要秉承“融合式”发展的理念,一方面,政府要为智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让大学既要回归学术本源,也要发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促进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协调智库建设中不同主体的权责关系及利益分配,创新智库知识生产机制,重点是要建立传统学科评价与智库成果评价的“转换”机制,避免大学中盛行的科研“学科依赖”文化,导致智库与现有大学的成果评价体系、职称体系等的不兼容,出现“智库孤岛”问题。
发展研究院在创建之初,就一直将研究国际问题作为出发点,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政策议题。反观我国各类智库,尽管早在2015年出台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要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总体上,国内智库对国际或他国的“精确政策研究”较为缺乏,导致在关键国际事务决策方面反应的迟缓。目前,我国及发展中国家智库建设大多处于智库10时代的规模扩张发展期,但发达国家的智库建设已然进入了智库20时代,更加注重发挥智库的内涵建设。为了提升我国一流大学智库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充分利用一流大学学科齐全、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通过已有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加强与国家高端智库的项目交流;其次,国家应鼓励一流大学智库在国外设立研究分院,鼓励智库研究的“国际现场”;再次,政府应主动邀请一流大学智库积与外交活动,让大学智库熟悉本领域内的最前沿的国际政策动态,而不仅仅是获得“二手信息”;最后,一流大学智库要树立品牌意识,精准发力国际事务研究,主导国际性的政策研究网络。
(四)重视人才培养,健全一流人才的培养机制
发展研究院将培养高学历、跨领域的国际化人才作为重要任务,让培养的人才成为智库高端人才的中转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才的聚集效应。众所周知,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是其四大功能之一,大学内部的任何组织都要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运转。大学智库作为大学内部的组织之一,自然也要履行人才培养的责任,智库是人才培养功能的自然延伸。教育部在2014年印发的《推进计划》中也明确指出“高校智库应当发挥人才培养的重要功能”。虽然我国一流大学智库虽然也借鉴了英美大学智库的经验,但智库的人才培养功能还有待提升。分析原因,发现一些关于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存在严重误导,将智库人才的理解仅局限于智库专家、党政领导干部等,而没有把学生作为储备人才。因此,我国一流大学智库在发挥资政启民的同时,更要借助平台培养人才。大学智库培养的人才思维活跃,具有广阔的视野,能从国家层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去就现实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将服务社会和理论研究有机结合。首先,大学智库是大学高水平人才的聚集地,研究的是事关国家、行业发展的政策问题。这些高水平人才的周围不乏优秀的青年学子。所以,我们要改变思维,将智库人才的范围加以扩大,不仅包含智库专家,更包含高学历的学生群体;其次,在具体的学生培养过程中,智库应在教学、研究方面要多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让学生掌握政策研究的分析框架,还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了解政府、企业的运作理念,让专业知识和卓越学术有机会结合。学生在深度参与智库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提升了研究素养,培养了理性思维。最后,大学智库的人才培养形式要多元化,除学位项目外,还可以灵活开展一些短期智库的培训项目,方便在职人员的时间安排,如实习项目、冬季项目和暑期项目等。
(五)重视智库营销,建立智库成果的传播渠道
2014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和智库交往。智库外交已然成为国际交流的“第二轨道”,我国大学智库作为智库的主力军,在智库营销方面已然较为落后,智库成果的发布方式集中于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和研究报告,传播形式更是与当今“移动互联”的大背景不相符合,缺乏“互联网基因”。因此,我国一流大学智库必须借鉴发展研究院的经验,重视智库的营销,建立多渠道的成果传播渠道,提高智库的影响力。一是要建立多元化的成果发布渠道。除要继续发挥图书专著、期刊论文等传统传播媒介的作用外,高校智库必须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并及时更新网站内容,还要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载体传播研究成果,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扩大受众面,增强智库的影响力;二是要主动沟通,建立一流大学智库与国外智库的交流平台。如由中联部牵头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就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等一流大学的智库,目前该联盟已举办数次有影响力的圆桌会议、智库论坛,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权威性的建议。三是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促进大学、政府和社会在民生焦点、公共话题、社会热点问题上的良性互动,保障社会主体间达成共识性意见。
注释:
①Transparify提供了主要智库财务透明度的全球首个评级。2014年初,我们访问了40多个国家/地区的150多个智囊团的网站,以了解它们是否提供有关谁为其提供资金以及从每种来源获得多少的信息。
如无特殊说明,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的相关信息均来自于其官方网站的信息。
参考文献:
[1]Sussex.Rankings[EB/OL].(2020-07-03).https://www.sussex.ac.uk/about/facts/rankings.
[2]James G MaGann.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9[R].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9:207.
[3]侯琪山.苏塞克斯发展研究所[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3):80-96.
[4]Sussex.Research[EB/OL].(2020-07-03)https://www.sussex.ac.uk/research/about.
[5]珍妮特·V·登哈特登,等.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6.
[6]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Annual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2018[R].England: University of Sussex,2018:33.
[7]GOV.UK.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EB/OL].(2020-07-03).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8]戴慧.英国智库考察报告[J].中国发展观察,2014(1):34-38.
[9]高鹏飞.英国大学交叉学科建设:以苏塞克斯大学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13(12):116-119.
[10]李兴业.美英法日高校跨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探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4(5):71-75.
[11]James G McGann.2017 Global Go To ThinkTank Index Report[EB/OL].(2020-07-03).https:/ /repository.Upenn.edu/think _ tanks/13/? utm _source.
[12]Lovitts,B.E.& Nelson,C.The Hidden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Attrition from PhD.Programs[J].Academe,2000(6).
[13]Medvetz T.Hybrid Intellectuals: To Ward a Social Praxeology of US Think TankExperts [DB/OL].[2016-10-01]http://irle.berkeley.edu/culture/papers/Medvetz06.pdf.
[14]Abelson D E.From Policy Research toPolitical Advocac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olitics [ J].Canadian Reviewof American Studies, 1995, 25 (1): 93-126.
[15]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EB/OL].(2020-07-03).https://www.ids.ac.uk/publications/handwashing-compendium-for-low-resource-settings-a-living-document/.
[16]梁占軍.国外高校智库要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195.
[17]李韵婷,张日新.治理结构在资源投入和智库产出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基于125家高校智库数据的实证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0,14(1):98-105.
[18]李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新型智库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江苏高教,2019(10):35-40.
[19]刘继虎.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制度比较与借鉴[J].河北法学,2008(4):95-98.
[20]田山俊.论美国智库资金筹集与管理之道及其启示[J].高教探索,2017(7):62-67.
[21]詹姆斯·艾伦·史密斯.思想的掮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M].李刚,邹婧雅,赖雅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2]武建鑫.协同创新中心学科分布与单位组建机理研究:对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8):11-16.
(责任编辑 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