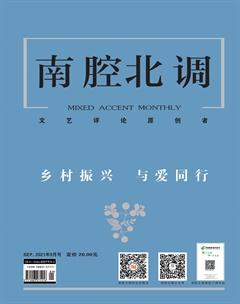多重叙述·历史审思·精神探求
姜汉西
摘要:《梁光正的光》借助于“灵光”消逝的父亲形象的多重叙述,勾勒出一个特定时代下充满矛盾性的行为主体,展开了对历史建构过程中叙述话语的思考。在不同的话语背后有着不同的情感基础和价值逻辑,导致了同一叙述对象在体认上的分歧和差异。在对这种分歧和差异的追踪、考察与研究中,作为具象化的个体成为了一个触点,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平面联接进一步强化,对历史、自我与他者之间内在关系的纵深探求,成为了小说文本最终的归宿点。作为父亲的梁光正身上具有较多的争议性,这种争议性也是这个世界的一种镜像和投射,重新正视梁光正,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新起点,也是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一个开端。
关键词:多重叙述 历史审思 精神探求 《梁光正的光》
在梁鸿的文学世界里,非虚构写作奠定了她创作的姿态和风格,也使得这样一位来自中原大地的女作家逐渐得到当代文坛的认可。除此之外,从她已经出版的作品来看,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等作品里慢慢串联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也是她写作的一个方向,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观察视角在个体、家庭、家族、村庄和国家等不同层面上发生的不断地转移,她并没有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梁庄”和“吴镇”等地,也不是简单地将个体从社会和历史中抽离,而是通过具体的乡村景观呈现,去展示整个乡土中国都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单行本的前言中就已经正式提了出来,“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1]《梁光正的光》在对乡土中国当代遭遇的探寻中有着更加具象化的目标导向,小说从一个普通的多子女共生家庭入手,将乡土世界里最为普通的一位农民父亲置于观照的中心,通过与父亲有过交集的不同个体的回忆和讲述,以及父亲自我的辩驳和言说,重点揭示不同话语之间存在的张力,内蕴着如何对待父亲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现实性拷问。同时,将梁光正一生的沉浮和乡土中国的变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个体的小历史和社会的大历史,来观察和思考个人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复杂性,体现出对社会中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以及环境如何影响着存在于其中的个体等具有永恒性命题的探求努力。梁鸿在对当代乡土小说的考察中,曾以“灵光”的消逝来对乡土小说的美学裂变进行描述,突出了世俗化乡土的普遍性,而《梁光正的光》中对混沌“梁庄”的进入,就是一种对“灵光”消逝后的乡土的重返与还原,内蕴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导向和审美追求。鉴于小说存在着两种版本(初刊本与初版本),且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诸多差异,尤其是初版本中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修正,在艺术上也更加成熟,因此在具体的论述中,所有的讨论所依据的版本都将以此为准。
一 .主体差异与历史叙述的分歧和张力
历史是对人类过去的经历和事物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记录、研究和阐释,求实求真是其最为本质的属性和特点,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历史作为一种被叙述的对象有着不可让渡的客观性与唯一性。这种客观性与唯一性也保证了历史本身的权威性,体现出后人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和敬畏,也是后世“以史为鉴”的重要参照和依据。可历史的叙述和传播是在不同主体甚至是在不同代际间进行的,尤其是历史的书写往往受到意识形态导向和历史叙述者个人的观念、立场和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历史的呈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史家的色彩,从而导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某种程度上的失真。当然也有人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地对话”等观点,我们无法否认诸如此类论断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观点的局限性,从当下出发去理解历史,其实是把历史工具化,在历史和当下的并置中没有做到必要的平衡,缺乏应有的理解与同情。历史一旦形成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历史客观性和唯一性的根本保障,但是在共识性的历史叙述形成之前,历史尽管存在但更多表现出一种驳杂状态,甚至带有一种未经打磨和淘洗的粗糙感,究其原因还在于叙述主体的差异性。《在梁光正的光》中,历史的叙述就呈现出多声部的典型特征,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对于那段历史,更具体说是对那段有父亲陪伴的家庭时光的独特记忆,他们的记忆建立在同一史实的基础之上,却有着不同的细节和样态,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巨大分歧,就是在这种分歧中,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对话和互动,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们的每一个都处于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2]在对照中,他们互相纠正了自己的偏见,找到了沟通的基础,建立了对话的平台,从纯粹孤立逐渐走向相对统一,并采用新的视角和立场,对历史中的父亲这一人物和他的一生进行审视与评判,于是开始了对父亲的理解和认同,父亲也从原来单一刻板的印象中挣脱出来,展现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一面。
在对父亲梁光正历史的叙述中,至少出现了三种声音,或者说有三类群体共同参与了梁光正历史形象的塑造,他的子女和他的生前好友是他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他们以在场和亲历的天然优势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对梁光正的叙述和评判也因为这种关系而平添了更多的信服力与真实感。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从叙述者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进行梁光正历史的叙述,这种叙述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天然优势,却容易在后天的加工中泯灭史实的客观性。除此之外,小说中梁光正也一直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着追踪和梳理,他的一次次寻亲和对往事的一遍遍重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提醒自己返回历史现场,通过对当事人的寻找来充实自己的生命空隙,最终实现对自我历史完整而清晰地表达。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为父亲的梁光正,在子女眼中与在他生前好友眼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甚至在性格特点和精神谱系上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对立,在这种不同和对立中就内蕴着意义的张力。他的子女无论是勇智还是冬雪、冬竹、冬玉,他们都曾经跟着父亲吃了太多的苦头,在人世间的各种冷暖中穿梭,但是一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在物質和精神层面上获得圆满。在他们的认知中,家庭和个体的不幸都与那个“事儿烦”的父亲有关,于是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那个“爱折腾”的父亲身上,并以此为耻,“父亲的名声已经败坏。父亲不务正业、不好好种庄稼,父亲好大喜功、惹是生非,父亲敢说敢骂、爱出风头,父亲冷嘲热讽、蔑视那些勤勤恳恳的人,父亲那件终年不变的白衬衫,都早已让人们看不惯。”[3]梁光正做生意搞投机倒把,发展种植业,确实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子女在身心上也都深受其害。然而那些和梁光正同处一个时空,面对同样处境,不折腾的人结果又怎样呢?梁光正与自我、与时代博弈,如果他不再折腾,那么他就不是梁光正了,而是与那些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一样和那个时代一起在历史的车轮下渐行渐远,直至最后销声匿迹。因此作为他者的叙述与梁光正自我的叙述之间是一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存在状态,他者的叙述正是梁光正的矛头所向,但是梁光正的自我叙述却不被重视,甚至受到了外力的压制。
梁光正的一生都在反抗压制,他性格中的不屈不挠和敢作敢当正是在不断地反抗中得到强化,凸显出一份难得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毅力。他在为人处世中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方法,他不会为了某一个目的而舍弃和背叛自己的信仰,因而被批斗、被打、与子女反目,这也成为了梁光正悲剧人生的强力注解,可这种悲剧更多是一种误解,是缺乏对梁光正内心世界深入观察的一种表现。他一次次失败的背后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困境的突围尝试,其目的是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摆脱贫穷对于他们的压迫和限制;他帮助别人打官司,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公平正义的渴求,他因此吃过苦头,对那个求助者的心理能够感同身受;他大量收购麦冬,也并不是为了吃独食,而是希望借此减轻乡亲们的损失。他的反抗压制,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生命价值实现,而是怀揣着更加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只是在更多时候,他对家人的义、对蛮子的爱和对朋友的情一直是处于潜藏状态,因此才招致了非议与责难,幸亏梁光正历史的叙述者呈现出多重主体性,多重主体就代表了多重声音和多种可能。在梁光正去世后,那些从四面八方来的陌生人终于走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叙述中,梁光正终于从失败者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且翻身成为英雄。当冬雪兄妹都以为父亲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的苦难时,父亲的死亡象征着一种苦难的超脱和仇恨的释然,但那些曾经得到梁光正帮助的人听到梁光正的死讯后闻讯赶来,在他们的哭声和言语中,没有“愤怒的成分”,是一种“伤心欲绝,是后悔没有早来看看这个人的悔恨,是多年不见已经淡了下去但又因其死亡而勾起的一些亲密感情”。当来自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的两种声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在对立和碰撞中,历史真相逐渐浮出地表,作为父亲的梁光正才真正完整和具体,因此才有了最终论断:“梁光正的世界,梁光正的儿女们知道得并不多。”[3]
二.在自我言说和重返现场中审思历史
梁光正的历史是丰富的,梁光正的形象是多元的,他的形象的多元性一方面依赖于子女和生前好友的集体性回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对自我历史的反复言说,也就是说,在梁光正的个人历史建构中,他自己不但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还有意识地参与了对自我的历史的修订。这种参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自我言说,以达到對历史细节的补充和修正,更多体现出对后世历史叙述的引导作用;另一种方式是在他的带领下,在历史现场的重返中和具体的人物、地点相遇,疏通历史的脉络,对自我的存在与生命轨迹进行追踪和确证。梁光正对自我历史的言说和对历史现场的重访,表面上看是对自己一辈子存在价值和生命轨迹的爬梳剔抉,其中内蕴着对自我的怀疑。他之所以反复讲述那段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往事,同时还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寻找过去的踪迹和影子,实际上就反映出一种个体历史的虚无感。小说中的梁光正时刻保持着与现实的距离,他敏感而又率性,在一次次反抗中始终以逆行者的身份出现,与时代的潮流背道而驰,因而在许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从社会轨道中滑落进尘埃的失足者,他明白真实的自己早已经被周围的环境所包围和浸染,失去了本真的面目和色彩,在识别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可是那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和那些确实出现过的人物是可以成为历史的素材的,也唯有他们可以证明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并不虚空,从中可以看出,梁光正的自我言说不仅有着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同时还有着对当代历史叙述的怀疑,自我言说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如杨庆祥所说:“梁光正不是一个失败者,他甚至有一种自觉意识,他自觉到他的故事必将沉入历史的深渊,所以,他一直不屈不挠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历史的层面来说,这种讲述是必要的;而就艺术的层面来说,他的讲述带有某种元叙事的意味,并直接拆解了当代史的合法性。”[4]可是梁光正的自我言说,在不断重复中,前因和后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同一件事往往有着不同的版本,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修饰痕迹,失去了对他人的说服力,相比之下,重返历史现场对梁光正个人历史的叙述则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小说《梁光正的光》中,寻亲是一个用浓墨重彩来写的情节,寻亲其实就是一种重返,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和仪式感。他的寻亲之旅是在65岁以后,当他意识到这种寻找的必要性时,尽管遭到了子女们集体反对,在旁人看来是一种近乎荒唐可笑的行为,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充满冒险性的征程,这是他性格使然,同时还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如他的子女所言:“只要父亲想做的,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他所要求的从来都是充满正义感的、关乎大是大非的、涉及根本善恶的事情。”从素未谋面的外婆和舅舅开始,“父亲寻亲寻上了瘾,寻完表叔寻表哥,寻完表哥寻表妹,几乎把郧阳、十堰、武汉几个城市和周边的村庄翻了个遍,又跑到广州和新疆去寻找那些搬到天边儿的亲戚。”[3]在寻完亲戚之后,父亲在寻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中心不断向外延扩展,他又开始去寻找早年帮助过他和勇智的那些人。梁光正的寻亲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对历史时空的重返,从大的方面来说则有着哲学的终极意义,即包含着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重大问题的追问和探寻。除此之外,与梁光正有着亲密关系的人也在寻亲中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父亲这里充当的是一个纽带的角色,有了他的存在,其他人才有被融进历史的可能,否则他们对于当下具有历史叙述话语权的人来说将会一直处于遮蔽的状态,成为历史当中不为人所注意的存在。“一路上说说笑笑,彼此打趣,一遍又一遍追问父亲少年时代的经历,还原奶奶和爷爷的形象。”[3]由爷爷和奶奶的形象,我们就可以对梁光正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有一个初步的想象,对他性格特征和精神谱系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就多了一份理解,这是贴近历史人物和进入历史现场的重要基础。
在梁光正不断寻亲的过程中,一个个人物和地点串联起了他的一生,不但完成了自我的生命追踪,也将自己的另一面展示了出来,如由卫娟所言:“父亲用各种手段将儿女们绑架成一个寻亲团队,表面上看,似是寻找亲人和恩人,其实是寻找一个叫做梁光正的个体的拼图碎片,以修补破碎的关系和自己。儿女对父亲完成了认识和理解,也让自己和生活达成了和解。”[5]梁光正在没有开始寻亲之前,他的存在因为频繁出走而从家人的视线中消失,几个重要的节点都成为了一段模糊的历史,这也直接造成了众人对梁光正的偏见,而最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的就是他自己,因此他的寻亲将自己从一个碎片化状态中逐渐完整起来,慢慢展示出一个更加全景化的自我,还原了一个生命个体原有的质感和层级。但无论是他的自我言说还是寻亲之旅,都已经不可能完全再现他经历过的欢乐与悲伤。一方面是物是人非的缘故,曾经的历史见证者已经在时间的流逝中和他产生了距离,不可能对话;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某些历史已经开始淡忘,这种淡忘也有可能是故意在遮蔽什么东西,因而在他的寻亲和言说中,作为子女的冬雪兄妹虽然对父亲的过去慢慢地表示出认同,可这种认同中也存在着怀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半认同的状态,如“那次寻亲,父亲经历了什么,勇智始终没搞清楚。父亲的版本太多难分真伪。……这些破碎的信息,经过几十年的磨损、遗忘、篡改和任意增删,早已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3]这里对历史信息真假的质疑,就涉及行为主体对历史叙述本身的审视和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而这也引导着我们对历史的叙述不能仅仅停留于叙事结构的平面逻辑,还要在纵深处探求世事的真谛,从时代环境里发掘生命的奥义。
三.从有限的真实中深入历史纵深处
历史的勾勒并非易事,无论是梁光正自己,还是他的子女和好友,在对梁光正的叙述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内在和外在等多种支配因素的影响,他们口中的梁光正并不完整,而是局限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进行“断章取义”的结果。这样一种对个人历史的肢解和拆分,势必会损害个体历史的有机统一性,在碎片化的叙述中对历史主体的全景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遮蔽,但这又是历史叙述中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历史的叙述上,在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叙述中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真实性中深入历史的纵深处就变得极为重要。国家、民族和个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国家和民族将自己的投影映射到个体身上,个体也只有在国家和民族的视域中才能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历史的深化探求中,有必要将社会大历史和个体的小历史结合起来,在互相关照中寻求异质性因素。除此之外,在梁光正的个人历史钩沉中,在有限的真实性中,对历史细节的重视和把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细节可以点亮一个形象、成就一个人物,因此要在历史细节中窥探出深层次的社会性与个人性内涵。在小说中吵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吵架本身就是一种对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有着精神景观、文化景观和社会景观的凸显,而这种凸显是一种嵌入式的,并没有直接从正面来写,在人物的命运和语言中,成为一种碎片,只有在所有人的共同叙述中才能拼凑出来,从而进入特定的情景、时代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如种植麦冬的失败,就是20世纪80年代乡村大破产的一种表现,在当时的乡村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数以万计的农民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因而对于梁光正的失败,我们就要从更深的社会历史层面加以关怀,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的影响,而不是将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他的自大和盲目。从这种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变故中,我们发现了历史的残酷性,以及个体的渺小和卑微,对梁光正这样一个父亲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就会生发出更多的理解与同情。
在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比照中,个人史是微缩了的社会史,社会史成为了放大的个人史,虽然两者之间并非具有永远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但这是一种深化历史认知和探求历史真相的一条可行的路径。在历史细节中对历史主体的言行举止进行考察,从更微小的层面去透视和提炼宏大的历史,需要更加谨慎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也能从一个侧面对历史的发生作出相对精确的史实还原和价值判断。但对于因主体差异而带来的一个碎片化的历史叙述状态来说,如果能在众声喧哗中找到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或者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小说中的冬竹就是故事中历史线索的收集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在一家人为了一些琐事而喋喋不休争吵时,她如同一个置身事外的记录者,对这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进行观察,并借助于过去的信件和日记等打开了那些尘封的历史记忆,如她所言:“我就像一个侦探。身边堆满信件、日记、纸片和乱七八糟的物件,冬竹一封封一本本一片片研究,拼接出时间、情节、故事和秘密。她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的伤心和怨恨,看到埋藏很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爱”,冬竹对于“时间、情节、故事和秘密”的拼接,就是在试图破译出历史的真相,除此之外,“冬竹喜欢听大家讲过去的事情,打牌时,开心笑时,她总是小心翼翼打听一些过去的事情。她想把过去的日子拼起来,想拼出一个图案,看看那图的形状、走势和发展逻辑,她想弄明白,是什么样的逻辑造成了今天这样子。她也想拼出妈的图形,她羡慕父亲和冬雪谈起妈来那意味深长的对视,那里面藏有妈,藏有这个家,她也想进去。”[3]冬竹对于历史的这种求索,包含着对静态、有固定结论的历史叙述的批判,这种批判最终指向的就是对深层次历史的发现。但她依然没有走进历史的深处,“梁光正是丰满而复杂的,他的生命中不仅有浮在表面的‘光,更有深入骨髓的‘伤。不仅‘他的儿女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他的世界,我们要真正深入地走进他的内心也一样需要时间考验和生命的体验。”[6]
对于历史的认识和探索是没有止境的,而文学的根本任务也不在于对历史真实的追溯,文学能够提供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思考和个体在历史中的面貌。梁光正是一个被塑造的具象个体,他的敢作敢为和惹是生非的背后有无数个父辈的影子,在众多的评论中包括梁鸿自己也都一直在强调为“我们的父亲”这样一代人树碑立传的写作意图,这种意图其实从梁鸿最开始的“梁庄系列”中就已经露出一些端倪,如那个争强好斗和“爱管闲事”的农民父亲梁光正、瘫痪八年遭受身体和精神双重苦难的母親、还有那个作为家里主心骨和主事人的大姐等,他们已经成为作者笔下具有经典性的人物形象,在不同的文本和故事中,他们的形象不断地得到完善和补充,因为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虚构的小说,两者在内容上有着极强的互文性。在《中国在梁庄》中“被围困的乡村政治”一章中开篇第一节:“梁光正:我没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我的麻烦。”这里的父亲依然是一个不安分的农民,以“破坏者”和“批斗对象”的身份参与了当时的政治,同时也一手造就了整个家庭的受难史,可是梁光正身上的缺点已经得到了修饰,他的好斗和“爱管闲事”也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和象征性,“他的身上绽放出中国乡村内在的欢腾和生命力,这是无待外部赋予的。”[7]作为父亲的梁光正,更像一面多棱镜,正是通过他每个人都看清了自我,当大家把苦难都归罪于梁光正爱管闲事上时,其实,他们也深知这只是一个自我开脱的幌子,如果父亲勤勤恳恳务农,依然无法将这个家庭从泥淖中脱离出去。困难的生活使得他们的怨恨在不断累积,可是又无法找到发泄的出口,在对父亲的有意误读中,他们实现了自我心理的平衡。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敢面对现实,缺乏反抗生活与命运的勇气,而父亲在这一点上要远胜于他们,正是通过父亲,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懦弱和无力。“一个家庭的破产并不只是一家人的悲剧,一个人的倔强远非只是个人事件,它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所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3]这是一种对族群未来的忧思。
结语
梁鸿是一个不断在跨越中找寻方法和道路的作家,当她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出现而为人所知,并且引发了学界关于虚构/非虚构的讨论热潮后,她并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而是以非虚构的方式继续着她的梁庄书写,“梁鸿跨越了文类的边界,文本的体积也在增大。无疑,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写作并不始于梁鸿,梁鸿和许多有才华的写作者一样,显示了她多方面的才华和可能。”[8]在梁鸿的笔下,梁光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的历史在新时代语境中却被激活了,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打量梁光正时,梁光正已经从过去那个“事儿烦”和“调解大师”的角色中跳脱出来,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的魔幻感和传奇性的时代英雄,可是他的步调并没有与那个时代保持同步,在很多时候都是以逆潮流的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在走向英雄和成为英雄这条路上他是一个不被理解的独行侠,而最终对英雄的追认与肯定也是在他死后才完成的。梁光正是孤独的,是不被理解的,是“灵光”消逝的老者,他的丰富性和创造力曾经被展现得酣畅淋漓,可那都已经渐渐失去了“重返”的可能,因而在不同的叙述主体那里,梁光正有着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精神谱系,建构在多重形象基础之上的梁光正是對历史讲述者的反讽。梁光正的历史是大历史背景下的小历史,他的小历史与社会的大历史之间在一种背离主流方向上渐行渐远,丧失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可能,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中自然会被排斥在选择的范围之外。然而这并没有彻底遮蔽掉梁光正在本书中的光芒,历史细节和历史线索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历史史实的渠道和途径,因此,梁光正成为一种生命力的象征,而他也成为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传承中的最具精神性和力量性的一群人。
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与质量提升计划项目资助(SYL20060115)
参考文献:
[1]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
[2][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86.
[3]梁鸿.梁光正的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06,293,11-18,98,165-189,315.
[4]杨庆祥.梁鸿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追逐历史的背影[N].文艺报,2017-11-29(3).
[5]由卫娟.梁鸿:致我们互相错待的亲人[J].齐鲁周刊,2017(48):58-60.
[6]徐洪军.版本的修改与创伤的书写——从《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到《梁光正的光》[J].小说评论,2018(2):187-194.
[7]金理.在“文学父亲”的巨大谱系中,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个“父亲”[N].文汇报,2017-12-22(10).
[8]王尧.关于梁鸿的阅读札记[J].扬子江评论,2018(1):29-33.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