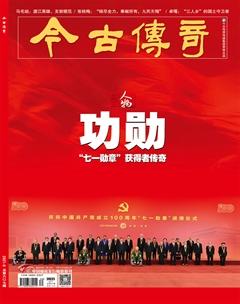魏德友“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
中哈边境上“永不移动的活界碑”他的家被称为边防站的“夫妻哨所”“我要一直守下去,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
魏德友(1940- ),汉族,山东沂水人,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退休职工。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等称号。2021年6月29日荣获“七一勋章”。
一根牧鞭,一架望远镜,一台收音机,每天陪伴着魏德友走在巡逻路上,萨尔布拉克草原100多平方公里山川上的每一株蒿草都记得魏德友的脚步声,每一块石头上都印上了魏德友的身影。57年来,魏德友倾力做好一件事——为国守边防。他用实际行动铸成了中哈(哈萨克斯坦)边境上“永不移动的活界碑”。
“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
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授勋仪式中,最后一位走上授勋台的是魏德友。魏德友说:“在颁授现场,当总书记握着我的手时,由于激动和紧张,我说不出话来。除了激动,也感到惭愧,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但我感觉我没有做多大的事,也没有作出多么大的贡献,就是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事。”质朴而简洁的话语,道出的是拳拳爱国之情。
1964年,魏德友与30多名北京军区集体转业军人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兵2连。当时的连长张万台说的话,魏德友到现在都还记得:“1962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边民在‘有边无防的状态下,裹挟牛羊,从咱们这一带逃往苏联。兵团派武装民兵第一时间在此地建立哨所、执勤点。我们新组建的兵2连,来到这里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就是为屯垦戍边而来,要用‘南泥湾精神创建新家园。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
据魏德友回忆:
1964年,24岁的我在北京军区当兵,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兵团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我是山东人,那时候没见过世面,甚至不知道新疆原來那么远。但作为军人,听党指挥,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哪里艰苦到哪里去。
到新疆之后,我们就在萨尔布拉克,条件很艰苦。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人工开荒,砍土锄地,用水也要人工打井、挖水渠。住的地方在“地窝子”里。就跟我老家山东的菜窖一样,在山坡上挖个坑,用烂木头和草往上一盖,然后埋上土弄个小门,一米二高的小门向外开,就是住的地方了。
1967年,魏德友从山东老家把刘京好接到新疆结婚成家。
从此,“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成了魏德友夫妇日常生活的写照。每次巡逻前,魏德友都会将院子里的国旗高高升起,傍晚回来,看到国旗就看到了家。
魏德友与兵2连的战友们一起每天放牧巡逻,一起在辖区西巴里坤、萨尔布拉克、额敏河南畔构筑了长达20公里,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领土。据魏德友回忆:
过去,戍边条件非常艰苦,饮水主要以河水、高山融雪为主。晚上站岗放哨,时不时传来狼叫,有时还能看见冒着绿光的眼睛,挺吓人的。原来草原狼多,狼群要是冲进羊群里去,这群羊就危险了。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草有一两米高,要是狼把羊吃了,放羊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就拿着望远镜到处看,发现狼就喊。一到冬季,大雪封山,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让身上的棉衣仿佛成了薄纸……
我家西边4公里是边境线,向北是边防站。马、骆驼、牛,经常会越界,靠近边境线的时候,就要赶过来。巡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牧民会靠近边界线,这时候就要提醒、劝阻他们别越界,跟他们解释说“边境无小事”。每天去放羊巡边,出门的时候,我们带着望远镜、收音机、水壶、馍馍。那里春天天短,早上7时左右就出去了,天长的时候,晚上11时点太阳落山时才回家,中间一般不回家。我们顺着边境线,向南或者向北,一天最少走15公里。
“请你当护边员,行不行?”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
魏德友和战友们时刻坚守着捍卫国家领土的使命,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绝不后退。魏德友神色凝重地回忆说:“1969年,边境事件频发。我参加了161团‘铁牛队行动,在塔斯提河南岸紧握钢枪与苏军对峙了三天三夜。在萨尔布拉克巡逻,不时与苏军擦肩而过,时时都能闻到火药味。161团就是以这种方式冲在边境争议区最前沿。”
那个时期,边防斗争最激烈、最危险的工作要数放牧。魏德友请缨到萨尔布拉克担任牛群组组长,拖儿带女地住进了萨尔布拉克小溪旁的半地窝子里。“搬来的那年,大女儿不足三岁,儿子还在吃奶,我央求他说,萨尔布拉克冬天封路,雨天道路泥泞湿滑,孩子又太小了,能不能不去?可他一口回绝说,不行!这事没商量!实在不行你留在连队,我一个人去!”刘京好回忆。
1973年的一天,魏德友骑马巡查,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发现两串通向境内的脚印,魏德友立刻向连队汇报。经过地毯式搜索,终于发现可疑人员,并将其劝退到边境线外。魏德友的胆大心细赢得连队官兵一致称赞。1983年6月,魏德友光荣入党,还被9师党委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1981年兵团恢复建制以后,兵2连所属地归裕民县管辖。由此,兵2连百余户人家分批陆续撤离了屯垦戍边20年的家园。1984年,161团牛群被拍卖,魏德友也要从兵2连搬迁至别的连队工作了。他却出乎意料地选择停薪留职,买了牛羊,在全团率先发展养殖业。说到底,他就是不愿离开兵2连。
时任辖区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魏德友说:“老战友,你既然决定不走了,我想把用于改善战士生活的羊群交给你。还有,牧民搬走后这里成了荒凉的无人区,即便是牧民搬回来,牛马羊在没有边境设施的状况下易造成涉外事件。你有戍边经验,请你当护边员,行不行?”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白松给魏德友配发了“义务护边员”袖章和一架望远镜。
兵2连戍守的边防线上,到处都留下了魏德友放牧巡逻的足迹。
魏德友在放牧巡边中,几次差点丢掉性命,其中一次发生在1987年冬天。
那天,魏德友像平时一样在黄昏时分出去巡边。他骑着马绕完一圈准备回的时候,突然刮起了暴风雪,嘶吼的风刮得他睁不开眼,大雪漫天,一会儿就淹没了牧道。走走歇歇5个小时,汗水浸透的衣服冻成了冰。已经筋疲力尽的他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前方亮起几道白光。“是手电筒!”他赶紧打开自己的手电,使劲地摇。远处的人影渐渐地清晰起来——是边防连的战士!魏德友逃过了一劫。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地方,魏德友依然坚守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努力做一个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人”
魏德友为边防站放牧多年,没有要一分钱的放牧费。边防站官兵为魏德友家盖了一幢新土房,这里也被官兵称之为边防站的“夫妻哨所”。
更让人感慨的是,兵2连原来的党支部早在1984年被撤并,而魏德友几十年里没落下一分钱党费,有时托人代缴,有时亲自到30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纳。过不上组织生活,他就到边防站与年轻战士们一起学习,更多的是从收音机里聆听党的声音。他说:“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努力做一个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人。”
魏德友至今住土屋,吃的米面需要女儿穿越几十公里牧道送进来,喝的是井里打出的连牲畜都不爱喝的苦咸水。平时一顿饭,节俭惯了的老两口就着一盘蔬菜啃馍馍。放牧巡边时,馍馍掰开塞点菜就是一天的伙食。
魏德友的手在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拔出来后10个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艰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从未让魏德友退缩过。“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这个信念一直植根在这名老党员的心里。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一台黑色收音机。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魏德友来说,收音机是他的另一个“老婆”——“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从1964年至今,魏德友用坏了50台收音机。
“我要一直守下去,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
魏德友育有一儿三女。在他们眼中,父亲很少进城,一刻都不愿离开草原。
2002年,魏德友夫妇退休,在山东工作的四兄妹力劝父母回乡养老,但魏德友就是不肯,还说服老伴留下来。子女在临近的裕民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想让二老住进去。可魏德友夫妇至今都没在那个房子住过一晚。
2003年仲夏,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界桩、围欄、国防公路等设施建成,兵2连人曾舍身捍卫的争议地界尘埃落定。魏德友成为兵2连唯一见证这一庄严时刻的人。他激动地抚摸着中国第173号界碑,流下了泪水。
巡边这么多年,魏德友只在2017年回了一趟老家,他说:“我特别对不起爸妈……爸妈都是2月份去世的,我接到电报是四五月份了。”
从英俊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吆喝着羊群孤身坚守,至今已有57年。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义务巡边20万多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从未发生一起涉外矛盾。
而今,81岁的他仍住土屋、喝咸水、啃冷馍、守寂寞,与星月羊犬为伴,与风雪饿狼较量。他说:“我要一直守下去,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
2017年,在父亲的感召下,二女儿魏萍辞去在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当了一名护边员。魏萍说:“我要向父亲学习,继续发扬兵团精神,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兰馨、陈小婷 来源/《“活界碑”魏德友: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高健华、梁晨、郝超/文,《中国国防报》2021年7月12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