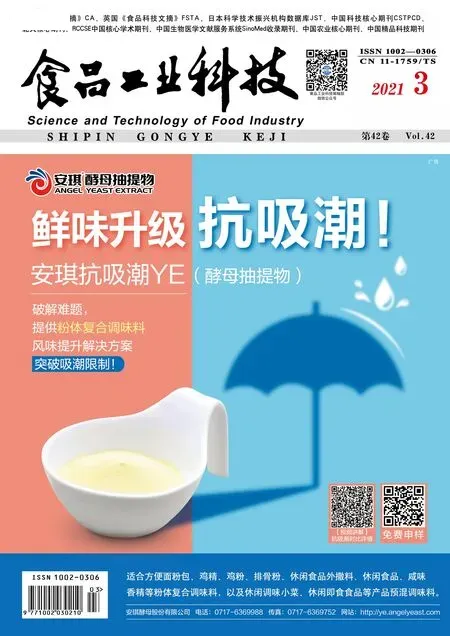茶树精油抗微生物作用机理研究进展
程 峰,尚若锋,杨 珍,梁剑平,郝宝成,王学红,郭文柱,刘 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兽用药物创制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新兽药工程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 730050)
近年来,消费者对于天然产物的兴趣日益增加,精油(EO)作为人工添加剂或药理学相关制剂的替代品,在生物医学、制药,化妆品、食品、农业等领域的应用得到了极大的普及[1]。截止到目前,研究人员已经鉴定了3000多种精油,但是只有300多个样品得以应用[2]。
茶树精油(tea tree oil,TTO)是从澳大利亚的桃金娘科互叶白千层的新鲜枝叶中以水蒸馏的方式提取出来的一种无色至淡黄色液体,具有尖锐的樟脑气味和薄荷醇的清凉感[3],在香料、农业、食品工业以及化妆品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茶树精油是由100多种化学物质所组成的混合物,主要是由单萜,倍半萜烯及醇类等所组成[4],具有六种化学类型,分别是萜品油烯化学型、松油烯-4-醇化学型和四种1,8-桉叶素化学型[5]。由于1,8-桉叶素的副作用较多,在实际应用中多选用松油烯-4-醇化学型。目前,茶树精油作为杀菌剂、防腐剂等广泛的应用于食品、医药和化妆品等领域,本文总结了茶树精油的抗微生物作用及部分机理,旨在为茶树精油在食品保鲜以及医药行业中“减抗替抗”提供理论依据。
1 茶树精油的成分以及含量范围
茶树精油的相对密度为0.885~0.906,微溶于水,可与非极性溶剂混溶。其主要成分是由单萜(对伞花烃,松油烯-4-醇,萜品油烯,1,8-桉叶素,α-pine烯,γ-萜品烯),倍半萜烯及醇类(单萜醇)等组成,Brophy等[4]开创性的通过气相色谱和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了800多个TTO样品,并给出了大约100种成分及其浓度范围。ISO 4730-2017中规定了松油烯-4-醇化学型的茶树精油中的14种特征性组分的含量范围(表1)[6]。

表1 茶树精油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量范围Table 1 The main contents of TTO
2 茶树精油的抗菌活性及抗菌作用机制
2.1 茶树精油的抗菌活性
茶树精油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北部Bundjalung原住民将茶树叶子打碎,吸入其碎叶以治疗感冒和咳嗽,或者将碎叶撒在伤口上,敷在伤口表面[7]。Penfold[8]最早测定了茶树精油及其主要成分的抑菌活性并和苯酚的抑菌活性做了对比。茶树精油对一些常见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及最小杀菌浓度(MBC)如表2所示。数据表明茶树精油对大多数细菌的MIC值在0.1%以下,并且多数细菌的MIC值与MBC值相当,这说明茶树精油对大多数细菌起杀菌作用,但对于部分细菌在低浓度情况下只起抑菌作用。

表2 部分细菌对茶树精油的药敏数据Table 2 The susceptibility data for bacteria tested to TTO
近年来,随着细菌耐药性日趋严重,植物精油由于其独抗菌谱广、毒副作用小而进入了研究人员的视野,Walsh[18]首先提出茶树精油具有杀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潜力,和化学药物相比,茶树精油的成分更为复杂;Carson[19]通过实验证明了茶树精油及其主要成分松油烯-4-醇不会影响细菌的耐药性以及不会使细菌产生新的耐药性[20],在延缓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茶树精油作为一种广谱、低毒、性能优异并具有一定芳香气味的抗菌剂,对于控制医院获得性感染和在家庭卫生消毒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2.2 茶树精油的抗菌作用机制
从茶树精油大部分成分的亲脂性中可以推测出茶树精油的抗菌机理可能是破坏细胞膜的生物功能,而Cox等[21]的茶树精油可以渗透脂质体系统的数据也支持这个观点。目前大多数研究也都集中在茶树精油对细菌细胞膜的影响上,具体表现为在形态学上,细菌细胞膜以及生物膜被破坏[22],在功能上表现为钾离子外流[23],碘化丙啶(PI)摄入增加[24],培养液中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加[24],DNA、RNA以及其它大分子物质的渗出[25]。Ce等[26]发现暴露于茶树精油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大肠杆菌的细胞膜发生严重损伤,使用碘化丙啶染色后发现暴露于茶树精油的细菌的细胞膜损伤可以达到95%以上,同时钾离子的外流增加也抑制了细菌的呼吸作用,进一步促进了细菌的死亡。扫描电镜拍照也观察到了大肠杆菌菌体的溶解与对细胞表面电子致密物质的破坏[22]。以上结果均证明了茶树精油通过破坏细菌膜的结构和功能完整性导致细菌的死亡。
细菌生物被膜(BF)是一种自我合成、表面附着的细胞群[27],可以显著增强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并促进其逃脱机体免疫。茶树精油可以有效破坏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生物膜,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可清晰观察到所引起的生物膜损伤[12]。松油烯-4-醇处理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可发生类似的生物膜损伤现象。多糖胞间粘附素(PIA)是细菌形成生物膜的关键物质之一[28],相关研究指出,金黄色葡萄球菌经茶树精油处理后,SarA和icaADBC基因均显著下调[12],SarA基因可以促进icaADBC基因的表达,进一步促进PIA的形成;同时,与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途径相关的11个基因的表达也显著上调,丝氨酸与苏氨酸的代谢可以产生更多的纤溶蛋白,从而防止细菌粘附在表面,破坏生物膜基质的结构,导致细菌释放及死亡。以上研究表明茶树精油可以通过破坏细菌的生物膜起到杀菌作用。
茶树精油对细菌毒素也有一定的影响,Liu等[29]发现茶树精油可以抑制李斯特杆菌的毒素,并进一步验证了茶树精油通过抑制李斯特杆菌溶血素O(LLO)的p60蛋白的分泌和相关基因Hly以及IAP的表达,并有效抑制李斯特菌刺激的巨噬细胞激活的NLRP3炎症途径蛋白的表达。
茶树精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抑制以及杀灭细菌,并对生物膜中和浮游的细菌均表现出良好的抑菌活性,可以有效地降低细菌耐药性的发展。目前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不是特别透彻,尤其是茶树精油中各种单体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 茶树精油的抗真菌活性及其作用机制
3.1 茶树精油的抗真菌活性
茶树精油具有良好的抗真菌活性,并且在阴道念珠菌的治疗[30]和果蔬保鲜[31]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有研究数据表明茶树精油对酵母菌[32]和某些丝状真菌[33]较为敏感,从表3可以看出,茶树精油对大多数真菌的MIC(最小抑真菌浓度)值在0.12%~0.2%之间。Oliva等[34]测定了茶树精油、5-氟胞嘧啶和两性霉素B的抗真菌活性,发现茶树精油的抗真菌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其他两种。但是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在对化学试剂不敏感的分生孢子上,Hammer[32]比较了萌发前后的黑曲霉分生孢子对茶树精油敏感性,发现萌发的比未萌发的更敏感。这一结果表明,完整的分生孢子壁对真菌有强大的保护作用。Rocha等[35]证明0.25%的茶树精油水蒸气也能明显的抑制扩张青霉分生孢子的萌发。

表3 部分真菌对茶树精油的药敏数据Table 3 The susceptibility data for fungal tested to TTO
3.2 茶树精油的抗真菌作用机制
3.2.1 茶树精油对真菌细胞膜的破坏 茶树精油对真菌作用机制与细菌相类似,也是通过改变真菌细胞膜的通透性进而起到对真菌的抑制作用。Hammer等[38]用0.016%~0.06%(v/v)茶树精油培养白色念珠菌24 h后发现细胞膜的流动性明显增加;Zhang等[39]发现的茶树精油可以促进抗生素譬如氟康唑向胞内扩散,从而产生强大的协同效应,可见茶树精油通过改变膜特性和损害细胞膜相关功能发挥其抗真菌作用。
3.2.2 茶树精油对真菌芽管形成的抑制 茶树精油可以抑制真菌在生殖活动中芽管或菌丝转换体的形成。Hammer[38]和D’Auria[40]等研究发现在0.25%和0.125%茶树精油的存在下,胚芽管形成被完全抑制,同时还观察到芽孢子从单芽或单芽形态变为多胎形态的趋势。此外,去除茶树精油后真菌能够重新形成胚芽管,表明了茶树精油对真菌生殖管的抑制是可逆的。
3.2.3 茶树精油对真菌呼吸的抑制 茶树精油还可以抑制真菌的呼吸作用。Cox等[41]发现茶树精油的浓度在0.125%时即可显著的抑制白色念珠菌的呼吸作用。在浓度为1.0%、0.5%时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作用分别为95%、40%。Hammer[38]等还发现茶树精油可以抑制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酿酒酵母的葡萄糖诱导的培养基酸化,而培养基酸化的原因可能是通过质膜ATP泵所产生的。可见茶树精油可以通过抑制真菌的能量代谢过程和破坏线粒体膜的完整性而起到杀真菌作用。
Li等[31]的研究发现,茶树精油可以导致灰葡萄孢线粒体膜的形态和超微结构发生改变,增加线粒体膜的通透性,从而导致细胞内ATP的含量下降,细胞外ATP含量增加;并且增加茶树精油的浓度进一步影响与三羧酸循环有关酶的活性,使柠檬酸合成酶、柠檬酸脱氢酶、α-酮戊二酸脱氢酶、琥珀酸脱氢酶、苹果酸脱氢酶和ATP酶的活性降低,同时大大增加了活性氧(ROS)的水平,从而破坏了三羧酸循环,最终导致菌体的死亡。Xu[42]用等压标记进行相对和绝对定量的方法,在茶树精油处理与未处理的灰霉病菌中发现了718个差异表达蛋白(DEP),其中17个显著上调,701个显著下调。其中约78%与糖酵解、三羧酸循环(TCA循环)和嘌呤代谢有关,这些都表明了茶树精油可能是通过抑制真菌的三羧酸循环来杀灭或者抑制真菌生长。
茶树精油具有强大的抗真菌作用,对霉菌、酵母以及镰刀菌属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茶树精油在食物保鲜以及人类皮肤病的防治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并且茶树精油对真菌作用的靶点的多样,对其细胞膜、生殖作用、呼吸作用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了产生耐药性的风险,但其对于真菌的芽管的作用的机制以及各个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还不够透彻,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4 茶树精油的抗病毒活性
茶树精油具有一定的抗病毒活性,Bishop等[42]首先报道了茶树精油具有抗烟草花叶病毒的活性,还有研究指出茶树精油对单纯疱疹病毒Ⅰ[43]、流感病毒[44]、人类乳头状瘤病毒[45]、腺病毒2型[46]、痘病毒[47]有很好的杀灭作用。但对于其杀灭机理的研究较少。Schnitzler等[48]用茶树精油处理处于不同复制周期的病毒发现茶树精油对游离病毒的杀灭效果最好。Garozzo等[48]发现在流感病毒吸附后1 h内用茶树油处理会造成活病毒数量的大量减少,但是2 h以后用茶树精油对病毒的活性基本没有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茶树精油可以通过干扰抑制病毒脱壳的溶酶体内腔室酸化来抑制流感病毒在细胞中的生长,内泌体和溶酶体的酸性条件可以引起病毒包膜融合活动,包膜融合对流感病毒感染的脱壳过程至关重要,可见,茶树精油是干扰了病毒复制的早期阶段。虽然茶树精油具有一定的抗病毒效果,但迄今为止测试的病毒范围非常有限,缺乏大量的体外和临床数据证明其存在广谱的抗病毒效果。
5 茶树精油的抗寄生虫活性

6 茶树精油的有效作用成分
茶树精油的RW[8]系数表明,其主要活性成分可能是松油烯-4-醇和α-萜品醇,有大量的数据显示这两种成分对微生物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α-萜品醇在茶树精油中的含量较低,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松油烯-4-醇是茶树精油的最主要的活性成分。Cox等[41]发现松油烯-4-醇和γ-萜品烯或和癸烯的组合产生与茶树精油近的抑菌活性,但是γ-萜品烯和癸烯却降低了松油烯-4-醇的水溶性;Li等[53]发现松油烯-4-醇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以及黑曲霉菌的抑制活性与茶树精油相当,可以推测松油烯-4-醇的抑菌活性和茶树精油相当甚至更加强大。
但近期有研究表示松油烯-4-醇可能不是茶树精油的主要活性成分。Paola Brun等[14]研究了10种市售的茶树精油产品的抗微生物活性和化学特征,通过GC-MS发现尽管10种产品都属于松油烯-4-醇型茶树精油,并且九种主要化学成分的含量都符合ISO的规定,但是它们每种成分的具体含量还有较大的差别。它们分别测定了这10种精油对光滑念珠菌、单纯疱疹病毒1型(HSV-1)、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铜绿假单胞菌评估抗菌活性,结果发现只有5种精油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抗微生物作用,并且在这5种精油中抗微生物活性最好的是含有较低含量的松油烯-4-醇和较高的α-萜品醇、α-品烯和1,8-桉叶素,松油烯-4-醇含量最高的茶树精油的抗微生物活性反而最低。通过数据分析无法确认茶树精油某一成分的含量与其抗微生物活性之间有明确的关联。这些结果说明了松油烯-4-醇可能不是茶树精油抗菌活性的全部来源,其抗微生物活性可能是多种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茶树精油成分的多样性,其中各个组份抗微生物的机理也不尽相同,因此很难将其生物活性归于其中复杂化合物中的单一化合物,可以将其抗微生物效果视为包括每种微量成分在内的多种化合物之间的协同作用,但是这种协同作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7 结语
随着抗生素滥用所带来的细菌耐药性问题的不断恶化,诸如茶树精油之类的天然替抗产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茶树精油已被应用于治疗和预防某些微生物感染,并且由于其毒副作用小,受到了研究人员的普遍青睐,但目前仍缺乏针对微生物感染治疗的临床证据,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大规模临床研究来巩固茶树精油在替抗领域的用药地位。
茶树精油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其抗微生物机理也较为复杂,目前大部分研究也都集中在茶树精油对微生物细胞壁、细胞膜和线粒体膜的破坏以及对能量代谢、生殖活动的影响上,但各个药物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明确,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
近年来随着系统生物学以及计算机模拟的天然产物靶标预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可通过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和代谢组学等技术研究茶树精油抗微生物的作用机制。同时,结合计算机模拟的天然产物靶标预测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等方法,对揭示茶树精油对于微生物某个靶点的作用乃至整个蛋白质网络的影响和在“减抗替抗”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