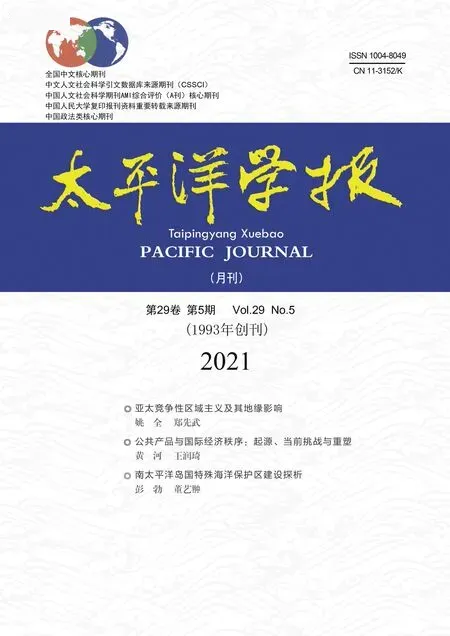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及其地缘影响
姚 全 郑先武
(1.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区域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的数量大幅增长。近些年来全球化逆动,“回到区域”更成为未来国际局势最有可能的图景,①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6 期,第203 页。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衰退,区域愈发成为国家关系的重要舞台。②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2020 年第3 期,第142 页。无论区域制度规模如何,均成为大国相互竞争的重要平台,大国借助区域制度进行权力角逐和利益争夺。 国家间的区域合作从属于国家间的区域竞争,国际社会出现了竞争性区域主义现象。 而大国在亚太的区域制度竞争最为激烈,这在亚太区域三大不同层次均有鲜明体现(参见表1)。 然而,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区域范围制度之间的竞争存在哪些共同特点,呈现哪几种形态类型,大国主要采取哪些区域竞争的手段,对区域秩序造成哪些影响,学术界尚未从区域主义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 因此,本文将以大国在亚太区域的区域竞争为切入点并结合具体分析案例,回答以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以进一步丰富竞争性区域主义概念的内涵,并尝试构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表1 亚太不同区域层次的区域制度竞争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文简称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下文简称 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下文简称RCEP);日本主导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Asia-Pacific Regional Space Agency Forum,下文简称APRSAF);中国主导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sia-Pacific Spa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下文简称APSCO);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sian Monetary Fund,下文简称AMF);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下文简称EAEG)。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当前,大国竞争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鲜有从国际区域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既有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以中美战略竞争作为大国竞争最主要的分析对象,研究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过程、特点、本质、限度、影响,以及对中美战略竞争进行管理的建议等。 第二,以大国竞争为时代背景,分析第三国、区域政府组织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在此背景下其所采取的或者应该采取的战略选择和所扮演的角色分析。 第三,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分析大国竞争的内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②Patrick Porter, “ Advice for a Dark Age: Manag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Washington Quarterly,Vol.42, No.1,2019, pp.7-22; Alexander Korolev, “Shrinking Room for Hedging: System-Unit Dynamics and Behavior of Smaller Pow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 No.3, 2019, pp.419-452;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第 96-130 页等。
从总体上看,有关大国竞争的既有研究内容丰富,分析深入,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从研究层次看,既有研究从国家层面分析大国竞争的态势,从国际秩序、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层面分析大国竞争带来的影响,忽视了大国以区域为平台所展开的战略竞争;从研究领域看,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自独立的领域研究大国竞争,缺乏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从研究方法看,分析某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对外战略或者以大国竞争为背景分析第三方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容易陷入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缺乏大国、区域政府组织,以及中小国家之间变化的、互动的关系分析。 因此,本文引入竞争性区域主义的概念,分析亚太不同区域层次区域制度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关系,探讨大国区域竞争如何影响区域秩序。 竞争性区域主义的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大学科领域: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 “竞争性区域主义”概念源于20 世纪9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分别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区域一体化之间的竞争,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深化区域主义进程中的作用。 进入21 世纪,区域主义快速发展,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区域贸易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明显。 2008 年在位于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召开了关于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国际专题研讨会;2009 年,米瑞娅·索利斯(Mireya Solís)等学者主编的专著以自由贸易协定扩散为切入视角,重点评估环太平洋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竞争压力的影响。①Jens van Scherpenberg, Elke Thiel, eds., Towards Rival Regionalism? US and EU Regional Regulatory Regime Building,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1997; Kiichiro Fukasaku, Shujiro Urata, Urata Kumura, eds., Asia and Europe: Beyond Competing Regionalism,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Stephen Woolcock, et al.,“Competing Regionalism: Patterns, Economic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tereconomics, Vol.42, No.5,2007, pp.236-259; Mireya Solís, Barbara Stallings, Saori N. Katada eds.,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FTA Diffusion in the Pacific Rim,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二是城市发展与区域规划领域。 2000 年,美国托莱多大学的琳达·麦卡锡(Linda McCarthy)将竞争性区域主义引入城市发展与区域规划领域,认为区域内各个行为体通过互相协作,能够增强区域整体的竞争力,进而使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全球竞争。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区域协调网络的兴起又会导致区域之间的竞争,形成竞争性区域主义现象。②Linda McCarthy,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Beyond Individual Competition,” Revie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No.6, 2000, https:/ /www. researchgate. net/publication/237129627 _ Competitive _ Regionalism _ Beyond _ Individual _Competition);罗小龙:“竞争性区域主义与区域建构研究展望”,《人文地理》,2012 年第 3 期,第 7-10 页。
三是国际关系领域。 竞争性区域主义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时间最晚,用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各个区域都存在的竞争性区域主义现象。例如在非洲大陆,不同动机、不同合作理念的政府间机构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威胁了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③Benedikt Franke, “ Competing Regionalisms in Africa and the Continent’ s Emerg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9, Issue 3, 2007, pp.31-54.在亚太(东亚)区域,区域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特征——“放大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过度发展,成为竞争性区域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这些区域主义自诞生起就带有竞争性质。 大国强调以区域机制作为竞争平台,以此服务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真正为了促进多边团结,造成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导致“制度过剩”,形成“竞争性的地区主义”格局;但与此同时,竞争性区域主义也为最终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并有一定的政治与安全意义;而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亚洲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历史源流及最新发展趋势,并为防止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滑向恶性竞争提供对策。④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外交评论(外文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第 78-80 页; T. J. Pempel, “Regional Decoupling: The Asia-Pacific Minus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9, pp.259-262.在欧亚大陆,竞争性区域主义表现为欧盟和俄罗斯在争夺周边邻国方面,推行相互竞争和排他的区域主义,展开了“一体化竞赛”。⑤Andrey A. Kinyakin and Svetlana Kucheriavaia, “The European Union v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 Integration Race 2.0?’” Przegld Europejski, No. 3, 2019.在南亚区域,竞争性区域主义主要反映为印度建立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环印度洋联盟(IORA)、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MGC)四大区域制度之间的相互竞争,削弱了南亚及其毗邻区域的区域多边主义。⑥Arndt Michael, “Competing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under Narendra Modi: New Leadership, Old Problems,”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iędzynarodoweenarodoweeg,Vol.51, No.4, 2015, pp.179-197。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发现,竞争性区域主义研究从一开始的政治经济学领域陆续转向区域规划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而自引入国关领域之后还未发展成为一项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 既有研究偏向经验性的案例研究,重历史与现实的案例分析,缺乏理论上的归纳与提炼,理论发展和完善不明显,关于竞争性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较为散乱,仍然只是一些孤立、涣散的理论碎片,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成型的理论。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亚太区域大国区域竞争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对竞争性区域主义进行一次更为系统、详细的阐述与分析,进一步总结并完善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分析框架。
二、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基本内涵
在竞争性区域主义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亚太区域主义的特点,将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定义为,以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等为代表的行为体通过区域主义路径实现或保护自身利益,削弱和排斥竞争者的影响力,造成区域主义之间相互竞争,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和状态。 其实质是大国以区域主义为工具开展地缘竞争,国际组织或者国家集团则通过区域主义维护区域内的权力平衡。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存在区域重叠、功能重叠和大国互斥的鲜明特点,呈现出轴辐型、同心圆型、相交型三种不同的形态类型。
2.1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特点
(1)区域重叠
竞争性区域主义最为直观的特点是区域制度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即不同的竞争性区域制度之间存在相同的成员。 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区域政府组织与域外国家组成不同的区域制度,但区域政府组织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当中保持不变,并处于中心位置。 例如,作为区域政府组织的东盟以整体为单位参与多个区域制度,如 “东盟+1”“10+3”合作机制,以及东亚峰会从“10+6”扩容到“10+8”。 第二,国家集团与域外国家组成不同的区域制度安排,但由于国家集团并不是一个区域政府组织,在与其他域外国家组成新制度的过程中,既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也无法处于中心位置,而是域外大国主导区域机制的发展。例如,在湄公河五国与域外国家所组成的区域合作机制当中,湄公河五国并不发挥主导作用,制度设计与议程设置主要依靠美日等域外大国。 第三,某些国家同时加入了大国所主导的不同区域制度安排。 例如,东盟的四个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是 RCEP、TPP/CPTPP 的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涵盖的国家也存在部分重叠。 前两种呈现一种比较规则的重叠形态,且重叠程度较高,而最后一种区域重叠是不规则的,重叠程度相对较低。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竞争性的区域制度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重叠,这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的两大阵营完全互斥、排他和相互独立的情况截然不同。
(2)功能重叠
区域制度安排不仅存在客观上的区域重叠,在主观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重叠。 尤其是当区域制度本身就是单一功能指向,那么彼此之间的功能重叠程度往往更高。 例如,TPP和RCEP 存在相同目标(即贸易自由化与经济一体化),①陈淑梅、全毅:“TPP、RCEP 谈判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亚太经济》,2013 年第 2 期,第 6 页。被认为是难以避免的二元轨道的竞争。 日本主导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APRSAF) 与中国主导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都专注于“外层空间利用”这一主题。
即便区域制度的功能是多样化、综合性的,彼此之间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 根据东盟与域外国家对话伙伴关系概览的报告可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的合作机制均围绕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领域,具体的合作内容和项目存在差别,但在制度功能上并无根本上的不同。②“External Relations,” ASEAN, https:/ /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访问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10 +3” 与东亚峰会“10+8”在发展愿景、议题设置等方面高度重合。和平、繁荣、进步、稳定是两者共同的发展愿景,金融、环境、能源、教育、疾病和自然灾害管理等具体的区域合作任务是两者共同关注的领域。东亚峰会通过简单地复制而不是补充或取代“10+3”,与后者的任务重叠,这导致东亚区域架构的重复与区域功能的重叠。③Jae Cheol Kim,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Asian Perspective, Vol.34, No.3,2010, p.132.“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方面都存在重叠之处,尤其经济领域的重叠较多,同时,双方都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经济领域的首要位置,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的核心目标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④刘飞涛:“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策略”,《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1 页。澜湄合作机制与美日印澳韩等国分别主导的湄公河区域合作机制均关注非传统安全议题,存在较大功能重叠。
(3)大国互斥
“当今一切现实的地区主义实践都是由民族国家推动的”,“地区主义内部和地区主义之间充满着各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集团的相互竞争”。①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欧洲》,1999 年第 2期,第 41 页。亚太区域大国林立,大国之间不仅存在利益矛盾,而且还受到历史恩怨的困扰。 中美作为世界级大国存在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强大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性规则迫使中美走向竞争,②[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1 页。东盟和美国之间虽然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议,东盟甚至将美国视为一个良性大国,希望美国维持在东亚的持续存在,但双方之间又存在难以彻底调和与完全相互社会化的规范矛盾。③张云著:《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6-240 页。因此,亚太区域发展的动力总是受国家中心逻辑控制,④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3, 2000, p.465.本以“走向融合”为目标的区域主义发展成为竞争性的区域主义。 在区域重叠、功能重叠的基础上,大国互斥使得区域制度之间的兼容性和合作性大为削弱,竞争性显著强化。 大国互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国各自主导区域制度安排相互独立,彼此所主导的区域制度互不包含对方,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 这种排他性既可能是大国将另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国排斥在外,也可能是大国拒绝加入对方所主导的区域制度安排,其客观结果是大国互不参与对方的制度安排,这是大国互斥的常见形态。 例如,中日韩三国单独与东盟发起“10+1”,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分别与湄公河五国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在泰国的建议下建立了澜湄合作机制;美国主导的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简 称TTIP)通过高门槛把中国排除在“带有明显俱乐部色彩”的贸易体系之外,⑤高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国际观察》,2018 年第 2 期,第 57 页。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有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⑥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宏观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1 期,第 33 页。对中国的战略制衡甚至“遏制”行动又迫使中国同样采用区域主义制衡美国的联盟体系,⑦Baogang He, “ Regionalism as an Instrument for Global Power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Vol.44, No.1, 2020, p.6.但中美所主导的区域制度互不包含对方。 第二,大国处于同一项制度安排,但互斥的大国都不发挥领导作用,而强调区域政府组织的重要地位。 相关组织为了巩固和保持自身地位,也利用大国的彼此互斥,引入足够多的区域外大国并建立新的区域制度,形成以区域政府组织为中心的密集的区域制度网络。
《东盟宪章》明确将“东盟中心性”定位为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各类区域制度安排的“首要驱动力量”。 东盟在东亚峰会的官方文件中反复以诉诸文字的方式强调东盟的核心与主体地位。 区域重叠、功能重叠及大国互斥共同决定了区域制度之间的竞争性,它们既是竞争性区域主义的特点,也是其基本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类型划分
从区域竞争的具体形态特征方面来看,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呈现三大不同的形态类型。
(1)轴辐型竞争性区域主义
轴辐型竞争性区域主义存在两大核心要素:轮轴——在亚太区域表现为位于中心位置的区域政府组织或一个松散的、尚未制度化的国家集团;轮辐——多个与区域政府组织或国家集团建立区域制度安排的域外国家,这些域外国家通常是大国或者中等强国,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 每一个域外国家与区域政府组织或国家集团共同组成一项区域制度安排。 每一项区域制度安排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参见图1)。 典型的例子包括,其一,东盟10 国与域外大国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政府组织是“轮轴”,处于“中心位置”,发挥“主导作用”,以“东盟中心性”为目标和原则,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美国、韩国、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域外作为“轮辐”的国家建立外部对话伙伴关系,甚至成立了自由贸易区。 但每一个“东盟+1”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其中某一个“东盟+1”有新的变化或进展,可能引发其他的“东盟+1”机制产生相应的连锁反应。 例如,200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 年,日本、印度紧跟其后,也与东盟签署了类似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 年11 月,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盟签署了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联合声明,2005 年12 月,韩国也与东盟签署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而且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考、借鉴了东盟—中国自贸区谈判模式。 其二,湄公河五国与域外国家建立的区域合作机制。 在湄公河区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美国均与湄公河国家建立了合作机制,而澜湄合作机制2016 年正式启动。 湄公河五国虽然不是一个区域政府组织,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域外大国建立合作机制,也展现出明显的轴辐形态。 只是湄公河五国并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域外大国主导着合作机制的发展。 虽然域外大国之间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地缘位置皆不相同,存在优势互补的可能,可能以对湄公河国家开展援助为共同目标,但大国间的优势互补让位于同质竞争,大国主导的合作机制在成立之初就带有竞争性动机,尤其是美湄合作机制,带有强烈的制衡中国的色彩。 而湄公河国家也满足于域外国家间竞争给本区域带来的多方收益,因而各个区域合作机制无法兼容,并且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澜湄合作机制与美湄合作机制之间的竞争也呈加剧之势。
(2)同心圆型竞争性区域主义

图1 轴辐型竞争性区域主义
同心圆型竞争性区域主义代表不同规模的区域制度形成嵌套,即新建立、扩容的区域制度在成员上完全包含了原有区域制度,并彼此共存,形成了一组同心圆结构(参见图2)。 同心圆扩展的过程就是成员国之间竞争的过程。 将同心圆型竞争性区域主义与轴辐型竞争性区域主义进行对比,能更好地理解两者各自突出的特点。 首先,在区域中心问题上,轴辐型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区域中心有可能是一个作为“小强权”的区域政府组织,也有可能是一个松散的区域国家集团,偏向于形态意义上的中心,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处于中心地位,也无法发挥领导作用;同心圆在对外扩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区域政府组织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仅仅是形态意义上的中心位置,而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处于中心位置,能够决定扩容的成员国对象、区域组织的目标和愿景等,发挥较强的领导作用。其次,在区域制度的组建形态上,轴辐型是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发展的,轮辐国家并不同时归属于一个区域组织,每一个轴辐都是独立存在的;而同心圆型是朝着成员数量增加、区域范围扩大的方向发展的,扩容后的、更大规模的区域新制度完全包含了区域制度原来的所有成员。 最后,在区域制度组建的时间序列上,同心圆型的扩容有一种明显的“时间—规模”逻辑,最先成立的区域制度即内圆,其规模最小、包含的成员国数量最少;而由于权力平衡的需要,同心圆逐步外扩,最晚成立的区域制度即外圆,其规模最大、包含的成员国数量最多。 而轴辐型竞争性区域主义的每一轴辐单独存在,彼此或许有合作,但并不相互融合,没有随时间推移导致规模不断扩大的特点。 例如,东亚峰会从“10+6”扩容为“10+8”,完全涵盖了“10+3”的所有成员,三者在外部形态上表现出同心圆型外扩的特点。 “东盟具有最高的中心性”,①董贺:“东盟的中心地位:一个网络视角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7 期,第 77 页。其扩容过程被认为是所有大国在亚太区域影响力的相互平衡,是一种“包容性制度平衡”的构建过程。②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Routledge, 2009, pp.144-145.

图2 同心圆型竞争性区域主义
(3)相交型竞争性区域主义
轴辐型和同心圆型竞争性区域主义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两种竞争性区域主义类型,它们都体现出独特的形态特征,在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实际分型中所占比例并不高。 更为常见的形态是相交型的竞争性区域主义,主要表现为大国(或区域政府组织)引领一个区域组织或区域制度安排建设,另一个大国发起一项带有针对性竞争目标的、同质的区域制度安排,竞争性大国不属同一项区域制度范围之内,互不参与对方组建的区域制度。 双方主导的区域制度所覆盖的区域范围通常比较广泛,包含的成员国数量众多,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但又不完全重合,只有部分国家同时是两个区域制度的成员(参见图3)。

图3 相交型竞争性区域主义
典型例子主要包括:其一,原美国主导的TPP 与东盟主导的、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RCEP之间的竞争。 两者包含众多相同的成员国,大范围区域重叠,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不同是TPP 不包括中国,而RCEP 将美国排除在外”,舆论普遍认为,TPP 和RCEP 是美中两个大国在亚太区域的势力范围争夺。③张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主要看点及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比较”,《国际论坛》,2013 年第6 期,第51 页。美国退出TPP后,TPP 转型为日本主导的CPTPP,日本同是CPTPP 与RCEP 的成员国,但日本在CPTPP 之中是主导国家,而在RCEP 则无法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势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CPTPP 的建设。 其二,APRSAF 与 APSCO 之间的竞争。APRSAF 成立于1993 年,由日本和东道国组织联合举办年度会议,来自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空间机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相关会议。④“About APRSAF,” APRSAF, https:/ /www.aprsaf.org/about/, 访问时间:2020 年 11 月 2 日。APSCO 于2008 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共有11 个成员国,是政府间的区域组织。 由于激烈的竞争和变化持续存在,中日两国国家安全空间范式的转变只会加深两国的警惕和竞争。 无论是APRSAF 还是APSCO,都不大可能成为空间合作的平台。⑤Saadia M. Pekkanen, “China and Japan Vie to Shape Asia"s Approach to Outer Space,” Forbes, October 31, 2016, https:/ /www.forbes.com/sites/saadiampekkanen/2016/10/31/china-and-japanvie-to-shape-asias-approach-to-outer-space/#5246f9a62606.其三,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作为大规模的区域间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相互重叠,其中,东南亚是最重要的重叠区域,也是中美竞争最激烈的舞台。 制衡中国是美国出台“印太战略”的“最现实原因,也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动因”,且“做法更为粗暴大胆”。①胡波:“美国‘印太战略’趋势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10 期,第 24 页。两者之间相互排斥,互不兼容,标志着以中国为首的区域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之间的较量越来越激烈。②Baogang He, “ Regionalism as an Instrument for Global Power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Vol.44, No.1, 2020, p.2.
三、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形成路径
大国以区域制度作为战略竞争工具,既可以新建一项区域制度与竞争对手主导的区域制度相抗衡,也可以选择引入新的区域制度成员以中和、平衡大国权力,还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建立新的区域制度,以及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破坏其已建立的区域制度。
3.1 新建竞争性区域制度
建立一项新的竞争性区域制度是大国在竞争性区域主义当中最常选择的路径。 大国遵循这一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1)大国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规范创建和议程设置等具体举措在新制度当中体现自身的意愿和偏好,即便大国在新区域制度当中同样经受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与限制,但总体上能够服务于大国的战略目标。 (2)迫于竞争对手所建制度将大国排除在区域制度之外的情况,谋求建立新的竞争性区域制度成为被排除在外的大国的自然选择。有趣的是,竞争对手所建立的区域制度安排所包含的中小国家为了平衡大国关系及试图同时从两边的区域制度中获利,可能主动提出与被排除在外的大国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安排,新旧区域制度之间构成对应竞争关系,这体现在亚太区域各个层次的区域制度竞争之中。
在区域间层面,美国主导TPP 后,其发展势头迅猛,部分东盟成员国相继加入,东盟既担心东盟内部离心趋势增强,也害怕其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当中的领导地位受损,主动中和了中日两国对东亚经济合作模式的分歧,提出组建RCEP 的倡议。③全毅:“TPP 和RCEP 博弈背景下的亚太自贸区前景”,《和平与发展》,2014 年第 5 期,第 79 页。中国因战略上和安全上的焦虑感,对美国倡导的TPP 持排斥态度,对RCEP谈判更加积极。④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12 期,第27 页。再如,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是为抗衡美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而寻找新出路的结果,⑤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0 期,第 45 页。服务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筹资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在“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后不久便正式成立,美国则又出台了“印太战略”,作为压制“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依托;⑥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4 页。在区域层面,东盟积极倡导和推动与东南亚域外国家之间的“对话伙伴关系”建设,先后建立起一套对话机制,同时在“10+3”合作机制区域合作“主渠道”背景下又建立了成员国范围更广的东亚峰会;在微区域层面,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初,美国与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四国建立了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 年吸纳缅甸加入该倡议,唯独将上游国家中国排除在外。 同年,泰国提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中方给予积极回应。 2016 年,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成功举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启动。2020 年9 月,美国发起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取代湄公河下游倡议,针对和制衡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
3.2 扩大原有区域制度
区域制度中要求扩员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该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大国,其总是担心另一大国权力的上升给自身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需要引入制度外的国家,让区域制度的权力更加平衡;另一类是区域政府组织,其希望在区域制度内的大国互斥的同时,又受到区域制度规范的限制,以突出和确保其自身中心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在哪个层次、哪种规模的制度框架下讨论和解决某一区域事务,成为成员国之间博弈的重大问题。 不同的成员国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希望在最小规模层级下商讨并解决问题,有的希望在最大范围内进行。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选择不同规模的区域制度引入或排斥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成员国,使得所开展的谈判对自身最有利。
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亚峰会的扩容。 除最初的东盟10 国与中日韩3 国以外,南亚的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横跨欧亚的俄罗斯,以及北美洲的美国最后都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东亚峰会从计划中的区域层面扩展到实际的区域间层面。 “10 +3”合作机制的成立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驱动的,东盟和中日韩三国践行着东亚区域主义的实验,这一进程首次将东南亚区域与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东亚大国联系起来,①Lay Hwee Yeo, “Institutional Regionalism versus Networked Regionalism: Europe and Asia Compa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7, No.3-4, 2010, p.325.“东亚区域一体化开始启动”。②全毅:“TPP 和RCEP 博弈背景下的亚太自贸区前景”,《和平与发展》,2014 年第 5 期,第 79 页。但是时至2004 年,当“10+3”合作机制进入第七个年头,马来西亚建议召开第一届东亚峰会,成员国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争论的焦点——东亚峰会成员国规模问题。 “10+3”合作机制成员国就此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意见对立的两大阵营,中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主张维持现状,不增加新的成员国,而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主张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峰会。③Benny Teh Cheng Guan, “Japan-China Rivalry: What Role Does the East Asia Summit Play?”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52, No.3, 2011, p.349.决定参与东亚峰会成员国的问题最后只能由东盟来决定。 最终,“10+3+3”的提法获得胜利,即“通过将一个更大的不结盟国家——印度,两个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在内,东亚峰会不会成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集团,从而保障东盟的地位”,④Nick Bisley, “The East Asia Summit and ASEAN: Potential and Problem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39, No.2, 2017, p.267.这是东盟决定引入更多域外国家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执政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由中东向亚太转移,派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并代表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美国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扫清了技术障碍。⑤王光厚:“美国与东亚峰会”,《国际论坛》,2011 年第 6期,第 30 页。而东盟也担心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东亚区域可能造成东盟“中心地位”转向“边缘化”,从而引入美国。美国和俄罗斯自2011 年起正式加入东亚峰会。虽然“东亚峰会”的名称没有改变,但是成员国所覆盖的范围已经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 在东亚峰会扩容的过程中,东盟和各个成员国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是否吸纳更多的成员国,而没有一个国家把重点真正放在区域建设和区域协调的问题上”。⑥Min Gyo Koo,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ASEAN+‘X’ Foru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19, No.1, 2012, p.88.东亚峰会成为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利用的一件与东亚接触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工具,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真正目的或理由。⑦Mark Beeson and Troy Lee-Brown, “The Future of Asian Regionalism: Not What It Used to Be?” Asia&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Vol.4, No.2, 2016, p.199.东亚峰会建立又扩容的过程就是区域竞争的过程。
3.3 阻止竞争对手建立竞争性区域制度
对于一些尚未正式成立的区域制度,如果对大国不利,大国也有能力阻止其建立,往往会在区域制度的提出和讨论阶段就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亚洲的一些区域制度最终未能建立与大国的反对存在很大的关系,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难以在美国的反对下建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主要国家货币相继贬值,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否能为陷入危机的国家制定一揽子计划并不确定,即便能够出台解救计划也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与之相比,由亚洲国家新成立一个区域组织制定一套金融支持方案则比IMF 实施解救危机计划容易得多。①Takatoshi Ito, “Asian Currency Crisi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0 Years Later: Overview,”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2, No.1, 2007, p.27.当处于危机之中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向日本求助时,日本提出了建立AMF 的设想。 但日本此举被认为是其试图通过在AMF 担任领导角色,获得更大的地区领导地位,②Julie Gilson, “Region Building in East Asia: ASEAN Plus Three and Beyond,” in Paul J.J. Welfens, et al.,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Europe: Historical Dynamics, Political Issues,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Berlin: Springer, 2006, p.223.削弱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亚太区域的领导作用,③Min Gyo Koo,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ASEAN+‘X’ Foru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19, No.1, 2012, p.83.其中,排除美国是实现这种利益的关键。④Yong Wook Lee, “Japan and the Asian Monetary Fund: An Identity-Inten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0,No.2, 2006, p.339.美国和美国主导的IMF 显然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竞争对手,“在美国反对、IMF 不支持,以及中国沉默的情况下”,⑤张卫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何时诞生?”,《经济》,2007年第 8 期,第 11 页。AMF 最终没能建立起来。 再如,早在1990 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提议,美国也持反对态度,它同样担心日本在东亚形成排美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最终控制亚太区域,⑥王志宏、刘建民:“‘东亚经济集团’能够真正建立吗?”,《亚太经济》,1996 年第 5 期,第 3 页。该提议最终也未付诸实施。
3.4 破坏竞争对手已经建立的竞争性区域制度
对于无法阻止的、竞争对手已经建立的竞争性区域制度,大国有三种破坏手段:(1)诋毁对手的竞争性区域制度,质疑其建立区域制度的目标和愿景,且自身率先拒绝加入,为盟友与合作伙伴树立反对性示范。 例如美国对倡导开放和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知偏负面,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中国版“再平衡”战略论、“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论、中国“新怀柔政策”论等消极认知甚嚣尘上,⑦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0 期,第 107-115 页。并有持续深化的趋势,认为“‘一带一路’可能侵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全球霸权的基础”,在不参与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加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制衡。 再如澜湄合作机制,美国针对中国作为上游国家的地理位置,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政治化、安全化、国际化、污名化,破坏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相互依存关系。 (2)劝服盟友不参与竞争对手建立的制度。 美国不但反对盟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服务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也一以贯之持抵制态度,并说服日本抵制亚投行。⑧T. J. Pempel, “ Regional Decoupling: The Asia-Pacific Minus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9, p.260.(3)质疑选择加入竞争性制度安排的国家能否获得预期收益。 当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简称G7)成员国意大利率先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之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Garrett Marquis)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评论,怀疑意大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能否给其带来好处,并敦促盟国和合作伙伴加大对中国的压力。⑨Evelyn Cheng, “Italy is Reportedly Going to Support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gram,” CNBC, March 6, 2019, https:/ /www.cnbc.com/2019 /03 /06 /italy-set-to-support-chinas-belt-and-roadprogram-ft-report-says.html.
四、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产生的主要影响
事物发展通常会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它们共同决定着事物的兴衰,并推动事物改革和向前发展。 竞争性区域主义也不例外。 它有助于避免大国竞争走向军事对抗,促进区域和平与区域制度的创新,但同时也造成区域发展碎片化、区域认同悬浮化,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削弱区域多边主义的发展。
4.1 维持区域安全稳定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核心是制度之争,制度竞争的关键手段是“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①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83 页。而不以发展军备、建立军事同盟等传统军事安全竞赛为主要手段。 再加上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主要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不太可能升级为以军事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对抗性竞斗。 制度竞争是一种相互软平衡的行为,其“所产生的摩擦有时可能会表现得比较直接甚至比较激烈,但总体是可控、可协调的”,②卢光盛、金珍:“超越拥堵: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路径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7 期,第 112-113 页。会制约大国走向以军事冲突为首要特征的硬平衡。大国之间一旦走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代表大国摒弃制度竞争的工具,而采取诉诸武力的极端手段。 但要重新实现和平,必须通过制度规范重新安排战后秩序。 例如,1815 年、1919 年和1945 年的战后安排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战后国际制度建立战略约束。③[美]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后约束与战略秩序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 页。因此,制度不仅是防止大国走向战争,也是战后重新恢复和平秩序不可或缺的工具。 大国维持在制度层面的竞争有助于维持区域甚至世界的和平,防止大国走向热战,这也是竞争性区域主义最显著的积极影响。
当然,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传统安全的地缘竞争对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传统安全压力,美国赋予新的区域制度安排以军事制衡的内容。 美国最早推出的《印太战略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制定,其早期目标偏向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要求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力求打造多维度的联盟体系以制衡中国崛起,同时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对敌人或者竞争对手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而且一旦陷入军事冲突,能够保证美国迅速取得战争胜利,④“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June 1,2019, pp.15-51.而其核心内容是美日印澳的安全合作,并以建立“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主要目标。⑤张弛:“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亚洲合作的现状及未来”,《东北亚论坛》,2021 年第 2 期,第 90 页。但亚太区域的中小国家将极力避免中美全面对抗,这将迫使其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从而失去更大收益。 日本、韩国、越南或东盟等众多中等强国正在不同的权力层次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急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积极寻求同双方同时建立良性的双边关系,⑥T. J. Pempel, “ Regional Decoupling: The Asia-Pacific Minus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9, p.262.在缓和中美潜在的两极竞争关系方面发挥影响。⑦Baogang He, “ Regionalism as an Instrument for Global Power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Vol.44, No.1, 2020, p.13.东南亚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中心区域,东盟是美国“印太战略”寻求支持的重要行为体,东盟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被认为是东盟版的“印太战略”,其主要强调包容、合作、发展的区域合作理念,试图消解美国“印太战略”的对抗性、竞争性,通过避免大国竞争进一步升级对抗来维持东盟的“中心地位”。⑧刘琳:“东盟‘印太展望’及其对美日等国‘印太战略’的消解”,《东南亚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72-90 页。东盟既不会接受与中国竞争、对抗为主旨的“印太战略”,也不承认美日印澳“四国+X”的“印太构想”机制,再加上四国利益目标的差异及资源不足,“印太战略”军事安全举措的实施受到很大制约。⑨刘鸣:“美国‘印太战略’最新进展与前景评估”,《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0 期,第 54 页。因此,虽然传统安全方面的地缘竞争甚至冲突赋予某些区域主义涉及传统军事安全竞争的内容,但军事竞争并不能凌驾或超越制度和规则,而且受到内部盟友目标差异及外部中小国家采取大国平衡政策战略对冲的制约与影响,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不太可能走向军事同盟对峙的恶性对抗。
4.2 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大国制度竞争将促进区域制度创新,大国不同的区域竞争路径和所形成的不同的竞争性区域主义形态将催生不同的区域制度创新方式。 在轴辐型和相交型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背景下,大国不在同一项区域制度之内,而是各自引领一项区域制度相互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制度竞争力,保持制度的优越性。 文明和文化没有高下之分,但制度却有优劣之别。 大国区域竞争的成败取决于各自区域制度竞争力的高低。 因此,大国需将更多精力投入区域制度设计、规范创建、议程设置及认同强化方面,对内实现权力平衡、利益共享与促进彼此信任,对外需要体现出强大的优势和抵御力。 前者让制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表现出适用性特性;后者使制度富有强大的竞争力,表现出优越性特性,内外有机结合保障大国的区域制度更经得起考验,在区域制度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同心圆型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背景下,大国同处于不同规模的区域制度当中,大国之间的权力相对平衡,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区域内的分歧和矛盾更多依靠大国来协调,实现区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新的区域制度不仅能为所有成员国接受,而且具备解决更多、更深层次问题的能力。
从长远来看,在新制度产生的过程中,一些旧的区域制度将因为不合时宜要么被合并,要么自行解散消亡,走向制度达尔文主义。①T. J.Pempel, “ 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2010, pp.209-238.亚太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要有实质性发展,不可能同时长期存在大量同质的区域制度,其数量过多恰恰表明区域一体化进程到达了瓶颈期,还需要继续摸索最适合的一体化道路。 竞争性区域主义将促进制度达尔文主义,遴选、洗练出更具优越性和适应性的区域制度,成为国际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新范式。 但由于“放弃现有制度的沉没成本以及建立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对于各国而言均相对较高”,②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83 页。制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3 区域发展碎片化
区域融合的漫长过程使区域发展碎片化现状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 竞争性区域主义代表不同区域制度之间的竞争关系,本区域的合作是为与另一个区域开展竞争服务的。 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区域建设的大国无法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行事,在某些本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共同合作的领域,大国各自为政,在同一个区域就相同议题提出各自的方案,区域组织或区域制度嵌套、交叉、重叠,不同层次的区域主义相互分割、竞争,甚至对立,造成区域割裂和碎片化发展。 究其原因,亚太区域秩序变革的驱动力仍然是权力之间相互竞争的抗力,而不是基于认同与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合力。 亚太区域大国之间缺乏信任,传统安全困境依然存在,③秦亚青著:《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版,第 223 页。大国间竞争的意识普遍高于合作的意识,新的区域制度安排甚至是出于安全困境建立的。 未来的亚太区域秩序仍然是各种区域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中心的、维持现状的“区域合作”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区域碎片化秩序,这也许是走向一个超越无政府状态的、以“共同体”观念主导的、区域政治实体化的“变革性”区域共同体秩序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艰苦探索的过程。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参与世界上最典型的欠发达区域——湄公河区域的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均以湄公河国家的需求为导向,内容高度重叠,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却没能形成优势互补,各自与湄公河国家单线开展合作,相互之间没有合作的交集。 然而,参与湄公河区域的国家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大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在湄公河区域建立了一套区域制度,它们在湄公河区域所关注的领域基本大同小异,也以双边关系发展为主,没能形成更大范围的、统筹全局的多边合作机制。虽然美国牵头组建了参与主体更为广泛的“湄公河下游之友”(Friends of the Lower Mekong),④湄公河—美国合作伙伴关系取代湄公河下游倡议后,“湄公河下游之友”(Friends of the Lower Mekong)更名为“湄公河之友”(Friends of the Mekong)。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世界银行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纳入其中,美国和日本加强了在湄公河区域的合作,但域外国家与湄公河区域的合作机制仍然独立存在,相互之间未能得到有效整合。 亚太区域制度安排“过剩”“拥堵”,缺乏整合成为涵盖整个区域、高质量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动力。①刘均胜、沈铭辉:“亚太区域合作制度的演进:大国竞争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12 年第 9 期,第 65 页。
4.4 区域认同悬浮化
从规范意义上讲,区域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区域成员之间除拥有长期的共同利益之外,更需要有“共同的特性、共同的政治意识和共同的理解”,集体共识才能推动实践共同体或行动共同体的产生。②王明国:“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当代亚太》,2017 年第 4 期,第 94 页。从区域间到微区域,不同层次的区域主义均存在相互竞争,权力和利益仍然是国家选择组建或者参与区域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区域认同、区域共同体观念悬浮于行为体的行为选择之上,甚至停留在一种口号层面上,没有内化成所有成员国共同追求的目标。 区域的正向扩张或者逆向碎裂是权力和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区域认同的驱动。 在充满权力竞争的环境下,再加上亚太国家发展严重不平衡,以及不同的政治体制、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亚太区域并没有形成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肥沃土壤。 如果说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形成的关键外部因素是美国重返亚太、介入东亚,政治根源是国家中心主义盛行,经济根源是由市场驱动的区域主义发展乏力而依赖域外国家市场,那么内部根源则是区域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性缺位。 区域主义发展的社会性缺位,无法“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难以消除竞争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制约了区域认同的建构”,③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第 63-65 页。区域认同悬浮于亚太区域共同体的形塑过程。 在东亚峰会扩容升级过程中,中日韩以及东盟成员国内部一开始对东亚区域的定位和认同就不同,在“包含哪些成员国”这个有关区域认同的基本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 东亚峰会最后成为包含18 个国家的区域制度,在地理范围上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东亚地区范围,这是大国之间权力平衡的结果,并不是基于区域认同的主观塑造。 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10+3”还是东亚峰会都不太可能战胜对方,两者会继续共存并相互竞争。④Jae Cheol Kim,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Asian Perspective, Vol.34, No.3,2010, p.134.“10+3”和东亚峰会的竞争将继续限制区域认同的发展,⑤Gregory P. Corning, “Trade Regionalism in a Realist East A-sia: Rival Visions and Competitive Bilateralism,” Asian Perspective,Vol.35, No.2, 2011, p.260.这使得亚太区域主义在区域复合体和区域社会之间徘徊,而无法迈向具有明确集体认同的、更高层次的区域共同体。
五、结 论
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第一代“旧区域主义”、第二代“新区域主义”,以及第三代“区域间主义”三大阶段。 区域主义演进的脉络反映出区域主义研究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区域主义的合作向度,即区域主义如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从单一性向综合性迈进,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迈进,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的对话与合作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和重心。 然而,区域主义之间的相互竞争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传统地缘政治复苏,世界重新回归大国竞争,全球性大国回归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区域体系分化,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区域制度展开激烈竞争,区域主义之间的竞争向度越来越突出,区域主义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一种战略工具。
本文结合亚太区域大国区域竞争的现实实践,分析并探讨了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基本内涵、形成路径,以及对区域秩序的影响,初步构建了一个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研究分析框架。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表现出区域重叠、功能重叠及大国互斥的鲜明特点,并且在竞争形态上呈现出轴辐型、同心圆型与相交型的三大类型。主权国家和区域政府组织是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核心行为体,它们通过建立新的竞争性区域制度、扩大原有的区域制度、阻碍对手建立新的竞争性区域制度,以及破坏对手已经建立的竞争性区域制度等现实路径发起区域竞争。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既是大国区域竞争的手段,也是大国区域竞争形成的结果,它有助于维持区域安全和稳定,促进大国探索、完善更具竞争力和适应性的区域制度,然而也存在区域发展碎片化、区域认同悬浮化等消极影响。 如何克服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负面影响,走向区域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在未来的国际区域治理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上,依然任重道远。比较区域主义和历史分析方法,或许是目前研究亚太各国管控风险、化解风险,乃至趋利避害、谋取共赢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