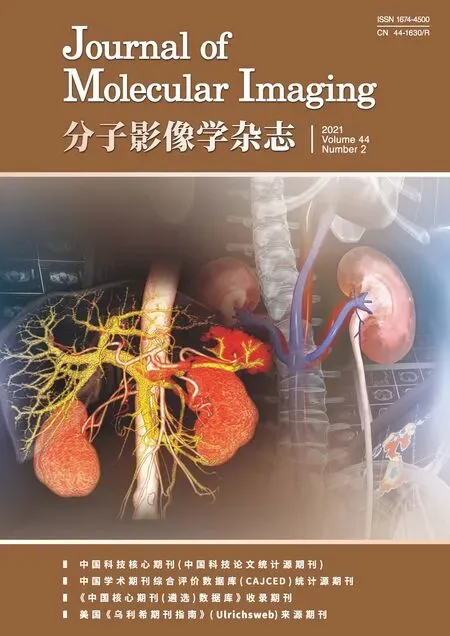2型糖尿病女性患者骨密度与骨转换率的相关性
张银华,龚瑞,李晨钟,胡世弟,沈洁,2
1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广东广州 510630;2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广东佛山528000
2型糖尿病(T2DM)患者患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比非糖尿病患者更高[1],而2型糖尿病合并低创伤性骨折患者的骨密度(BMD)可表现为正常、降低甚至增高[2-3],提示BMD对于T2DM合并骨质疏松的诊断不够全面,存在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情况,故临床上有必要结合其他指标来辅助诊断。
骨转换标志物(BTMs)可分为骨形成和骨吸收标志物。骨形成标志物如骨钙素N 端中分子片段(NMID)由成骨细胞合成或原骨胶原代谢所产生。而骨再吸收标志物如β-Ⅰ型胶原C-末端交联(β-CTX)则是破骨细胞合成或胶原降解的产物。结合骨代谢指标与骨密度能整体反映2型糖尿病骨代谢平衡的变化特点,BTMs可作为T2DM并发低创伤性骨折的辅助诊断手段。目前骨质丢失被认为是由于骨转换率的增加以及骨形成和骨吸收之间不平衡的结果。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骨转换率或骨重建率与骨流失率之间的相关程度[4-5]。单个的骨吸收或者骨转换标志物无法评估骨转换率或骨重建率。因此,从全身骨转换和骨平衡的角度来描述BTMs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目前骨平衡计算方法有以下4种:计算相对于同龄对照组的绝经后妇女Z值[6];使用多个BTMs的中位数来计算骨转换和骨平衡[7];基于尿I型胶原交联氨基末端肽和血清骨钙素(OC)之间的关系来计算绝经后妇女骨平衡指数,该指数与绝经期脊柱骨质丢失有关,但与股骨颈无关[8];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和Ⅰ型胶原C-末端交联经过标准正态转换后,分别来计算骨形成T值和骨吸收T值,结合两者T值来计算骨转换率和骨重建率,以往研究表明绝经后10年内女性的骨转换率与骨丢失率之间的存在负相关[9]。本研究引用了以上第4种统计方法,通过比较T2DM女性患者中骨质疏松组和骨量正常组的骨转换率T值和骨重建率T值来评估总体骨转换率和骨重建率,探讨骨转换率和骨重建率与骨密度之间的相关性,为T2DM并发低创伤性骨折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提供新的视角。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1年4月~2020年9月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女性T2DM患者201例。纳入标准:均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在住院期间已完善β-CTX(骨吸收的标志)和NMID(骨形成的标志)测定,并已完整行腰椎(L1~4)及左侧髋关节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检查。排除标准:1型糖尿病、继发型糖尿病患者;患有甲状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肾功能不全、肿瘤、各种急性及慢性感染、结缔组织病、代谢综合征等可能影响糖代谢、骨代谢的疾病;长期服用钙剂、抗骨质疏松药、糖皮质激素、噻唑烷二酮类降糖药等可能影响骨代谢的药物;长期大量吸烟、饮酒者;绝经前的孕妇。201例T2DM住院患者年龄64.93±10.21 岁,平均糖化血红蛋白(HbA1c)(7.50±2.69)%。与骨量正常组相比,骨质疏松组年龄、收缩压、HbA1c和肌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舒张压、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β-CTX和N-MI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e among groups(Mean±SD)
1.2 资料采集
由专人采集并记录病史内容,包括患者年龄、既往病史、用药史(降糖方案、激素、钙剂、抗骨质疏松药等使用情况)、月经史、吸烟及饮酒史等临床资料。
1.3 实验室检查
研究对象均空腹8 h以上,入院次日清晨抽取正中静脉血标本送检,检测β-CTX和N-MID、HbA1c、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酐。
1.4 骨密度及髋部几何结构参数测定
采用Prodigy双能X线骨密度仪(GE),该仪器由骨密度检测室专人操作,变异系数为<1.0%。测量所有研究对象的后前位BMD:腰椎(L1~4)、总体(L1~4-BMD)、左侧股骨颈(FN-BMD)、髋部总体(TH-BMD),变异系数分别为0.97%、2.20%、2.97%、0.9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骨质疏松诊断标准:T值>-1.0为骨量正常;-2.5 应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将CTX 和N-MID 进行标准正态转换。每个BTMs的T值被用来计算骨形成T值和骨吸收T值,计算公式为:T值=(BTM-平均BTM)/标准差。根据骨形成T值和骨吸收的T值来计算骨转换率[骨转换率T值=(骨形成T值+骨吸收T值)/2)]和骨重建率[(骨重建率T值=骨形成T值-骨吸收T值)]。BMD与骨转换率T值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在校正HbA1c时采用Partial偏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骨量减少组的L1~4-BMD、FN-BMD、TH-BMD较骨量正常组分别下降了0.2、0.193、0.215 g/cm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质疏松组的L1~4-BMD、FN-BMD、TH-BMD较骨量正常组下降了0.307、0.327、 图1 骨量正常组和骨质疏松组的DXA影像比较Fig.1 Comparison of DXAimages between normal bone mass group and osteoporosis group 表2 三组BMD及骨转换率T值和骨重建率T值比较Tab.2 Comparison of BMD and T-score of bone turnover and bone balance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骨转换率T 值与髋部BMD呈负相关(r=-0.14,P<0.05),HbA1c与髋部BMD、骨转换率T值无相关性(表3)。Partial偏相关分析显示,在校正HbA1c后,骨转换率T值与髋部BMD呈负相关(r=-0.144,P<0.05,表3)。 表3 骨转换T值与髋部BMD的相关性分析Tab.3 Correlation of T-score of bone turnover and hip BMD 本研究的T2DM女性患者一般资料分析显示,骨质疏松组的N-MID和β-CTX较骨量正常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本研究人群年龄跨度大,骨质疏松组的骨标志物呈现高骨转换和低骨转换两种状态,N-MID和β-CTX水平呈非线性改变,故组间单因素分析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单个骨标志物不能很好反应骨丢失,受影响因素较多,故我们在本研究中采用了新的评估方法,结合骨形成标志物和骨吸收标志从整体上评估骨转换或骨重建与骨丢失之间的相关程度。本研究的N-MID和β-CTX经过标准正态转换后,分别来计算骨形成T值和骨吸收T值,结合两者T值来计算骨转换率和骨重建率。本研究骨质疏松组的骨转换率T值较骨量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经过新的统计方法转换后,BTMs与BMD之间的关联才更显著。 但本研究只有髋部BMD的骨质疏松组的骨转换率T值与骨量正常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股骨颈和腰椎等部位的骨质疏松组的骨转换率T值与骨量正常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是由于腰椎骨密度容易受到椎体压缩性骨折、骨质增生和邻近主动脉钙化灶等影响而容易得出阴性结论[10]。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骨转换率T值与髋部BMD呈负相关(r=-0.14,P=0.049),Partial 偏相关分析显示,在校正HbA1c 后,骨转换率T 值与髋部BMD 呈负相关(r=-0.144,P=0.043),这提示校正血糖对BMD的影响因素后,骨转换率T值与髋部BMD仍呈负相关,提示T2DM女性患者随着骨转换率T值的升高,髋部BMD呈下降的趋势,并发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也会随之增高。这提示本研究的T2DM女性患者的骨质疏松组的骨转换率增高,符合绝经后骨质疏松的骨转换特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一般发生在女性绝经后5~10年内;绝经期的开始预示着骨骼基本多细胞单位激活频率的增加,骨吸收期的延长,骨形成期的缩短[11]。生化指标显示,骨代谢呈高转换状态[12]。有研究发现在绝经后1~10年的女性中,骨转换率T值与BMD存在负相关性,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骨转换率T 值与髋部BMD 相关性较弱(r=-0.14),可能由于衰老引起的退行变干扰了T2DM人群骨转换T值与髋部BMD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骨质疏松组平均年龄72.59±8.732岁,70岁以后发生的骨质疏松主要由衰老引起[13],与衰老相关的炎症和氧化应激,可能是骨形成和骨吸收失衡的主要原因[14],血清骨钙素和CTX呈低水平,呈现低骨转换状态[15]。但本研究中T2DM骨质疏松组呈高骨转换状态,提示该人群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绝经后雌激素缺乏引起的。 有研究报道,血清骨钙素、血清Ⅰ型原胶原N-端前肽、β-CTX和碱性磷酸酶水平的升高与男性3个部位骨密度水平的降低相关,同时与女性腰椎骨密度水平降低有关[5]。骨重建分为吸收、逆转、形成和休止4个阶段。在健康的年轻成人骨骼中,骨重建可以移除和替换旧骨以及受损骨,从而保持骨强度[16]。骨重建的变化可由骨形成和骨吸收的BTMs来反映。β-CTX是破骨细胞骨吸收时,I型胶原被降解所产生的C-末端交联片段。因此,β-CTX被认为是破骨细胞活性和骨吸收的标志[17]。有研究报道,在绝经后期妇女中,血清骨钙素和CTX的低水平与胰岛素抵抗风险增加和长期发生糖尿病风险增加相关[15]。因本临床研究选择了T2DM人群做数据分析,故选择β-CTX来计算骨吸收T值。 本研究对引用的统计方法做相关调整,在计算骨形成T值时选用N-MID,非引用研究的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因本研究人群为T2DM患者,选用骨钙素更能符合该人群在糖尿病这种疾病状态下骨代谢状态。骨钙素是由成骨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主要储存在骨基质中的一种特异非胶原骨基质蛋白质,在骨重塑和骨吸收过程中释放进入血液[18],在血液循环过程中,被分解为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N-MID)。骨钙素在动物模型体内被证明是一个新陈代谢活跃的激素,提高胰岛β细胞功能和促进胰岛素分泌,同时增强骨骼肌和脂肪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19]。有纵列研究表明,血清骨钙素是糖尿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0]。有研究显示在T2DM患者中,血清骨钙素水平较糖耐量正常者明显降低,与空腹血糖、HbA1c,脂含量和胰岛素抵抗呈负相关[21],故本研究选择N-MID来计算骨形成T值。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人群仅限于中国南方妇女,可能不适用于男性和其他种族,仍需扩大人群样本量去验证该统计方法的检验效力。骨代谢标志物已被广泛应用于预测骨质疏松症患者治疗后发生骨折的风险、评估骨折愈合和骨质疏松治疗药物的选择等方面,但是骨形成和骨吸收之间的平衡程度,以及骨转换率和骨重塑与骨流失率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楚,本研究通过结合骨形成和骨吸收的骨标志物来计算骨转换率T值,并结合BMD来证实,在T2DM女性患者人群中,骨转换率T值与髋部BMD呈负相关,提示T2DM患者随着骨转换率T值的升高,BMD呈下降的趋势,并发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也会随之增高。在未来,骨转换率T值方法有可能应用在T2DM人群里预测骨折和监测骨合成和抗吸收治疗的效果。1.5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BMD及骨转换率T值和骨重建率T值比较


2.2 髋部骨转换率T值与髋部BMD的相关性分析

3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