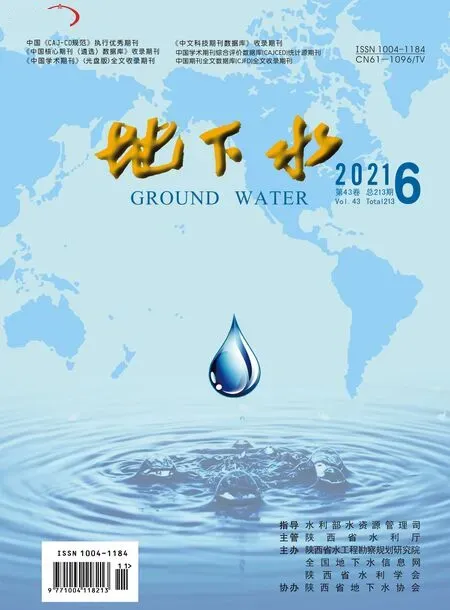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探索与思考
张丽佳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2.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北京 100034)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煤炭、金属等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当前以及未来仍将高度依赖煤炭、金属资源的开采和生产。在经济转型发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探讨单一自然要素如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及受政策、经济的影响,以矿区为研究对象和单元,探讨如何实现矿区生态产品价值的研究较少。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便是搭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桥梁[1-2]。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赋予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3]。绿水青山存在于所有国土空间内,矿区也不例外。因此,对于矿区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不断探索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能够在促进矿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改善矿区生态环境,创造矿区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本文拟从矿区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出发,探讨实现矿区生态产品价值的多种路径,总结不同类型矿区的治理修复重点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背景
2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中首次提出生态产品的概念,即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生态产品是我国特有的概念,狭义的生态产品概念与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调节服务类似。广义的生态产品概念,还包括生态农产品、生态旅游服务等[4]。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等要求。2021年4月,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建设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价值评价机制、经营开发机制、补偿机制、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和价值实现推进机制。自2016年起,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先后开展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部署,取得了一定成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
2 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探索
2.1 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夯实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基础
2019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自然资规[2019]6号),从国土调查、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土地利用、废弃物料利用等角度,提出据实核定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引领、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鼓励矿山企业综合修复利用、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合理利用废弃矿山土石料等矿山生态修复政策路径,从6个方面尝试破解矿山生态修复面临的重大问题。矿山生态修复为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奠定了政策基础,只有将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加以修复、利用,才能实现生态产品的正向供给,形成保护-修复-利用的良性循环,彰显自然资源价值。
2.2 聚焦资金筹措,推广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研究
2020年11月,自然资源部印发《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案例(第一批)》,收集了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土地综合整治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4种类型共10个案例[5]。其中包括以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建、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发展结合、与脱贫攻坚融合、生态修复带动旅游业发展等模式。通过修复后与资源利用、产业发展等的结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多种形式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其中,以矿山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为多数典型,介绍了实践中山东威海华夏城、安徽淮北市金湖采煤塌陷地治理、云南大板桥矿山、浙江长兴县原陈湾石矿、河南辉县市废弃矿山、山东青岛莱西市矿山等推动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做法,以矿山生态修复与资源利用及与相关产业发展结合的方式,探索了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
2.3 立足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统筹开展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研究
2020年4月-10月,自然资源部先后发布了两批21个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总体归纳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四种模式,向全社会鼓励、引导保护生态环境[5]。一是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类。类似于国外的规划管控+市场交易(cap+trade)或强制性抵消补偿计划(offset)。通过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创造市场需求,以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和政府管控下的指标限额交易为核心,通过直接、间接的生态产品交易实现资源价值。二是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类。通过生态修复、系统治理和综合开发,恢复受损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增加生态产品供给,采取优化国土空间布局、调整土地用途等政策发展接续产业,实现价值外溢。三是生态产业化经营类。综合利用政策工具,发挥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生态产品价值附着在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价值中,促进价值实现。四是生态保护补偿类。各级政府或受益地区以资金补偿、园区共建、产业扶持等方式向生态保护地区购买生态产品,确保生态优势的价值转化。两批案例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提供借鉴。其中,列举了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山东省邹城市采煤塌陷地治理、河北省唐山市南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河北省唐山市南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河北省唐山市南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河北省唐山市南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等生态修复+价值外溢典型案例探索实践,总结了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行路径。
2.4 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价值显化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中,包含大量的矿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问题,通过整体规划、系统综合治理的方式,能够将矿山生态修复融合到整个项目、区域的综合性治理当中,充分发挥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及修复价值的聚合效应。2016-2018年,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分三批共支持了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计划总投资约2000多亿,其中中央奖补资金500亿。与以往单项生态修复工程不同,工程试点是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实施的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生态保护修复活动,积累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经验。通过系统性、全流域、大尺度的工程实施,充分挖掘与生态系统难以分割的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依托于土地政策、金融工具、产业发展等,多渠道拓宽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对优美生态产品的需要[6]。
3 促进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启示与讨论
我国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模式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初期,聚焦矿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优质生态产品输出等问题,是实现矿区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所在。
3.1 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开展
充分调动矿山企业积极性,切实解决矿区的用地、监测监管等实际问题,积极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开展,为矿区生态产品输出创造基础条件。另一方面,针对历史遗留的矿山废弃地修复,应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率与作用,助力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多种途径促进矿区生态产品价值的开发和利用。在矿区生态产品价值收益分配方面,充分考量主体积极性和对生态产品价值创造的贡献度,进行差异化政策制度安排。
3.2 大力推广典型案例实践,利用成功经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修复
无论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还是从我国各地开展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工作的实践案例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必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通过总结国内外典型案例,能够认识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是促进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可持发展,增强矿区生态产品产出与价值实现的重要举措。社会资本通过工程实施、获取补贴或间接参与收益分成等多种方式,形成相应的盈利与商业模式,逐步形成并拓展市场预期,真正成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力量,推动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多种实现方式。
3.3 针对矿区特点深入开展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与核算研究
目前,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资产等概念繁多,相关概念间的内涵外延和相互关系尚未达成共识。且基于矿区生态产品价值的探讨少之又少,需要根据有关的管理学、经济学理论基础与原理,深入探讨矿区范围内生态保护修复的特点,及不同矿种可能输出的生态产品及价值提升路径。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面,如何计算矿区生态产品的直接、间接价值,统一核算标准,也成为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3.4 不断提升采矿科技水平,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矿业开采与复垦的全生命周期
从矿业开采初期,引入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矿区开采规划与后续的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输出和价值实现统一进行设计、考量,将矿区开采-复垦-产业发展做全生命周期分析与规划,避免走损毁再复垦,破坏再修复的“被动修复”老路,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坚持源头控制、绿色开采、综合系统治理修复,在最小程度破坏生态环境前提下,保证矿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矿区生态产品价值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