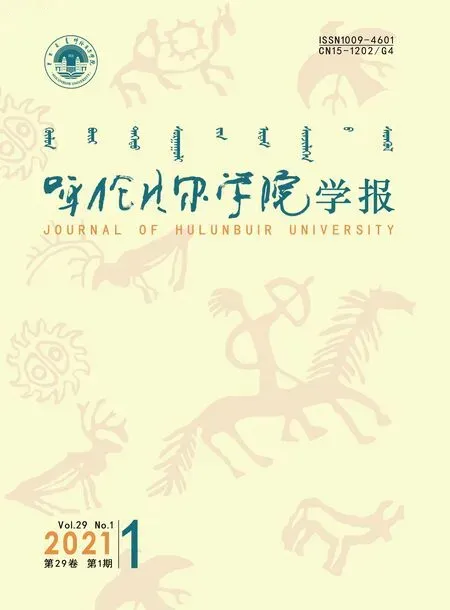崇高及其限度
——论乌热尔图小说中的主体生成
戴 琳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乌热尔图,上世纪80年代国内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曾凭借1978-1992年间的创作,多次斩获主流文学的奖项。在许多文学史叙述中,乌热尔图被归于“寻根文学”作家群体。他笔下流淌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现有研究也自然关注他作为鄂温克文化阐释者的面向。这些论文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偏重挖掘小说蕴含的宗教意识,图腾形象或原始仪式,评估其具有的民俗学、人类学价值。①也有人运用生态批评的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乌热尔图极具生态学的警示意义。②
“民族-作家”的镜像结构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存在于论述中,构成了乌热尔图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因为这个认识框架既是研究的前提,也是大多数研究的结论。反思以往的研究,我们必须再度真切地走进文本之中。这要求我们首先悬置起阅读积习,以更感性的心态去注视细节。
一、作为精神象征的图腾
观察人物的建立,不妨先从图腾视角切入。“图腾”是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概念。涂尔干认为,图腾就是用来命名氏族、群体的动物或植物,它们与群体而言具有凝聚性的象征力量。在小说中,乌热尔图则有意运用动物形象,把它们“图腾化”,将崇高的情感寄予其上。人物常常通过对图腾的认识、遭遇和记忆,获得部落推崇的精神气质。
(一)“鹿”与生存经验
在使鹿鄂温克部落中,鹿是生活经验中极为核心的要素。在早期《鹿啊,我的小白鹿》(1980)《七叉犄角的公鹿》(1982)等小说中,作家选用“成长小说”模式,以人物的沿途遭遇构成情节的动力。作家笔下,孩子们都是以寻找鹿为出发而完成成人仪式。《七叉犄角的公鹿》对鹿的生活习性有详细的描述。小说中,叙述者“我”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猎手,带着勇气,独自放足于凶险的森林。在发觉鹿的行踪后,“我”便一路跟随。于是,故事就演变成一场关于追随的仪式:“我”从隐蔽处观察鹿,见证鹿与狼的搏斗,闻着鹿特别的气味。鹿是“我”追随的目标、狩猎的对象,同时也是“我”精神勇气的投射对象。
《鹿啊,我的小白鹿》中讲述两个小孩儿对鹿的追寻。川鲁和岩桑一路跟踪小鹿,当他俩感到饥渴,但是没有带锅而无法烧水。整个故事,在讲述追寻小白鹿,但也是在讲述两个孩子如何借追寻的契机练习生存、实践技能。鹿不仅是一个狩猎目标,它还启动了青少年主人公的自我认知。烧好茶后,岩桑得意地说到:“这是从爷爷讲的故事里知道的。过去,很早很早的时候,咱们鄂温克人的祖先就是这样烧茶喝的。”③传统是记忆,也是此刻必需的生存手段。岩桑认出了由爷爷所代表的、由积累的生存经验而形成的族群记忆。寻鹿带来丰沛的结果,其中之一是岩桑的认识超越了此时此地。那一刻好像爷爷、孩子、鹿以及更多的鄂温克人在森林中,共同围绕茶火而坐,连结为一个超越时空的共同体。
(二)“熊”与精神力量
在精神象征的意义上,“熊”是另一个在乌热尔图小说中了占据分量的角色。《丛林幽幽》(1993)里,主角额腾科的身体、行动就时刻关联着熊。额腾科不同寻常,身形如熊,充满着雄性荷尔蒙,代表着男性的生殖力量。但由于额腾科被认为是不洁的孩子,他的力量总是处于压抑之中。在营地,人们对他始终抱有敌视。再加上乌里阿老祖母也是被熊掳走的,让这种敌意尤甚。但当他被人们驱逐之后,营地竟陷入了不详之中,直到一位萨满出现后才改善。这位萨满揭示了真相:人们之所欲遭遇不幸,是因为他们的记忆是残缺的。唤回的记忆终于道破了额腾科的寓言和真相。萨满在入神时提示额腾科实际上是光芒而神圣的存在。人们通过重获的记忆,也认出了额腾科是森林生殖力、生命力的代表。如此,过去的记忆、仪式被重新找回,并帮助治愈当下的创伤。经历曲折之后,族群文化被更深邃地刻写进族群成员的记忆中。小说有一个细节引人瞩目,暗示作家在创造人物时具有的宗教思维。当掳走祖母的熊被杀死后,人们发现这头熊竟带有老祖母的遗物。若根据《金枝》对于交感巫术的解释,人跟事物可以通过食用或使用来产生联系,并将自身投射到物品上。将人身与事物连结起来可以延长人的生命;也可以从通过杀死或者食用这种事物、动植物,获取其代表的精神象征力量。④当熊孩与母亲合力杀死巨熊,人们又在巨熊体内发现死去的老祖母的遗物时,一种隐秘的血脉连续起来。整个关系表现为“老祖母-巨熊-妻子-熊孩”这一血脉连结。因此也不难理解,熊孩一旦被驱逐而脱离这一连结,总有伦理的破坏降临。通过反向的宗教逻辑,也就是证伪的情节,作家建立了熊和熊孩代表的象征性力量。
二、 英雄的再造
在乌热尔图笔下,“鹿”和“熊”不仅是森林常驻的生灵,而且担当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出发点。不过出发之后,人物主体的真正生成还仰赖于人物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广义上的行动诉诸于人物的言语、神情、动作,以细节的生动性透视人物个性,彰显他们的存在。
(一)追寻图式与主体
乌热尔图的多数小说都以儿童作为故事的主角,“追寻”是它们共同的主题。如前文提及的,主人公通过寻鹿来习得鄂温克的生活习惯,实现一种精神上的蜕变。纵观他的创作,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追寻”作为契机为情节提供动力。若从几篇小说的叙事目的、叙事阻力和叙事结果进行分析,便能清晰看到人物行动的要素构成。
如表1中列举的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怀揣着强烈的动机出发。他们或寻找,或追击,或为奇异的事情困扰而企图找到背后的原因。作为小说情节的一种完整结构,图式讲求完整性,具有美感效果。乌热尔图对情节的完整性有一种偏好:人物经历一番波折之后,必定抵达某个终点。作家对完整图示的偏好,也是对人物精神完整性的偏好。诚然,“完美图示”带来故事的完整性,但它并非小说水准的保证——人物因此会单薄。小说理论家福斯特认为图式的建立虽使小说具有完善的结构,但必须付出牺牲人物复杂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审视乌热尔图的创作会发现,他许多的主要人物都分享同一种性格,完善的图式造就了人物的英雄气质和美好品格,但也使得他们沦为“功能人物”。

表1 叙事结构表
(二)“文化间性”中的人物行动
大多数汉语读者会下意识地把乌热尔图的小说当作鄂温克的“真实”反映,然而在细读下会发现,鄂温克部落的世界杂芜丛生。“文化间性”常被用作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分析,但在乌热尔图那里,这个概念也发挥着作用。《琥珀色的篝火》(1983)的主人公尼库的妻子病重,他正带领妻子和孩子前往医院,跋涉在灌木丛中。途中他发现林中有人的踪迹,凭经验他立马就判断一定是外乡人在森林中迷路了。对此他表面若无其事,心里一直担心:因为不掌握林中行路的技能,他们很快就会因缺乏食物而毙命。然而这时,他若去救迷途者,妻子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他一度陷入两难境地。最终,他决定先去拯救迷途的外乡人。
主人公尼库返回救助时,小说以十分详尽的动作描写来展示他的对森林的熟稔。这些描写用意明确,短促的句子是为配合尼库行动时身手敏捷、干净利索。作家不惜笔墨地说明主人公劳动量之大,能力之强。但作家也为尼库赋予另一层特别意味。它使原本属于生存所需的劳动,带上了某种“表演”涵义。首先,尼库返回是为救助“城里人”,而他所使用的技能于后者恰是陌生而奇异的。他们的遭遇也是两种文化的遭遇。尼库救助“城里人”不啻是一个隐喻,提醒我们必须在文化间性的关系中去解读主人公的一系列行为。除道义之外,尼库对他眼前的被救者似乎有一种暗中诉求。小说写道,在他安顿好“城里人”后,“他最后望了他们一眼。他想:有一天,在他们的城里见面,能认出他来,就行了。”⑤他以回望向“城里人”索取另一样东西:尊重。这种无声的诉求邀请我们想象另一幅场景:某一天尼库到了城里,那他是否能被城市人报以今日般的尊敬的目光?不论如何,在离别之际两者之间、两种文化文化之间目光的询唤,催生了一个人格平等的场域。
三、“时代语境”中的主体性
如果说,文化间性的角度主要从小说内部透析写作动机,那把作家放在时代语境之中则能看出更多外部关系。“时代语境”提示研究者去追溯作家写作的语境,看他如何与彼时的思想、情感互动。作为民族文化的“阐释者”,乌热尔图自身的心路历程也像一个文本,属于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
(一)故事内外的语境
尼库的行动除却“文化间性”之外,小说实际上还暗示山外已是一个“现代”的世界。历史的维度被作家有限地暴露出来,这种特征在其它的小说中同样存在。人物在森林中踏上精神追寻之前,实际上常常都是刚从外界的失落中返回。而山外的世界不仅是空间上的异域,还总粘带提示着时代气候。尽管小说的主角是林中猎民,但是他们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外部历史的回应,包括劳改、“文革”、抗日战争等等。森林人物总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中生成,尽管后者总是被做了虚化处理。而这些被轻描淡写的部分,在作家文学精神的源头处也可瞥见。
乌热尔图的文学源头,首先是他对鄂温克母族的体认。在自传性散文《我在林中狩猎的日子》(2012)中,他回忆了与鄂温克产生认同的时刻。在他的描述中,那是具有启示意味的时刻,意外、神秘,但又命中注定。他的认同产生于对母族口语的听觉回应。他写道,他与父亲重逢在根河车站,那里人声嘈杂。但拥挤的车厢里,鄂温克语使他感到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开朗明晰。鄂温克语如同一道亮光,让他“不再惧怕任何威吓与欺侮了”。这里的“何威吓与欺侮”并非泛泛而谈,而有特定所指。乌热尔图在“文革”期间命运多舛,遭受了许多精神创伤。对17岁的少年乌热尔图来说,他工作和精神上受到打击都是深刻的。散文中写道他因为政审条件不好,没有分到好的工作而只能孤独流浪。我们不难理解,少年乌热尔图与父亲重逢也是他与母族相认的时刻,孤独的心灵被鄂温克母族接纳——这完全是由于精神抚慰所需。
(二)不合时宜的人物
作家的心灵经历让我们想到,他的小说人物总能在狩猎、追寻行动中,克服来自外界的种种精神压力和创伤。他带着记忆写作,许多成长小说也带有自画像的影子,笔下的人物也好像回荡着历史的余音。但是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历史叙述的年代,而是叙述历史的年代。
乌热尔图创作期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也就是现在被普遍称为“后社会主义”或“后革命”的时期。80年代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年代,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开放,所谓的“理想主义”也遭遇没落。但也有学者如贺照田指出“理想主义”的失落在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发生。⑥。80年代精神主体的失落就已经开始蔓延,只不过等到90年代整体新的破碎更为剧烈。在这样的精神语境下,重审乌热尔图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光亮,能发觉他与主流思潮对话的意图。不妨把他的人物与“新写实”小说对比,后者清晰地反映了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价值观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新写实”以市民生活的平常琐事为主要题材,鲜有激动人心的传奇。“新写实”充斥着个人生存的矛盾,理想主义消失地毫无踪影。反观乌热尔图的同期小说,主人公充满力量,始终持有一个明确而神圣的行动目的。与许多作家在技巧和思想上走向现代主义不同,乌热尔图继续用一种前现代的传奇手法在塑造“典型人物”,用以回应理想的崩塌。作家的迥异的创作思路中,显然内蕴着一种对现代性的回应。不过,同执着于“完美图式”而造成的后果类似,作家的“典型人物”也有过于简化的缺点。当时代的气候作用于作家时,他缺少一种更内在的转化意识。在现代性的腥风血雨中,他让人物紧握“崇高”的剑柄,但这种崇高缺乏心灵的逻辑依据。
结语
乌热尔图在鄂温克族文学创作上发挥了开荒者的作用。他在《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中认为,族群的外来者并不具有权力去篡改他人的形象。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自我言说和阐释是不能让渡的。乌热尔图写道:“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释的渴望,使生活在人类早期社会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自我阐释的权利存在于他们之中,存在于他们全身心溶入的部族意识里。”⑦因此,他提出著名的“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说明来自族群内部的阐释的合法性。
然而,对乌热尔图的“民族化”评价,终究是落入了循环阐释的二元结构中。姚新勇追问到:“究竟存在不存在绝对、纯粹、天然的民族文化之声?”⑧他进一步指出,强调本民族的尊严固然不错,但是分析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不应该武断地把问题与某种本质化的民族特性相联起来,也不应把问题的判断局限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中。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已看到乌热尔图小说中主体的复杂性:他们是孤独的,但处于文化间性的关系中;他们行动利索,但携带着时代的创伤记忆;他们看起来昂扬崇高,但更多是一种先验气质。从作家本人的传记看,他民族意识的生成伴随着驳杂的历史经验,只有考虑到他少年时代的革命遭遇,才能深刻理解他对鄂温克的追寻。在“自我阐释”性质的档案化写作中,被转码的不仅有族群内部的经验,族群以外的力量也无形地渗透其中。鄂温克之外的力量像一只手,无形中影响着作家思想。因此,乌热尔图自诩的“自我阐释权”也并不是“纯粹”的鄂温克的阐释之音。在族群与外部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个人经验与时代语境之间、小说写作与历史写作之间,充满着动态的能量的交互。乌热尔图的小说写作,就是这些多种力量博弈、制约、互动的结果。
注释:
①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王澜:《落日余晖的笼罩──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文化思考》,《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陈钰:《鄂温克文学的话语转型和建构——以乌热尔图的创作为例》,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3年;孙洪川:《鄂温克民族灵魂的雕塑——论乌热尔图“森林小说”中的猎人形象》,《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王云介:《论乌热尔图小说的性别角色》,《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6期;杨兰:《乌热尔图作品中的老人形象浅析》,《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04期;卜晶磊:《乌热尔图小说(1983-1993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王建芳:《乌热尔图小说意象论》,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1年。
②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王静:《自然与人:乌热尔图小说的生态冲突》,《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王云介:《乌热尔图的生态文学与生态关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
③乌热尔图:《鹿啊,我的小白鹿》,《七叉犄角的公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④关于“交感巫术”的理论阐释,详见于:[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汪培基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⑤同上,第60页。
⑥贺照田:《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⑦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2月。
⑧姚新勇:《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第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