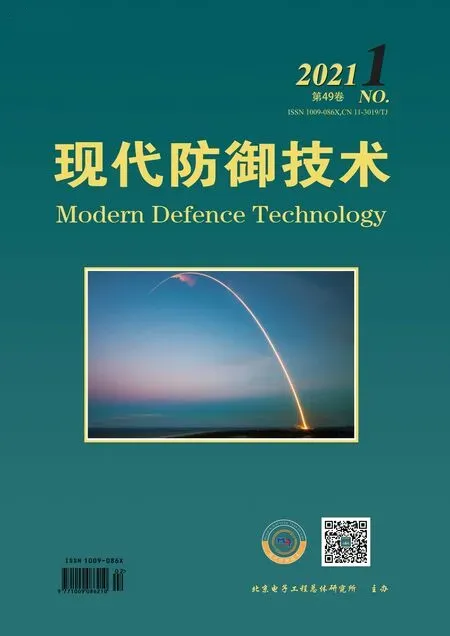美国国防采办中的需求生成机制*
宗凯彬,张承龙,薛晨曦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北京 100854)
0 引言
国防采办是指利用国防预算开展的国防建设活动,以实现战略规划中确定的目标[1]。按照美国国防部定义,国防采办是指武器系统或其他系统供应品、劳务(包括建筑)的方案论证、立项、设计、研制、试验、签订合同、生产、部署、后勤保障和退役处理等一系列活动,旨在满足国家防务需求[2]。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国防采办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采办对象(如武器系统等)全寿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同时其本质目的在于满足国家防务需求,实现战略规划中确定的目标。因此,对国防采办而言,其最早期、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便是需求生成,通过明确未来国防建设的顶层需求,为发展规划指明方向,同时也为后续各采办阶段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牵引[3-4]。
由于国防采办属于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其内部涉及的流程环节众多,参与单位广泛(通常横跨多个军兵种,涉及众多防务承包商和专业科研机构),且彼此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因此经常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2,5]。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用系统工程理论[6],通过构建一套结构完整、步骤清晰的方法论对采办过程予以指导,才能确保整体流程的平稳、高效运转;而需求生成作为国防采办的早期环节,也必须采用此种方法进行建模和描述,理清顶层论证的基本流程,并最终固化为国防采办体制机制[7-8]。因此,本文将对美国国防采办中的系统工程方法和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相关领域工作开展提供有效借鉴。
1 需求生成方法论
在国防建设领域,需求生成通常是指以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根据未来一定时期内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采用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工程理论、方法、模型、工具等,以能力建设为核心,详细描述待开发系统及其行为特征和相关约束,为提出武器装备建设需求而进行的一系列分析推理过程[9],其活动主要包括收集并分析客户要求、对系统各项功能及非功能需求进行规格说明,并形成需求文档等,同时对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演进给予支持。
为了支撑上述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需求生成领域内已出现多种具有实践意义的开发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结构化方法、面向对象方法、场景驱动方法和形式化方法[10]。结构化方法主要采用自顶向下、逐层分解的方式定义需求,通过明确需求抽取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和处理方法,确保抽取质量,最终形成完整、一致、无二义性的需求信息[11]。
面向对象的需求生成方法主要从系统组成方面入手,对问题进行分解,其核心在于利用面向对象的概念和方法为潜在系统需求建立模型,广为人知的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就是该领域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10]。
场景驱动方法(也称use case maps,UCM),最早由加拿大Carleton大学研究人员提出,该方法从用户设想或期望的目标入手,通过提供一系列可视化标记(包括路径元素、责任、构件等),构建场景的图形化表达,从而令使用者能够在较高抽象层级上理解系统行为[12]。
形式化方法主要采用数学语言表达系统需求,通过使用数学符号、法则等对目标系统结构及行为进行描述、推理和分析,使需求模型中含糊的、不完整的、矛盾的以及无法实现的表述能够被准确发现并尽早纠正,最终形成统一、完备的系统需求集合[10]。典型的需求生成方法汇总如表1所示。

表1 需求生成方法汇总Table 1 Summary of requirements generation methods
美国的国防采办体制历经几十年发展,几经改革变迁,在多年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一整套科学、完整的需求生成方法,以指导其采办过程中的项目论证。具体而言,美军的需求生成方法在充分借鉴结构化方法、场景驱动方法和形式化方法优点的基础上,以国家战略为指导,以作战概念为核心,自顶向下定义需求,在逐层分解的基础上不断迭代,并通过模型化方法进行表达,从而在需求逐步细化的同时,确保生成结果的有效性。
在需求生成过程中,美军充分运用系统工程理论[13],通过构建业务或使命分析流程、利益攸关者需要和需求定义流程、系统需求定义流程和架构定义流程,完成由国家战略到作战概念,再到系统需求和系统架构的有效转变,最终实现对装备发展的有效牵引和对国家战略的有力支撑。
在业务或使命分析流程中,分析人员将依据组织的运行意图开展业务/使命分析工作,明确任务的目标、假设及约束条件,并定义潜在的问题和机遇。在此过程中,分析人员还需识别主要的利益攸关者,并构建初步的生命周期概念,以便从运行者视角描述未来系统的工作方式。
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员将开展利益攸关者需要和需求定义流程,通过访谈、调研、焦点小组、头脑风暴和共情等方式,准确把握利益攸关者需要,并对其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和优先级排序。由于用户需要通常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将利益攸关者需要转化为需求(消除模糊性),从而形成对系统特性的准确描述,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对系统边界的有效识别,以确保需求定义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实现利益攸关者与系统开发者的共同理解。在此过程中,分析人员还需依据讨论结果,更新此前形成的运行概念文件,并进一步明确生命周期概念。
在明确利益攸关者需求后,分析人员将基于运行概念文件,将用户需求转化为项目团队可理解、可操作、可执行的系统需求,在完成需求细化分解的同时,实现由运行视角向能力视角的有效转变。通常用于实现这一转化的方法被称为质量功能展开(也称质量屋),该方法采用矩阵图解的方式,构建利益攸关者需求和系统功能间的关联关系,进而分析出哪些需求尚未满足,而哪些功能存在冗余,并通过对各条目进行量化评估和比较分析,支撑项目决策。
最后,基于经确认的系统需求,分析人员还需开展系统架构定义流程,以阐述未来系统可能呈现的基本结构。通常情况下,系统架构可分为功能架构、逻辑架构和物理架构3个层次,由于需求分析尚处于系统开发的早期阶段,因此该架构定义流程将以功能架构定义为主,其交付物主要包括运行图、任务流程图、组织图和信息流图等。同时,为了能够对不同架构进行比较分析,分析人员还需针对每种架构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如利用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法,FMEA),通过综合权衡各备选架构的成本、进度和效能等因素,实现对项目风险的有效管控,并从中选出最佳方案。
基于上述流程,分析人员将能有效识别系统能力需求、明确系统定位。通过开展需求分析论证,将使以此为基线开发的系统,既能满足用户需要,又可指导后续研制,从而为各武器装备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成功开发奠定基础。为了支撑上述流程,美军开发了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以确保各装备具备与生俱来的联合作战能力。因此,本文将以该系统为核心,对美军需求生成过程进行详细解读,并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支撑和参考。
2 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
2.1 系统概述
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是美国国防采办的三大决策支持系统之一,由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joint requirements oversight council,JROC)创建,以鼓励国防采办领域开展早期且持续的合作,并确保新能力的设计开发是在联合作战背景下展开的[8,14]。基于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美国国防部将能定义满足未来战争需求(包括能力、互操作性等)的最佳方式,其核心目标在于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CJCS)和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完成对联合作战能力的识别、评估、验证及优先级评定工作,同时确保其满足相应的性能指标,从而支撑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并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履行其法定职责提供系统性方法。
在操作层面,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采用基于能力的方法,由宏观的发展战略、作战概念,到中观的能力,再到微观的解决方案,不断深入细化,逐步实现由作战任务和作战需求,向能力需求、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的递进转化,进而明确当前或未来存在的能力差距,以指导国防部和有关机构做出决策,并为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提供有力支撑。
2.2 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
按照美国国防采办体制,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负责创建、使用和管理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该委员会是美国国防部为加强用户参与装备采办过程、密切作战部门同装备采办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成立的一个军事需求审议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军种管理部门同作战指挥部门在装备采办过程中的合作[15]。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共有5名成员,其法定负责人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但具体工作通常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导;其他成员则由来自陆军、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各一人),且具有将军军衔的人员担任,通常为各军种副参谋长、副作战部长或副司令。联合参谋部J-8局局长(Director J-8,DJ-8)任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秘书,而联合作战司令部代表可以顾问身份受邀参加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会议[16-17]。
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采用三层组织架构,从上到下分别为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联合能力委员会(joint capabilities board,JCB)和功能能力委员会(functional capabilities boards,FCB)。其中,联合能力委员会由联合参谋部J-8局局长领导,主要负责审查功能能力委员会提交的资助项目和相关文档,并就审查结果向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提交建议书。
功能能力委员会由联合参谋部J-8局副局长(Vice Director J-8,VDJ-8)领导,该委员会是一组委员会的统称,其中各委员会按照不同的功能领域设立。在能力识别与分析方面,各功能能力委员会将在其责任领域内,对联合作战能力展开分析研究及优先级评定,为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和联合能力委员会开展概念开发、能力识别和武装力量建设等提供有效支撑。
在能力验证与评估方面,各功能能力委员会还将就如何提升联合能力提供评估和建议、检验已有和未来项目的优先级、评估替代性方案、减少军种间重复工作、并监督装备与非装备管理变化,从而保障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的执行取得最佳效果。
2.3 系统组成与系统流程
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工作流程可分为5个部分,分别为构建联合未来概念集(the family of joint future concepts)、开展基于能力的评估(capabilities base assessment,CBA)、批准初始能力文档、批准能力开发文档和批准能力生产文档,其中前2个部分是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核心,充分体现着基于能力的分析过程。
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2.3.1 联合未来概念集
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采用自顶向下的分析模式,该系统以国家战略为指导(包括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NDS)、国家军事战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NMS)和四年防务评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QDR)等),基于战略中设定的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环境、威胁分析结果,生成面向未来战场的作战概念和作战想定,阐述未来战争将在何种环境下、以何种方式具体展开,给出潜在对手可能采用的作战样式,并分析可能由此产生的影响和风险,从而为高层领导和规划人员提供有关未来战场的场景描绘,并将其作为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设计输入。这种对于作战概念和作战想定的描述在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中被称为联合未来概念集。
按照美军定义,概念(concept)是对某个想法的陈述或表达,其中阐述了完成某件事的具体方式;而联合概念(joint concept)是对未来作战的一种描绘,其中刻画了指挥官将如何运用武装力量和科技实力来达到期望的作战效果。在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中,联合未来概念集(the family of joint future concepts)是一系列未来的联合作战概念,其中包括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作战概念和联合功能概念。具体而言,联合作战顶层概念(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CCJO或joint operations concepts,JOpsC)是指导联合作战力量能力发展的总体概念,其中全面描述了未来8~20年内,联合作战力量将如何在所有作战域内开展作战行动;而联合作战概念(joint operating concepts,JOC)是对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在某个特定任务领域内的进一步细化,其中详细阐述了未来8~20年内,联合作战指挥官将如何在军事冲突中组织开展作战行动。在此基础上,联合功能概念(joint functional concepts,JFC)将对联合作战概念(JOC)中描绘的作战行动做进一步说明,并初步识别用于支撑相关行动的能力需求。
在联合未来概念集之外,各军种还有自己的军种作战概念(concept of operations,CONOPS),这些作战概念主要从用户视角出发,对装备/系统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方式进行描述,其内容主要针对近期急需解决的问题(未来7年内),并生成相应的能力需求,同时允许对现有能力进行调整和更改。
2.3.2 基于能力的评估
基于联合未来概念集中描述的作战概念,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将开展基于能力的评估(capabilities base assessment,CBA)过程,其中包括功能领域分析(functional area analysis,FAA)、功能需求分析(functional needs analysis,FNA)和功能解决方案分析(functional solutions analysis,FSA)3部分内容,以下将分别展开说明。
在功能领域分析部分,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以联合作战为背景,面向真实战场环境下的兵力运用,将输入的作战概念和作战想定不断细化,逐步将其转化为需要依托武装力量完成的作战任务,同时明确军种间的职责分工与配合关系,进而将各项任务分解为所需的能力支撑,最终确定为实现作战概念和作战想定所需的全部能力集合,并依据一定标准(如作战需求的急迫性、可负担性等)给出能力需求的优先级排序,而其分析结果将集中体现在通用联合任务清单(universal joint task list,UJTL)中。
通用联合任务清单(UJTL)的基本样式如图2所示[18]。

图2 通用联合任务清单Fig.2 Universal joint task list (UJTL)
基于上述成果,美军将对现有和在研的武器装备及信息系统展开能力评估,系统梳理所能提供的作战能力,并与通用联合任务清单中描述的“能力-任务”网格进行对比,确定当前存在的能力差距(capability gaps)和能力冗余,从而为后续的能力开发与精简提供指导。对于存在的能力差距,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对其可能带来的、潜在的作战风险展开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给出能力差距的优先级排序。若潜在风险较低,则国防部可以选择接受风险,无需进一步处理;若潜在风险较高,则需要开发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弥补能力差距。这一过程在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中被称为功能需求分析[19]。
在此基础上,针对每项能力差距,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组织开展相应的解决方案分析工作,以寻求弥补能力差距的最佳方式,这一过程被称为功能解决方案分析。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美军对解决方案的定义早已超出了武器装备和信息系统的传统范畴,其内容同时涵盖了装备解决方案(material solutions)和非装备解决方案(non-material solutions)2个层面。对于某项能力差距,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首先考虑可能的非装备解决方案,此类方案主要从条令(D)、机构(O)、训练(T)、装备(M)、领导和培训(L)、人员(P)、设施(F)和政策(P)等维度,对当前的国防采办体制展开分析研究,以寻求能够满足联合能力需求的综合DOTMLPF-P改革方案。
当非装备解决方案无法完全弥补能力差距时,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致力于寻求装备与非装备的混合解决方案,通过开展相应的武器装备和信息系统采办活动,来获得综合改革方案无法提供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在混合解决方案的开发过程中,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不但要开发装备与非装备解决方案,还要兼顾装备解决方案对综合DOTMLPF-P改革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非装备解决方案无法产生效用时,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完全依赖装备解决方案。此类方案的开发过程将始终以联合作战为背景,通过开展跨机构合作,来确保相关装备/系统具有“与生俱来”的联合基因。基于这一过程,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获得有关装备/系统的初步构想,以及必要的系统属性和具体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能力差距的种类和范围多种多样,因此对于每个功能需求分析的结果(即每项能力差距),都可能存在多个与之对应的装备或非装备解决方案。举例来说,当面临国土防空需求时,既可基于陆基装备满足需求,也可通过海基装备实现目标,同时还可考虑空基装备解决方案;既可选择自研新型装备获得所需能力,也可面向其他国家采购成熟产品。由于不同方案通常对应着不同的研制难度、开发周期和采办成本,因此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需要一套系统性方法,来协助其对不同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与综合权衡,从而做出最佳决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将对生成的装备和非装备解决方案展开综合分析评估,而这一过程就被称为装备/非装备解决方案分析(material/non-material solution analysis)。对于非装备解决方案,如果能力差距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则国防部有关机构将依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令3180.01(CJCSI 3180.01),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其分析结果将被记录在DOTMLPF变更建议书中(DOTMLPF change recommendation,DCR)。
对于装备解决方案,在进行方案分析时,不仅要评估解决能力需求的最佳方案,同时还要考虑利用装备解决方案获得联合作战能力的最佳方式,其分析结果将是一个综合的方案列表,通过仔细权衡每种装备解决方案的成熟度、风险、可负担性,以及对联合能力需求的贡献度,最终确定方案的优先级排序。为了对排序过程提供有效指导,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不同方案,按其对应的资源需求和风险等级大致分为3个类别,其选择优先级由高到低依次为:改造现有装备和系统、采用其他国家或机构的装备解决方案、以及启动新的研制项目[7,14-15]。对装备解决方案而言,其分析结果将用于生成初始能力文档(initial capabilities document,ICD),以指导后续的研制及开发工作。
通过采用基于能力的评估方法,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能以国家战略为指导,基于作战概念和作战想定中给出的描述,将国家战略中设定的目标逐步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的“任务-能力”需求,再通过与作战能力(即现有能力)的匹配分析,发现现役及在研装备与联合未来概念集之间存在的能力差距和能力冗余,进而生成相应的解决方案。
2.3.3 审查、决策与输出
依据美国法典第10章,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拥有自由量裁权,可以审阅任何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文档,或审议其他需要联合解决方案的问题。为了对需求生成过程进行有效管理,美军按照需求对联合作战能力的影响程度,将其划分为5个级别,分别为: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关注、联合能力委员会关注、联合集成、联合信息与独立标志,并据此将工作分配到相应部门进行管理、审查与决策。
在工作流程上,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首先按需求涉及的专业领域,将审查工作分配给相应的功能能力委员会,并生成审查报告。在此过程中,功能能力委员会将充当总体协调机构,以确保联合作战力量能够通过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获得最佳的产品和服务。此后,联合能力委员会将依据审查报告对需求进行复议,并据此向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提交建议书,后者将基于上述材料完成对需求生成过程的最终审议和决策。
对于装备解决方案分析生成的初始能力文档,其内容通常涵盖环境与威胁描述、作战概念、能力需求、能力差距、解决方案、以及方案的分析评估等方面。在批准初始能力文档之前,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验证完成任务的能力需求、包含优先级排序的能力差距及其对应的作战风险,以及消除能力差距的方法和手段。
在初始能力文档审议通过后,国防采办系统(defense acquisition system,DAS)(三大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另一个)将正式启动[20]。在国防采办系统中,初始能力文档主要用于构建方案开发的边界条件,从而为替代性方案分析(analysis of alternatives,AoA)和保障方案的开发提供指导。随着采办项目成熟度的不断增加,其将经历一系列采办阶段和里程碑审查,而在此过程中,初始能力文档也将被不断细化,并依次生成能力开发文档(capability development document,CDD)和能力生产文档(capability production document,CPD),以牵引相应阶段的采办工作,并支撑下一次里程碑审查。
在方案细化过程中,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在国防采办系统协助下,识别出能够满足能力需求的核心指标,这些指标被称为关键性能指标(key performance parameters,KPP)和关键系统属性(key system attributes,KSA),其将被包含在能力开发文档和能力生产文档之中,并与项目目标进行关联。其中,关键性能指标还将在作战试验(operational test)中被用作性能度量(measures of performance,MOPs)标准。
具体而言,关键性能指标是指对于开发有效军事能力至关重要的系统性能属性(performance attributes),这些指标通常是在充分考虑技术成熟度、成本和进度约束的基础上,通过作战分析确定的。每一项关键性能指标都包含一个阈值和一个目标值,而两者之间的范围被称为权衡空间(trade space),其中阈值代表了在低-中等风险条件下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从而形成初始作战能力,若未能满足相关要求将可能导致采办项目失败;另一方面,目标值代表了期望达到的作战水平,但可能在成本、进度与技术指标方面面临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指标确定方面,关键性能指标将尽量避免重复,并可在不同的采办项目间实现复用。按照美军标准,采办项目通常可拥有3~8个关键性能指标,但由于随着指标数量的增加,采办项目在成本、进度与技术指标方面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因此关键性能指标一般保持在5个左右。
若某个属性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对满足系统核心目标而言相关性较弱,则可将其归类为关键系统属性(key system attribute,KSA);关键系统属性同样使用阈值和目标值进行描述,按照美军标准,强制性使用的关键系统属性一般包括可用性、可靠性、持有成本(ownership cost)等要素。
在批准能力开发文档前,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完成关键性能指标及其阈值和目标值的验证工作,同时还将评估为满足关键性能指标所面临的成本、进度和技术成熟度方面的风险,并对系统的可负担性展开分析研究,以便为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and execution,PPBE)过程提供相关建议[21]。在能力开发文档的审查过程中,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不但将考虑主要方案,同时还将考虑替代性方案,通过对所有备选方案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做出科学决策。
对于能力生产文档,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审查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采办项目在可负担范围内,能够满足初始能力文档中确定的具体要求,同时为开展相关生产活动做好准备。若采办项目无法满足关键性能指标中规定的全部阈值,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将评估该项目在作战层面的可接受性,若评估结果为无法接受,则该采办项目将被终止。
为了支撑基于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需求生成过程,同时对各种解决方案进行有效性评估,美军开发了国防部体系结构框架(DoD architecture framework,DoDAF)[22],该框架在图1中被称为“综合体系结构”。基于国防部体系结构框架,美军构建了能够有效支撑需求生成过程的信息化工具,通过构建各类系统视图(如全景视图、能力视图、作战视图等),完成了对需求生成过程的建模与描述,实现了由作战概念和基于能力的评估到各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文档的映射,从而有效支撑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履行其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是一个基于能力的系统(capability based system,CBS),通过该系统,用户可获得系统的、集成的、可互操作的装备或非装备解决方案,其输出(包括经验证的能力需求和性能指标)将作为防务承包商开发相应系统的基础,同时也将为作战试验鉴定提供必要依据。通过使用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美国实现了其国防采办体制由“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的有效转变,达到了通过能力需求牵引国防建设的总体目标。
3 美军需求生成机制的特点
(1) 坚持顶层牵引,支撑战略目标
美军的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始终以国家战略为输入,其中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等,这些文件系统阐述了美军未来可能面临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潜在威胁,以及需要构建的武装力量,并为需求生成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向指引;而所有后续分析流程则均以上述文件为核心,紧密围绕战略目标,开展作战分析工作,最终实现对战略内容的有效支撑。
(2) 坚持实战出发,深入研究战争
基于输入的战略文件,美军将深入开展作战研究工作,以文件中描述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潜在威胁等内容为基础,进一步明确未来战争中,美军将在何种条件下、与何种对象、展开何种规模的战争,并最终实现何种战后景象,而上述分析结果将最终体现在不同版本的作战概念中,从而使美军能够确定在未来战争中需要完成的作战任务,并为后续装备发展提供指导。
(3) 坚持能力导向,综合分析权衡
基于形成的作战概念,美军将通过功能领域分析和功能需求分析,明确当前为实现各项战略目标而存在的能力差距,进而完成由任务视角(或运行视角)向能力视角的有效转变。此后,美军将开展多方案比较权衡,以确定弥补能力差距的最佳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全面考虑包括非装备解决方案在内的各种可能。
基于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美军走出了“先列装,再集成”的发展误区,使系统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也使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能够基于该系统平衡各方利益,在科学规划论证(能力验证与优先级评定)的基础上做出最佳决策,并确保美国武装力量能够有效应对未来短期、中期和长期内的各类军事挑战。
4 结束语
为了实现需求生成对国防领域建设的有效牵引,理清由顶层战略和作战概念到能力差距和解决方案的转化步骤,本文从系统工程视角出发,对美国国防采办中的需求生成机制展开研究,从功能定位、管理机构和系统组成及流程步骤3个层面,对美军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进行了详细阐述,给出了一系列明确的、可执行的操作步骤,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并为系统工程方法在需求生成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