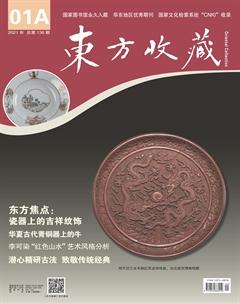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冯冕



读中国收藏家协会编著的《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十分欣喜(图1)。大系煌煌巨作,共12卷,收录藏品3120件(组/套)。所涵盖品种之多,囊括迄今所知陶瓷器全部品种;范围之广,自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涵盖包括港澳台在内全国各地域的藏品。收录藏品部分传承有序,更有精美和完整程度不逊色于国有博物馆收藏的,具有极高的资料性和学术性。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还没有一部通贯上下揽括全国,又兼具学术权威性的民间陶瓷资料。《大系》的出版或许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我国陶瓷收藏的面貌。
陶瓷是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涵极大,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审美等众多方面都与它有密切关系。它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显示着各个时期文化不同侧面的特点,以及时代变迁的方向。陶瓷史的研究,正是通过解码古陶瓷,来完成对历史叙述的补充。因此,古陶瓷无论是完整器还是标本,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资料。作为一名古陶瓷研究者,长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资料的缺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仅我国的博物馆都还处于全面建设时期,陶瓷考古也尚在发展阶段,能够以博物馆展出或出版书籍方式呈现的资料远不如今日之丰富。随着我国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勃兴,仍要面对大量古陶瓷在专业部门视野之外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标本流失的情况。以景德镇为例,景德镇老城区的南河沿岸几乎遍布宋、元、明、清的窑业遗存,但在市区建设过程中,一些标本残片流入民间,其中不乏涉及到学术前沿问题的证据。在早期古陶瓷研究中,我们并不排斥来自田野采集的,经得起学者们推敲鉴定的资料标本;随着古陶瓷考古研究范式的逐渐确立,为了确保科学性,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不采用非博物馆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这就使大量资料被排除在古陶瓷研究范围外。但这亦是不得已之举。现今民间资料鱼龙混杂,复杂程度远超上世纪末,若没有反复推敲鉴别,轻易使用则会损害研究的科学性。
如何在沙中淘金?这是新时代向古陶瓷学界提出的考验。
《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不仅吃了螃蟹,还拿出了一套吃螃蟹的方法。通过结集高校、研究机构及民间古陶瓷研究专家和藏家,各方力量,共同合作,对收录的藏品进行了严格鉴别筛选。分卷主编严格把关,实行一票否决制,总编辑委员会再组织专家就不同意见反复推敲,最后对于部分藏品,总编辑委员会还邀请各界人士进行“会诊”。即使在如此谨慎的情况下,《大系》还是反复强调“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真,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最大限度地预防赝品混进来。即便这样,我们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存疑现象,只能是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一次解决大量流于民间的古陶瓷资料如何利用的有效尝试。在专业权威的谨慎筛选之后,资料公布于众,更能促进真理越辩越明。《大系》的出版不仅是对古陶瓷学科研究资料基础的贡献,为古陶瓷研究引入又一源头活水;也有助于国有博物馆、民间收藏、私有博物馆三者间的沟通交流,建立起带动、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关系。以此来看《大系》可谓居功至伟!
辨别真伪虽至关重要,却仅仅是《大系》的基础工作。从《大系》藏品的编排来看,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各地古陶瓷收藏的特点和新发现。如江西福建卷中171页收录的景德镇皇窑陶瓷艺术博物馆藏的釉里红凤穿牡丹纹塔式盖罐(图2)。值得注意的是,与这对釉里红盖罐一同出土的地券(图3),有纪年“丁卯岁三月十三日”,编者认为应为元泰定四年(1327)。如能进一步证明其与同出土盖罐有共时关系,以及地券纪年确为泰定四年的话,就大大提高了此件器物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景德镇元末高温铜红釉和釉里红装饰的新产品,是对高温色釉和釉下彩装饰的巨大贡献,但这两种装饰工艺技术并不相同。古代景德镇配制釉里红是采用“铜花”(加工制作铜器时的铜屑的混合物或金属铜加热氧化的铜表面层制得)或铜灰(熔铜时铜液表面的一层渣滓)与溶剂配制而成;而铜红釉就是将铜金属氧化物的色料进行细磨,然后放入釉料中混合均匀制成。这两种技术是否有先后顺序,现有的资料尚不能解答。笔者曾发现元代乃至明早期一些看似为釉里红装饰的瓷器,实际是用铜红釉彩绘而成。1980年江西丰城发现的“至元戊寅”(1338)铭的青花釉里红四灵盖罐及阁楼式谷仓(图4),以及河北保定出土青花釉里红镂花花卉盖罐,都是铜红釉彩绘装饰的品种,而非釉里红装饰。因此江西丰城谷仓只能证明至晚到公元1338年,景德镇已经出现了高温铜红釉技术。但《大系》中这对釉里红盖罐,如能确定泰定四年(1327)为其时代下限,那则至少可以证明釉里红彩料装饰技法至晚在此时已经出现。这不仅能够对釉下彩装饰出现的时间段进行更精确定位,还能说明釉里红装饰略早于红釉装饰出现。高温铜红釉和釉里红工艺实为不同的技术逻辑,厘清两种工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理解景德镇窑高温彩和高温色釉技术的发展来说有重要意义。
除了高温彩绘以外,低温彩绘技术在景德镇的源起同样值得重视。眾所周知,元代是景德镇窑技术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此前景德镇主要生产单色釉品种。元代开启了景德镇高温、低温彩绘时代,为明清景德镇丰富的产品种类奠定了基础。一般学界都认为景德镇的低温彩绘技术是元代随北人南迁而来,但它究竟何时在景德镇生根发芽,还需更为精确的证据。
《大系》北京天津卷199页收录的天津荣禧古美术藏的景德镇窑弥勒像(图5),时代定为宋至元。这尊弥勒像的袈裟褶皱处还留有明显红彩痕迹。现有证据表明,景德镇低温彩到元代才出现。无论是湖田窑还是落马桥窑址,元代皆有红绿彩器物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景德镇窑影青加彩观音坐像,像底有“大宋淳祐十一年辛亥”(1251)的墨书纪年, 这件坐像的花冠与衣裙等露胎部的红彩明显与《大系》中的这件产品不同,是未经低温烧烤的红彩。《大系》这件弥勒像的时代确定尤为重要。如果它确实能到宋代,那么景德镇低温红彩的出现则可能提前。无独有偶,景德镇在2019年之际,出现了一批低温红彩的雕塑,大部分专家认为这批烤有红彩的器物应属于元代。丰富资料的揭露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正如《大系》所说,民间收藏往往具有原始信息较乱的特点,是这些资料不易被科学利用的原因。而且由于收藏器物只能从类型学的角度判断它们的年代和真伪,同考古发掘所得的器物在研究价值上不同。这种价值的损失太可惜了,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可叹!
每每翻阅此书,书卷所展现的排版设计、印刷装帧之精微,让人时刻感受到抚卷的愉悦。每件器物似乎透过色彩柔和而真实的图片将其身世娓娓道来。从此中细节亦可感到编者对古陶瓷研究、对民间收藏拳拳之情,不甚感怀!
——省景德镇老年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