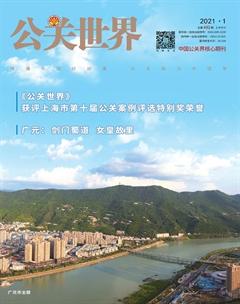行动承诺:公关中企业化解危机的策略
危机事件作为系统失控的信号,不仅需要企业倾注精力进行公关,挽回企业在公众心中的正面形象,还需要企业去主动反思内部问题。偶然事件或可简单地解释为管控不力,类似事件频发则可能如星星之火,迅速燃烧掉消费者的信任感。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消费者需要的不是千篇一律的道歉与保证,公关也不是通知公众,而是与公众站在同样的立场看待问题。因此,企业与其甩锅撇清自己,不如由危机事件衍生到企业管理制度,在通报中提出具体的处理措施和整改措施,不让道歉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于细微之处见真章,一场危机公关或许就能变为有迹可循的公关管理。
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先来汇总 2020年 12月值得记录的公关事件:

以下我们选择一些12月发生的代表性事件,以“公关黑白榜单”“危机处理警示榜”等形式来分析其在公关信息传播上的成败,分析其在复杂的公关信息传播生态中应注意的事项。
一、危机公关黑榜:哥老官陷入“食安危机”
12月15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了《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35批次不合格食品情况的通告》,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哥老官”杭州门店销售的一批次牛蛙被检出呋喃西林代谢物不合格,该涉事门店表示,检测出含有呋喃西林代谢物的同批次牛蛙已经销毁了。无独有偶,有媒体报道哥老官绍兴八佰伴店也被通报牛蛙中含有呋喃西林代谢物,且该批次牛蛙已于9月1日全部售尽。
由于呋喃西林及其代谢物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且留存时间长,长期大量食用含有此类药物的食品可能会诱发各种疾病,因此2002年农业农村部就已将呋喃西林列入禁用药。
食品安全问题向来备受公众关注,牛蛙中被检出禁用兽药的消息一出,#哥老官 兽药#等话题就登上了热搜。2020年餐饮业受疫情重创,但网红餐厅哥老官可能是少有被内部原因绊了个大跟头的,11月时被爆出后厨乱象后,未能痛定思痛、整肃管理,仅隔一个月后又因食品安全问题再上热搜榜,可谓是成也牛蛙,败也牛蛙。
然而,此次牛蛙检出禁用兽药并不是“哥老官”所用牛蛙第一次出现问题。
红星资本局在报道中提到,哥老官杭州其他门店在2018年、2019年销售牛蛙中曾被检测出禁用药物氧氟沙星和恩诺沙星。此外,该公司还在2019年11月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
但在12月16日,哥老官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的“牛蛙抽检报告”新功能中,以上有关监督管理局抽检的牛蛙禁用药物超标的通知并未列在其中,所提供的皆为检测中心或检测公司给出的合格结果。针对哥老官杭州龙湖滨江店事件,12月17日,在事件发酵几天后,哥老官姗姗来迟地通过微信公众号给出了回应,称涉事牛蛙送至哥老官杭州龙湖滨江店销售使用前,经杭州南开日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测,结果为合格。
哥老官在说明中表示,其采购流程索证索票均齐全,符合食安法相关规定。他们对于两次检测报告结果的不一致深感困惑和无奈,将等待相关权威检测机构给出最终的结果,并已与该供应商永久解除合作关系。
哥老官的回应看似合情合理,具体检测样本不同,同一批食材的检测结果有所出入并不少见,但不合理的是同一时间不同门店均被检测出呋喃西林代谢物,不合理的是哥老官近年屡次出现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
一个大流量的连锁网红餐厅,服务着无数顾客,本身应该更注重食品安全和连锁管理能力,但在此次哥老官杭州龙湖滨江事件中,其回应避重就轻,不反思内部管理问题,不去追溯牛蛙上游供应链的疏漏,反而以流程正规、符合食安法为由无视民众的呼声,之前后厨乱象所作出的食安承诺也沦为空口支票。哥老官企图为自己辩解,然而回避核心问题的做法终究让自己站在了消费者的对立面,相比之下,海底捞涨价被嘲后,官方主动坦承错误可谓是危机公关的典范,“我错了、我会改”加上行动承诺,及时而真诚的套路往往会被消费者所接受。
二、危机公关白榜:成都城市品牌公关
12月初,全面、严格的防控举措展现了成都的力量,一个又一个的白衣天使冲上疫情前线,一个又一个的基层防疫工作者坚守自己的岗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成都的各方力量都为战“疫”作出了贡献。这场“战争”不仅没有打垮成都,反而让更多人看见成都这座城市的力量。
其一,媒体的宣传与介入是树立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
自本土病例出现后,成都市紧急召开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土新增病例及近日行踪。之后,成都市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每日向社会大众公布成都的最新消息。及时、准确地发布病例近7日的行踪,有利于其他市民做好防范准备。同时,考虑到当代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四川日报官方微博每日都会发布成都最新消息,确保最大范围地传递信息。
在打赢防控阻击战中,媒体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12月8日,成都3例本土新增病例中一名女孩的行迹引起网友的热议。成都市有关部门公开确诊者的行踪本意是为了让相关接触者及时就医,防止扩散。然而,广大网友却本末倒置,指责、辱骂该名女子的私人生活,甚至有网友泄露该名女子的相关信息。这样的舆论氛围显然不利于防控工作的开展。当晚,央视节目《主播说联播》评论了“成都确诊女孩遭网暴”一事,指出“她的个人生活不该是公共话题,防疫才是。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感染疾病的人”。随后,多家主流媒体发文评论此事,引导舆论风向,将话题对准事件本身。
12月9日,成都确诊女孩发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向成都市民致歉”,不少网友在其评论底下鼓励她,为她加油。网络上的信息是肆意生长的,网民的关注焦点也是多角度的,这种信息传播模式需要媒体的介入与引导。有关疫情的信息公开是防控疫情的必要手段,然而在信息公開的同时,及时扭转舆论风向、把控信息走向,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事态的恶化。
其二,雷厉风行的防控手段是树立城市品牌形象的立足点。
成都人的生活节奏虽慢,但对待防控的行动却快。本土新增病例出现的前几天,是成都开展防控的关键时期。为了不让病毒有机可乘,成都快速发起响应,封锁小区、全员进行核酸检测、将相关城区列为高风险地区,严格把控相关城区的出入情况。本土新增病例的出现与数量上涨引起了成都市民的恐慌,部分网友趁机在网络上散布不实消息,谣传成都理工大学封校、成都即将封城等信息。在民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及时辟谣,稳住了民心。
12月7日晚,成都市建委抽调19个兄弟区(市)县1000余名医务人员,紧急集合到郫都支援核酸采样工作。截至10日18点,累计采样110万人,累计检测超104万人。12月11日,郫都区发布公告,将开展全区全员的核酸检测工作,确保不漏一人。检测费用由郫都区政府承担。庞大的工作量的背后是全体医护人员、基层防疫工作者和相关部门人员的艰辛付出。12月中下旬,成都公共卫生事件逐渐得到控制,但成都卫健委并没有放弃调查传染源头。12月31日,成都卫健委公布传染源头,为尼泊尔境外输入的病例,首发病例可能因接触了隔离点的垃圾导致感染。
其三,温情乐观是疫情中成都向外输出的名片
在这场突发的战“疫”中,成都向全国展示了温情而又乐观的成都精神。12月11日,凌晨,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3.2万人连夜做核酸检测,一名防疫工作人员穿着隔离服躺在草坪上休息的画面,刷屏了成都人的朋友圈。爱从来都是双向的。防疫工作者为广大市民的生命安全付出了努力,市民们也用自己的爱温暖着防疫工作者。12月11日晚11点,在成都机电工程学院的操场上,全校师生自发举起手机闪光灯,齐唱《听我说谢谢你》致敬医护工作者。病毒虽然无情,深夜虽然寒冷,但成都人却有情有温度。
过去,成都总是以“辣”“网红”“慢”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但在这场疫情中,成都拥有了更多的代名词,温情、乐观、坚韧、无畏……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不但没有打倒成都,反而让更多的人认识成都,见证成都的力量。
三、危机处理之组织警示榜:“阿里巴巴涉嫌壟断被调查”一案反映出现代生活便利背后的隐患
本月,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线上购物、移动支付的兴起极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足不出户便可满足生活的所有需求,然而这种便利的背后隐藏着资本垄断的深渊。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买东西上淘宝、饿了就上饿了么、买生鲜上盒马后,我们的消费行为已经被牢牢地掌控在互联网企业的手里。大数据的发展使得消费者的画像与行为在互联网企业面前一览无余,消费的主动权早已放在了互联网企业的手里。消费者只能看到平台让你看见的,购买平台向你推送的,消费市场中的买卖杠杆早已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入侵发生了变化。
12月17日,一篇名为《我被美团会员割了韭菜》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热议。文章的作者发现,自己在同一家店铺,用同一个配送地址,在同样的时间点单,会员的配送费比非会员更高。此文发出后,不少网友表示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时间,“美团被曝杀熟外卖会员”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榜。随后,美团发布回应称,配送费差异与会员身份无关。大数据杀熟的背后存在着价格歧视、独家交易、消费者权利被剥夺等问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规范。
12月24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国家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所谓的“二选一”指的是商家必须在两个平台中选择一个。如果商家想在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入驻,那么便不能在京东或其他平台上同时存在。这种涉嫌垄断的霸王条款剥夺了消费者在多个平台自由选择的权利。如今,阿里巴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旗下的天猫、淘宝、饿了么、高德地图等一众平台把握着大众的吃穿用行。如果有关部门不加以规范,任由这一庞大企业自由发展,将会对整个市场的良性竞争产生重大影响。
吃穿用行是大众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就是低需求弹性领域,俗称“刚需”。这一领域常常受到资本的青睐,比如已经形成垄断局面的两大外卖平台。资本往往会在早期拼命砸钱,让用户尝到“甜头”,在用户形成使用习惯后,开始回收早期成本。在互联网企业涉猎民生基本需求领域并获得成功后,资本的手开始伸向了民生菜篮子。12月24日,《半月谈》发文点评社区团购,认为社区团购在资本的助推下,高买低卖,以小规模资金轻易“控盘”地方社区生鲜采购等刚需民生领域,在形成相对垄断后,就获得了定价权,在后续运行中牟取高额利润。
不管是各大平台的大数据杀熟、阿里巴巴的“二选一”垄断,还是社区团购的资本化,互联网企业在其中都能分到一杯羹,资本垄断的背后伤害的终将是消费者和传统供应链上的普通民众。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此次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以及社区团购被点名,都意味着国家重视互联网企业的良性发展。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众多互联网企业应当以此次事件为鉴,规范自身,实现企业长足发展。
四、危机处理之名人警示榜:抄袭之风必将遏于新法规之下
2020年最后一天,曾经深陷抄袭风波的郭敬明公开向庄羽道歉,随后同样深陷抄袭泥淖的于正也在微博上向琼瑶进行道歉。两位名人时隔多年后的“悬崖勒马”,再次掀起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讨论。
郭敬明和于正从前拒不道歉,却纷纷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的前一天发文忏悔,我们很难将之视为良心发现的偶然巧合,网友们在“活久见”和“喜大普奔”的情绪之中,也有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道歉时间的选择上耐人寻味,将之视为2021年即将生效的著作权法条与行业自纠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12月21日晚,编剧余飞、宋方金等111位影视从业者发布了联名信,矛头直指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12月23日,新华社就百余位影视从业者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抵制有“抄袭劣迹”的于正、郭敬明的情况,对公开信的四位核心发起者进行了深度报道。次日,新华社继续追问:谁在给“劣迹艺人”提供粉墨登场的舞台?如何遏制资本把“劣迹”当卖点的不良行径?资本以及某些竭力为“劣迹艺人”粉饰的媒体应承担哪些责任?
12月31日,郭敬明和于正纷纷道歉。在声明中,郭敬明用“年少轻狂的虚荣和抗拒”“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来解释自己15年来为何不道歉,而于正也将不愿意承认错误归结于“缺乏内心的勇气”,一边打着感情牌,一边表示愿意对受害的原创者进行赔偿。
目前,琼瑶并未作出回应,庄羽于当日早上就在微博接受了道歉,但对郭敬明所说愿将《梦里花落知多少》出版以来线上线下的全部收益作为赔偿,或捐给公益慈善机构的表示,她站在了更高的道德层面,提议将自己关于《圈里圈外》线上线下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同郭敬明的抄袭所得收益,合并成一个反剽窃基金,用以帮助原创作者维权。
庄羽在郭敬明公开道歉的道德绑架下,杀了一个极漂亮的回马枪,反剽窃基金仿佛是在明晃晃地指责抄袭者多年知错不改,而无论内心是否有芥蒂,郭敬明能够选择的只有同意。但是,郭敬明对庄羽的回应里,犯了公关话术中极其低級的错误,短短几句话竟还附带引号。虽然郭敬明很快对微博进行编辑,删除了引号,但仍有部分网友认为,郭敬明就是在暗示所有人,这是公关发给我的,我道歉,但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了。
目前,郭敬明和于正已退出他们参与录制综艺,电影《晴雅集》于2021年1月6号全面下线,此外,还有传言称于正作编剧的《玉楼春》等影视剧也被延期上映。无论道歉方是否真心实意,这场旷日持久的抄袭与反抄袭的对峙僵局,在多重利益捆绑、多种因素作用的推动下,都以抄袭者受惩暂时落下了帷幕。
近年来,在抄袭难以判定且上诉费时费力的情况下,抄袭邪风甚嚣尘上,俨然已成为文化产业的沉疴。在众多被抄袭的原创者中,仅有少数能够得到公正判决,而涉嫌抄袭者追名逐利,在行业内赚得盆满钵满,即使被法院判定抄袭,也只是赔钱了事,拒不道歉,他们所损失的远远比不上所获得的。此类社会知名人士所凭仗的,实则是法律滞后性,但在知识产权新规和文娱行业自纠的双重规制下,公众人物若想继续游走在法律空当之中,将定会受到严惩,知识产权也将成为影视行业投资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风险因素。
五、危机处理之凡人警示榜:要悼念逝者,更要怜爱生者
12月24日,bilibili(以下简称B站)在微博发布了一则向逝者致以哀悼的灰色背景的公告。公告称,“自当日起,对于不幸离开人世的B站用户,他们将在取得其直系亲属确认和同意后,将其账号列为‘纪念账号并加以保护,以纪念他们和我们曾经存在于同一个世界,曾经看过同样的风景,为同样的事物欣喜或悲伤。”
此前,新浪微博也曾发布关于保护逝者账号的公告,设置为保护状态的逝者账号不能登录、发布删除内容。Facebook的“悼念账户”功能,赋予了用户在生前自由处置账号的权力,用户可以选择委托他人继续使用账户,也可选择永久删除。
国内国外,不同平台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体现了网络账号作为数字财产的重要性。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将“数字遗产”定位为以二进制的形式加以描述、存储和传输的人类活动,随着互联网在社会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人们成为了互联网住民,有关数字遗产的保护也逐渐引发热议。
生理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被人遗忘才是。纪念账号对互联网公司而言或许是在平衡逝者权益和企业利益之后的一项人性化的决断,但对广大用户而言,留存着大量个人痕迹的网络账号在象征着极具隐私的虚拟自我之外,还是逝者生命意义的延续,是让生者反思过去、思考人生的静默空间。
2009年清明期间,即有网站组织了悼念去世博友的活动,活动组织者在专刊导言中称:“阅读着他们鲜活、智慧的文字,我们在博客里缅怀他们……”2011年7月,一个名为“逝者如斯夫dead”的微博账号成为互联网中的入殓师,博主在微博记录逝者故事,发布生者对逝者的追思。在这里,一则则博文成为了逝者的虚拟墓碑,一座座承载着生者怀思的墓碑便构成了互联网中真实的悼念场所。
B站的公告下边,同样成为了一场自发的悼念仪式,网友们在留言区列举着已经离世的up主,在记忆中追思逝者之时,也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和祝福。逝者已矣,但纪念账号就像一束微光,照亮关怀着与之相遇的普通人,因新冠疫情去世的李文亮医生,自杀的留学生“路旁的叶修”等等,网友在其微博下留言,在其视频中持续发送弹幕,众多对空的倾诉中,逝者逐渐变成了一种形象,其账号也变成了某类人自我慰藉、相互扶持的纽带。
与在逝者账号下的怀思不同,一些账号主体在离世之前曾遭遇铺天盖地的辱骂。B站灰色公告中提到的UP主“卡夫卡松饼君”和“虎子的后半生”,都因某些个污点招致大量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该账号目前已被强制关闭弹幕,但那些冲着将死之人发出的污言秽语却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中国的传统里讲究死者为大,然而整体的泛娱乐化倾向之下,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死亡的严肃性被披上“戏谑”的外衣,生命的重量亦被遮蔽在非此即彼的争论中。生命可贵,我们与其跟风指责或在纪念账号下悼念,不如关爱患病之人,对他们多些宽容和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