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译介与研究
——韩国汉学家崔溶澈教授访谈录
受访人:[韩]崔溶澈 采访人:马君毅
马君毅:崔教授您好!十分感谢您接受我的邀请,就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译介与研究这一话题做一次访谈。自古以来,朝鲜就是中国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与频繁的交流。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更是在古代朝鲜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在古代的朝鲜半岛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朝鲜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不仅朝鲜文人善用汉语创作诗文,甚至连一些闺中佳丽也颇工于此。①参见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年。请您谈一谈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对朝鲜古代文学产生这般影响?另外,具体就小说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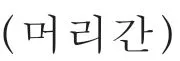
至高丽末年,“朱子学”进入朝鲜半岛,继之而兴的朝鲜王朝以宋明理学治国,甚至固执地要保持儒家思想,汉化程度非常高,所以朝鲜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都以中国文学为典范。在诗歌方面,楚辞、陶诗、杜诗等都成为朝鲜文人竞相研习的对象。尤其是杜诗,对朝鲜文人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方面,杜甫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朝鲜文人学习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忠君之情;另一方面,杜诗格律严谨,讲究炼字炼句,是格律诗的典范,故他们将杜诗视作学诗的轨则。正祖国王曾下诏精选杜甫诗五百首和陆游诗五百首,将其合编为《杜陆千选》,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朝鲜文人学习作诗的技巧,更为关键的是,从中学习杜、陆二人的爱国精神。在文章方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文章不仅文笔优美、情感真挚,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谋篇布局合理严谨,行文用语凝练得当,所以被朝鲜文人士大夫视作学习汉文的“教科书”。比如,成均馆和各地乡校无不将《千字文》《明心宝鉴》《古文真宝》《通鉴节要》及唐宋八大家文、杜诗等作为学习的重要科目。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朝鲜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是很大的。
虽然在朝鲜王朝初期,世宗大王创制朝鲜谚文,从此朝鲜民族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但谚文并未成为必学科目,因此,文人士大夫都不太使用谚文,基本只有妇女和译官两个群体经常使用。妇女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用谚文写书信,也以其创作小说。译官则是由于工作内容的要求,用谚文翻译中文典籍,以供不懂汉语的人阅读。唐传奇、“四大奇书”、《红楼梦》等中国古代小说就是译官应宫嫔们的要求,译成谚文,从而成为她们排忧解闷的读物。这也就是说,因为朝鲜文人士大夫全都使用汉字写作,并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
至于小说,其影响力稍逊于诗文,而且对于朝鲜文人而言,白话小说的影响又比文言小说要小。朝鲜文人尤为钟爱文言小说,其中《太平广记》与《剪灯新话》最受欢迎,影响颇大。《太平广记》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因卷帙浩繁,难以悉数通览,故在朝鲜王朝初年出现了50 卷的选本《太平广记详节》。《剪灯新话》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尤为显著,朝鲜古代小说中的经典《金鳌新话》就直接受其影响。或许是因为《剪灯新话》篇幅较短,全书仅有21 篇,易于传播,所以朝鲜半岛几乎各大城市都曾出版过。此外,比较流行的还有《三国演义》,其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依靠说书者(传奇叟)的表演而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
但是,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在朝鲜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朝鲜文人学习、使用的是文言,对白话非常陌生,只有译官和少部分文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看懂白话文。因此,白话通俗小说需要改写成文言,才能供更多的朝鲜文人阅读。例如,有一部名为《啖蔗》的书,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其中包含几十篇文言故事,细绎其内容,全都是“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有一位台湾学者初步研究后,认为该书是“三言二拍”的原本,声称是先有了这些文言故事,之后才由文言改写成白话。但王国良教授和其他几位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是懂白话的朝鲜人将“三言二拍”中的某些故事改写为文言,并编入此书的。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冯梦龙和凌濛初等都是将原来的文言故事改为白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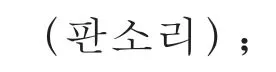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诗文方面,小说的影响远没有诗文广泛和深入。
马君毅:众所周知,在数量繁多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瞿祐的《剪灯新话》并不算是佼佼者,难以归入一流小说的行列,但如您所说,《剪灯新话》却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直接催生了朝鲜古代小说名著《金鳌新话》,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中、朝古代小说史上,《剪灯新话》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
崔溶澈:站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小说史的立场来看,《剪灯新话》是在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之间起承接作用的小说。它产生于明朝初年,与唐宋传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故事大多是根据新近发生的事件,即元明之际江浙一带战乱中的故事创作而成,这是前所未有的。
如前所述,对于朝鲜人来说,学习汉文一般是看“四书”“五经”《千字文》《古文真宝》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然而,这些书籍的内容都比较深奥,而且都是些过去的事情。所以朝鲜人想了解同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就要看明朝人创作的作品,并学习明朝人使用的语言。然而,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仅朝贡使节能够前往中国北京,在朝贡后必须按规定时间立即回国。朝鲜王朝曾多次向明王朝提出派遣留学生赴华学习的请求,但都被拒绝了。在此背景下,由明代文人创作的、描写明代社会生活及历史史事的文学作品就成为朝鲜人了解中国、学习中文的工具之一。而“四大奇书”(除《三国演义》之外)和“三言二拍”都是白话文,之前说过白话文对于朝鲜士大夫来说是很难读懂的,所以与其看“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还不如看《剪灯新话》。由此,《剪灯新话》就具有了两种功能:一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二是作为汉语教材的教育功能。而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剪灯新话》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剪灯新话》是文言故事集,较“四书”“五经”等经典更加生动有趣,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剪灯新话》中的不少故事以元末明初的史事为背景,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能让朝鲜人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上,在一部名为《训世评话》的汉语学习教程中,就有几篇取自《剪灯新话》。
由此可见,《剪灯新话》之所以在朝鲜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朝鲜人的汉语教科书。而随着《剪灯新话》的广泛传播,便有朝鲜文人对其进行摹仿,进而影响了朝鲜古代小说的创作。
马君毅:在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影响往往是双向的。拿造纸术来说,它虽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并从中国传入朝鲜,但朝鲜半岛出产的高丽纸却成为贡纸,回传中国,并在清乾隆时期成为中国人仿制的对象。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是有相当影响的,那么,朝鲜古代小说是否存在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的情况呢?
崔溶澈:这个情况不太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九云”系列小说,即《九云梦》《九云楼》和《九云记》。《九云梦》是朝鲜显宗、肃宗时期著名的闾巷文人金万重(1637—1692)所作,共十六回,讲述了杨少游与八位才貌双全的佳人之间的一段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九云楼》和《九云记》则是《九云梦》的两种改写本,三者间有着非常密切而又十分复杂的关系。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学术界对《九云楼》与《九云记》的关系及其国籍依然难以得出定论。
如今,韩国学者普遍认为《九云楼》是比《九云记》更早的本子。丁奎福教授曾发表过《〈九云梦〉与〈九云记〉之比较研究》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朝鲜译官金进洙(1797—1865)《碧芦集》有首诗的注释以及评文里就提到了《九云楼》。①金进洙《碧芦前集》卷一中有以“燕京杂咏”为总题的一首七绝:“墨鸢裴虎迄无休,篇休丛残尽刻舟。岂但梅花空集句,九云梦幻九云楼。”诗后有一条关于“九云梦”的注释:“我东小说《九云梦》,增演己意,如杨少游系杨震,贾春云系贾充,他皆仿此,皆写像于卷首,如圣叹四大书,著为十册,改名曰《九云楼》。自序曰:余官西省也,于舟中得见《九云梦》,即朝鲜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鲜不娴于稗官野史之书,故改撰云。”参见韩国奎章阁藏本《闾巷文学丛书》第5 辑影印本《碧芦集》。按照金进洙的诗注来看,应该是他在清朝道光年间出使中国时看到了《九云楼》,而且他看到的是在中国刊印的刻本,所以起码在19 世纪中期之前,《九云楼》在中国是有流传的。因此,金进洙看到的《九云楼》极有可能是由中国文人将《九云梦》改写后在中国刊行的本子。后来,在韩国岭南大学又找到一部手抄本《九云记》,共九册,三十五回,其内容与《九云梦》大同小异,只是在分回上由《九云梦》的十六回增多到三十五回。目前,学界对于《九云记》的国籍存在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九云记》是朝鲜汉文小说,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它应当属于中国古代小说。
另外,在1884 年,深受《剪灯新话》影响而创作的朝鲜汉文小说《金鳌新话》在日本出版,朝鲜人李树廷(1842—1886)在跋文中曾称《金鳌新话》和《九云梦》是两部非常出名的传奇小说,但是《九云梦》十册曾经在清朝出版过,而《金鳌新话》从来没人出版过,所以现在出版《金鳌新话》是很有意义的。①李树廷《金鳌新话·跋》:“朝鲜固多小说,然皆有根据,盖野史之类。其传奇之作甚稀,仅有梅月堂《金鳌新话》、金春泽《九云梦》数种而已。……惟《金鳌新话》,只有誊本,以梅月堂有重名于世。……此书为日本大冢氏收藏,已二百二十余年,书之古可知矣。今上于梓,以寿其传,乃如大冢氏,重其人也,读此者,宜致思焉。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三年,甲申之秋,汉阳李树廷识。”参见陈文新、[韩]闵宽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32 页。可见,李树廷是见过刻于中国的十卷本《九云梦》的,但李树廷所说的《九云梦》十卷刻本直到今天,都没在中国找到。
总之,“九云”系列小说存在诸多的疑点,体现着中、朝两国书籍环流的现象,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九云梦》是一部文学成就颇高的作品,我认为可以将《红楼梦》《九云梦》和《源氏物语》三部东亚文化圈中的小说巨著进行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将会非常有意义。
马君毅:如您所说,《剪灯新话》不仅曾经被朝鲜人当作汉语教科书,而且深深影响了朝鲜古代小说名著《金鳌新话》,它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您介绍一下《剪灯新话》在韩国的传播与译介情况。
崔溶澈:《剪灯新话》在韩国流传的历史非常悠久。明朝永乐年间,《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合刻本问世,此后不久,该书便传入朝鲜半岛。朝鲜世宗大王曾敕命编撰《龙飞御天歌》,在该书注释中已引用了《剪灯余话》的部分内容。此后,特别喜欢稗说的朝鲜国王燕山君特地命令燕行使节到中国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到了朝鲜中期,林芑、尹春年为《剪灯新话》作注,编成《剪灯新话句解》,在朝廷下属的校书馆刊行。该书是第一部由朝鲜人注释、刊印的中国小说注解本,在朝鲜王朝覆灭以前于朝鲜半岛广泛流行,甚至流传到了日本。
因为古代朝鲜文人的汉文功底普遍颇为深厚,能够直接阅读中国文言小说,所以在朝鲜王朝前期,并未出现《剪灯新话》的谚文译本。直到朝鲜王朝中后期,宫廷妃嫔及贵族妇女喜读中国古代小说,为方便他们阅读,《剪灯新话》才逐渐被翻译为谚文。根据有关记载,朝鲜时代既有选取某些篇章进行部分翻译的选译本,如择取《剪灯新话》中《绿衣人传》进行翻译的译本,也有对整部作品进行全面翻译的全译本,此类译本目前有两种,即首尔大学藏本与檀国大学藏本,但二者均有残缺。此外,在文人阶层中还流行一种较为特殊的译本——《悬吐剪灯新话》。所谓悬吐,是指在汉文原著的句读部分加入韩文助词,既便于朗诵阅读,又可帮助理解,这也是朝鲜一种独特的翻译方式。
韩国建国后,翻译家、学者对《剪灯新话》的兴趣有增无减,《剪灯新话》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译本,如尹泰荣译本(1950)、李炳赫译本(1968)、李庆善译本(1971)、郑容秀句解译注本(2003)等。
我对《剪灯新话》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翻译过《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并将其合订为《剪灯三种》(上册《剪灯新话》《觅灯因话》,下册《剪灯余话》),于2005 年由韩国SОМYUNG(召命)出版社出版。我的这部译本不仅对《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进行了全面的翻译,而且对《剪灯新话句解》中的序跋和题记,如朝鲜林芑《句解跋》、朝鲜尹春年《题注解剪灯新话后》、日本林罗山《题记》等内容,也进行了翻译。
马君毅:您前面提到在朝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剪灯新话》的谚文译本,那么现当代韩国学者为什么要重译《剪灯新话》,您觉得这些重译本有何功用与影响,又有哪些不足?
崔溶澈:在朝鲜时代,所有的谚文译本都是传统的、古典的,这是由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决定的。进入20 世纪后,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译本,与朝鲜时代相比,此时期的韩语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为满足读者的需要,自20世纪初至20 世纪70 年代,涌现出多部《剪灯新话》的谚文译本。然而,这些译本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有的并非全译本,内容不完整,有的在语言表述上不够准确,还有的文笔虽佳,学术严谨性却不足。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而恰在此时,一部在版本、校勘、注释等方面都颇为严谨、完备的《剪灯新话》全新校注本(周楞伽校注本)在中国出版,再加上这一时期的韩国学界热衷于研究东亚汉籍,《剪灯新话》作为一部在朝鲜半岛具有重大影响的汉籍,其研究热度可谓与日俱增。因此,韩国学界盼望有更加严谨、完备的《剪灯新话》新译本问世。可以说,我翻译的《剪灯三种》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东亚各国学界都开始认识到东亚汉籍的重要性,并提倡研究东亚汉籍,而东亚汉文小说研究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汉文小说,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的古典汉文小说,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深受《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影响。因此,研究《剪灯新话》有助于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的深入。对于韩国学者来说,《剪灯新话》译本能够为其研究提供莫大的便利,所以质量更好、更严谨的重译本有利于韩国学界对《剪灯新话》乃至东亚汉文小说展开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社会的传播与普及。
下面,我再谈一下这些现当代重译本的不足。20 世纪50 年代出版的尹泰荣译本并非全译本,只有上册,共11 篇,这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后册无法继续出版。李炳赫译本最初是在地方报刊《庆南每日新闻》上连载,直到2002 年才结集重新出版,但该译本不够严谨,学术性不强。1971 年,李庆善译本由乙酉文化社出版,此译本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不过,由于当时尚未发现奎章阁所藏的《剪灯新话》早期版本,也没有输入中国出版的新校注本,所以该译本是根据《悬吐剪灯新话》翻译的。到了21 世纪,学界才开始重视底本的版本问题,所以郑容秀以奎章阁所藏《剪灯新话句解》为底本,出版了新的译注本。
我在研究明清小说时,特别关注《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自朝鲜王朝初年,《剪灯余话》就与《剪灯新话》一起流传入朝鲜,并影响到朝鲜文学,但是《剪灯余话》从未出现过谚文全译本。因此,我以周楞伽校注的《剪灯新话(外二种)》做底本,进行全面翻译,并加入较为详细的注释和解说。我的译本最终在2005 年出版,这也是目前韩国唯一一部“剪灯三话”的完整翻译、注释本。当然,在翻译过程中,我吸收了谚文翻译、悬吐翻译以及前辈学者的早期经验。
马君毅:如今,韩国是东亚地区的发达国家之一,韩国民众在各方面无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传播与接受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崔溶澈: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有些人喜欢西方小说,也有些人喜欢现代科幻小说,当然还是有一大批人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其中《三国演义》最受欢迎,它也是在韩国出版及印刷次数最多的中国古代小说。据说,首尔大学的入学考试试题中,曾经有题目涉及《三国演义》,所以想要考上韩国最好的学校首尔大学,就必须读《三国演义》,于是家长就买《三国演义》给子女阅读。虽然这个事情只是一时传闻,并不一定真实,但《三国演义》基本上每家都有。除《三国演义》之外,《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也是家喻户晓,拥有众多读者。因为它们与《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奇书”,出版社在出版发行时,往往将“四大奇书”做为一套书,所以读者在购买《三国演义》时,就顺带把其他三部也买了。再有就是《红楼梦》,但《红楼梦》在韩国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读者群体也比较有限。总的来说,最受韩国读者喜爱的中国古代小说无疑是《三国演义》。
马君毅:您刚才提到《红楼梦》在韩国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不及《三国演义》,但我们都知道,《红楼梦》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水平。为何《红楼梦》在韩国遭受如此冷遇呢?
崔溶澈: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久。我认为,首要的原因是《红楼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比较晚。《红楼梦》程刻本刊印出版时,正值朝鲜正祖时期。正祖认为小说、戏曲、小品文是坏人心术的杂书,于是明令禁止任何人从中国携带此类书籍进入朝鲜,这为《红楼梦》在朝鲜的传播造成了巨大的阻碍。直到19 世纪末年,第一部《红楼梦》谚文译本即乐善斋本的出现才真正让朝鲜人读到了《红楼梦》。但读者群体仅限于宫廷之内,民间是无法读到的,所以影响不大。
其次,《红楼梦》的故事情节难以获得韩国人的认同。《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而这几个人物之间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在韩国人的伦理观念中,近亲婚恋是不道德的。况且,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在谈恋爱时都还未成年。换句话说,《红楼梦》描写的是具有亲缘关系的未成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这更是有违韩国人的道德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楼梦》与韩国人的伦理观背道而驰,令韩国读者难以接受。
再次,《红楼梦》篇幅很长,而且故事缺乏传奇性、故事性,没有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这使不少读者仅读了一部分,便觉得索然无味,就没有坚持读下去了。对这一情况,我深有体会。我与高旻喜教授共同翻译的《红楼梦》韩文全译本一共有六册,唯独第一册卖得最多,之后的几本都很难卖出去。因为韩国读者连第一册都看不完,又怎么会买第二册呢?有鉴于此,我想换种形式向韩国读者介绍《红楼梦》。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许多短小精悍的故事,这样的小故事便于传播,它们能够让读者一点一点地接受,并逐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所以,我打算把《红楼梦》的故事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按人物编排,如贾宝玉的故事、袭人的故事、晴雯的故事等。然后,把这些故事编辑成册,分别出版出来,让韩国读者按人物来读,让他们一点点地接触《红楼梦》,由此逐渐进入《红楼梦》的世界。
马君毅: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韩国的发展历程及韩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崔溶澈:1989 年,我们成立了中国小说研究会,后来改为中国小说学会。学会成立后,我们一方面关注保存在韩国的中、朝两国古代小说文献的问题,另一方面将中国的相关研究动态和成果介绍给韩国的学者与学生。学会还创办了《中国小说研究会报》,它刚刚发行了第100 号。1990年3 月初创时,第1 号还只是薄薄的一小册,而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本了。这个学会在成立之初曾在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界引起了轰动,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中国小说研究会,之前都是中文学会、中国学会,文史哲都是放在一起的,而中国小说研究会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后来逐渐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小说。总之,它是韩国第一个以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业学会,还创办了专业的学术期刊,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学会成立后,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日益兴盛。
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中、韩两国流传的小说文献的异同。比如,韩国刊印流传的《剪灯新话》与中国的版本就不一样。该书在朝鲜印行时,由原来的四卷本变成两卷本,而且还加了注释、句解,主要是注明典故、人名、年号、地名,因此成为东方小说中最早的注释本。其二,研究中国已经亡佚而现存于韩国的小说文献。《型世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型世言》是明末陆人龙的白话短篇话本小说集,共收40 篇,于20世纪80 年代末在韩国奎章阁被发现,引起了中、韩古代小说研究界的轰动。它的发现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书进行讨论,成果丰硕,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其三,中、韩两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我就曾仔细研究过《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二者间的关系,并在中、韩两国的学术刊物上都发表过相关论文。此外,中国古代小说对韩国古代小说的影响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门话题,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四,翻译中国古代小说,进而研究翻译方法和理论。中、韩两国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困难重重。我与高旻喜教授曾将《红楼梦》120 回全部翻译成韩文,前80 回的翻译是由我承担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对如何翻译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便将这些想法写成了论文。
马君毅: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是该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研究现状。
崔溶澈:总的来说,现在研究者还是比较多的,关注的领域也比较广泛。但与以前相比,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正逐渐减少。如今,韩国的各个大学基本都设有中文系。在各大高校的中文系中,研究语言学、现代汉语的学者人数最多,其次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人数最少,而且人数愈来愈少。在这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中,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算是比较多的,他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关注。
首先,韩国学者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小说的译介。将中国古代小说翻译成韩文是我们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近年来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一大批成果。比如,延世大学的金长焕教授将《太平广记》全部译成韩文,接下来准备翻译《太平御览》。又如,全南大学李腾渊教授对冯梦龙的《情史》进行了译介,书稿已经完成,即将出版发行。再如,“三言二拍”长久以来一直没能完整地翻译出来,先前的译本都只是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来翻译,所以现在也有学者在从事“三言二拍”的翻译工作,他们要将其全部翻译成韩文。其实,《型世言》也是现在亟待翻译的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我已经翻译了一部分,但是还没翻译完。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正在翻译清代的小说以及小说研究的有关资料。除了小说作品的译介外,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翻译也十分关心。近年来,赵宽熙教授就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翻译过来,并参考了多部中外学者编著的中国小说史著作,在书中加入了很多注释。但非常遗憾的是,韩国学者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很少,可能仅徐敬浩、全寅初两位先生写过。
其次,传教士汉文小说的研究是近些年来较为前沿且热门的课题。在韩国学者中,以崇实大学的吴淳邦教授为代表。他自己就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多年来一直从事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目前,传教士汉文小说是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话题,因为这是以往中国小说史中没有提到的,此类作品是西方人用汉文写的小说,我认为这个课题很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和价值。巴黎第七大学的陈庆浩教授打算在越南汉文小说和韩国汉文小说整理出版后,开始整理传教士汉文小说。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韩国汉文小说集成项目。这一项目大概是在1987 年由陈庆浩教授提议的。当时,韩国的学者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韩国汉文小说的数量太过庞大,没办法搜全,而且除《九云梦》《春香传》外,汉文小说很少刊刻出版,绝大多数都是抄本,这些抄本的版本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这项工作难度非常大,要克服很多困难。不过我和我校国文系的张孝铉教授齐心协力,积极推动韩国汉文小说集成的编纂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近十五年。后来,该项目转到上海师范大学,由孙逊、赵维国两位教授主管,成为高丽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共同执行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这一项庞大的工程现已接近尾声,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韩国汉文小说集成的出版可为学界提供不少新材料,届时可以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再次,韩国学者最近对小说插图的研究颇为关注。虽然韩国所藏的小说插图较少,但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中国小说绘模本》收了128 幅小说插图,而且它们都来源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十分珍贵。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插图的流传和刊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颇具研究价值。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韩国学界在中国古代小说翻译与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翻译和研究总是集中在几部著名的小说上,重复的现象比较多,同一部作品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本和研究著作。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韩国的很多译者并非学者,而是作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在此情况下,他们更乐意翻译较为知名的中国古代小说,因为翻译过程中可以参考日文译本。其二,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的成果最终是出版社出版的译本,而商业效益一直是出版社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许多出版社只愿意出版如“四大奇书”《红楼梦》这样的名著,其他知名度较低的中国古代小说就算被翻译出来,也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将其出版。对此,我认为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让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首先选拔一批具备学术实力的学者,让他们每人承担一部分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工作,并有计划地进行。待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再由政府和出版社出资,将这些成果作为文化项目进行出版。如此,便可以扩大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范围。
马君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在此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崔溶澈:谢谢!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