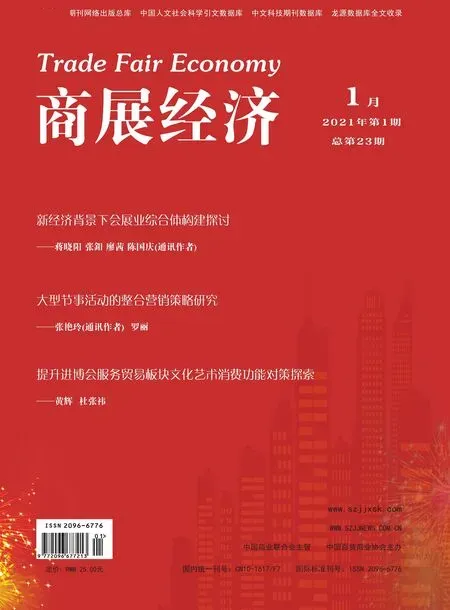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的相关理论综述①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青岛科技大学统战部 张洪坤
在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技术更迭周期不断缩短,技术创新任务的复杂度和不确定性不断提高,使得科技创新模式由传统的封闭式创新逐步向跨组织、跨知识、跨领域的开放型创新转变。为抓住创新形势变化带来的机遇并应对挑战,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跨越组织边界组成的协同创新团队成为完成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的重要载体。协同创新团队的组织模式不仅能够分担创新风险,同时也能使团队内部各创新主体更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以更高的效率满足独特创新任务的需求。虽然协同创新团队内部资源(如人才、技术和资金等)相比于一般团队而言更加丰富,但并不意味着协同创新团队的所有任务都能依靠其内部成员完成。相反,协同创新团队所承担的科技创新任务难度、所需资源多样性和失败风险等远高于一般团队,因此通过跨界活动与外部主体进行交流与合作,实现更广范围内的资源链接与整合,对协同创新团队顺利开展并完成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具有重要意义[1,2]。实际上,跨界活动已成为协同创新团队完成工作任务的微观运行机制。
1 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的概念界定
对跨界活动的界定应该先明确跨界主体[3]。本研究中跨界活动的主体是协同创新团队。本质上,协同创新团队是企业、中介机构、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立足于契约精神而形成的创新组织模式(袁庆宏等,2015)。协同创新团队内部各主体通过网络型链接实现资源的高效率集聚与整合,同时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能够聚焦于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合理有序的合作机制能够激发各主体充分发挥其优势与能力。相关学者认为团队层面的跨界活动是团队为实现任务目标,跨越自身边界,建立、维持和管理与其嵌入的外部环境中相关单位(如其他团队、团队上级领导、客户、供应商等)之间的关系联结并保持互动的过程[4]。团队跨界活动包括使节行为、任务协调行为与侦测行为三个维度。其中,使节行为是指团队成员与外部高阶单位的互动行为,反映了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的垂直维度;协调行为是指团队内部员工为顺利达成创新目标,与外部合作主体进行的沟通、协调、协商和反馈的行为;侦测行为是指团队成员为获得重要信息和相关技术而对外部主体进行关注的行为,体现了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的竞争维度[5]。
完成工作任务是协同创新团队组建并运行的根本意义,协同创新团队承担的科技创新任务的复杂程度、不确定性程度及失败概率远高于一般团队,为了分散创新风险并更好地完成创新任务,或者为了完成该协同创新团队不擅长、创新资源严重缺乏的创新任务,多数协同创新团队将选择开展跨界活动,以实现资源更高程度的解决和整合,放大自身原有的协同创新效应[6-8]。由此可知,相比于一般团队,跨界活动对协同创新团队的任务实施和绩效取得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定义为:由企业、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组成的网络型创新组织模式,为了更好地实现协同创新任务而与外部组织、团队或个体建立关系并不断进行互动的行为,包括使节行为、任务协调行为与侦测行为。图1为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的概念示意图。

图1 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概念示意图
2 团队跨界活动的作用效果研究
现阶段,团队跨界活动研究多聚焦于团队跨界活动的作用效果分析,并且重点探讨了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然而,该方面研究结论存在争议:首先,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团队跨界活动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跨界团队通过与外部相关方沟通并建立联系,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新信息、新技术和外部支持等资源,从而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力。臧维(2019)发现团队跨界活动中的使节行为、协调行为和侦测行为均对团队创造力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团队知识整合能力能够加强中介团队跨界活动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9]。臧维(2020)利用元分析对跨界活动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个体、团队、组织层面的跨界活动中,团队层面的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部分研究发现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无影响。王亮等以互联网为背景,探讨了团队跨界活动在团队领导方式对团队创造力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验证了团队跨界活动的中介作用,但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造力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部分学者认为团队跨界活动与团队创新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Gibson(2013)等研究发现,团队外部活动并非越多越好,团队跨界活动和团队效能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0]。袁庆宏等(2015)利用中国111个研发团队的问卷数据验证了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的倒U型影响。
3 团队跨界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部分研究从团队和组织层面对团队跨界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究。首先,在团队层面,团队异质性、团队领导风格以及任务特征对团队跨界行为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Choi(2002)指出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团队跨界活动的程度就越高,因为深层特质异质性的团队会由于缺乏一致性而产生分歧,从而促使他们向外部群体寻求互动和交流[11]。Joshi等(2009)的研究发现外向型的团队领导能有效地进行边界管理,鼓励团队开展跨界活动[12];而内向型团队领导的工作重心集中于团队内部,团队跨界活动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团队任务特征方面,Drach-Zahavy(2010)认为团队需要根据工作任务的特征决定采取何种跨界行为,如果当任务的依赖性很高,但与外部团队目标一致性低时,团队主要采取边界侦查行为;在目标和任务依赖性都很高时,团队主要从事任务协调活动[13]。
其次,在组织层面,组织文化特征、组织变革特征、组织情境特征对团队跨界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组织文化特征方面,刘松博(2014)认为在紧密型组织文化下,团队可能更多地进行边界紧缩活动[14];在努力进取的组织文化影响下,团队将频繁地开展跨界活动;在个体主义文化下,团队侦测活动会比较多;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团队成员会服从整体目标,协调活动会更为明显。组织变革方面,Yan(1999)的研究显示,当组织减少冗余人员或设备时,团队将再次搜索其需要的性能和更优的资源,侦测活动会得到加强[15];团队运用高科技设备时,团队将频繁开展以交流和学习为目的的跨界活动。关于组织情境特征,Joshi(2009)发现组织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使节活动,而与任务协调活动具有负相关关系。
4 研究述评
以上研究主要从概念界定、作用效果、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进行了剖析,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尚未构建起以工作任务为主线的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研究框架。相比于一般团队,完成重大科技创新任务是协同创新团队成立的起点,跨界活动在整个任务开展和绩效取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从工作任务视角认识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然而,既有研究还未构建以工作任务为主线的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研究框架,无法为协同创新团队如何避免跨界活动的“死亡怪圈”提供参考和借鉴。
第二,现阶段团队跨界活动的作用效果研究尚缺乏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没有发掘出关键的中介变量(Marrone,2010)。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团队跨界活动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方面开展了有益探讨,但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争议,并且仍缺乏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本研究认为,未能同时考虑到协同创新团队和员工个人层面的中介因素是导致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存在争议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将团队和员工层面的工作重塑纳入分析框架,以明确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是否能够提高团队创新绩效及具体作用机制。
第三,现阶段研究忽视了对协同创新团队如何有效开展跨界活动的探索。团队管理实践表明,协同创新团队在跨界活动出现“死亡怪圈”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未能根据团队承担的任务特征合理地开展跨界活动。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是从团队创新绩效等视角分析团队跨界活动的开展效果,而对其动力机制的研究较为欠缺。完成创新任务是协同创新团队存在的意义和运行的起点,如何理解创新任务的特征并基于此判断是否通过跨界活动完成该任务关系到协同创新团队的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任务特征对协同创新团队跨界活动决策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