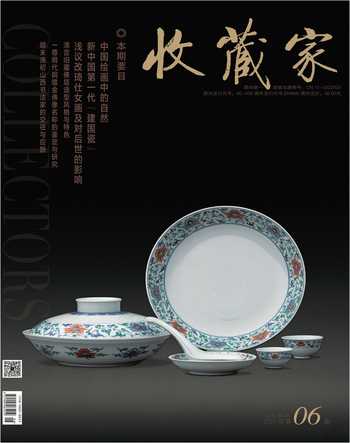略论西藏现代布面重彩画的形成及其特征
戚明





布面重彩,顾名思义,是在画布上敷设重彩进行创作的绘画方式。西藏现代布面重彩画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绘画形式,它吸收了唐卡、壁画等西藏传统绘画的材料与技法,借鉴了中国工笔重彩画和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形成了高原文化独有的艺术面貌。在西藏,以布面重彩画为核心,凝聚了一批藏、汉、瑶、回等各民族画家,形成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西藏本土绘画群体。
一、布面重彩画的形成
(一)缘起
上世纪70年代,陆续有内地美术工作者进入西藏,开始艺术创作。在当时,作为中国画常规材料的优质宣纸,在西藏并不容易购买到。而且,由于西藏的高原气候条件,空气稀薄而干燥,宣纸极易脆化而失去绵软柔韧的特性,常常导致创作无法顺利进行。因此,一些画家转而在绘画材料上寻求突破,探索可以替代宣纸的材料。他们受到唐卡绘画的启发,开始尝试使用画布进行创作。叶星生创作于1979年的《赛牦牛》(图1)是西藏出现较早的现代布画。这件作品的诞生有着一定的偶然性。画家在创作唐卡时无意将墨汁滴到棉布上,墨汁顺着布料的纹理晕染开来,别有一种朦胧的意趣,颇似牦牛头部。这给画家带来了创作布画的灵感。于是,作者又随形添上牛眼、牛角、牛背,牦牛的装饰则使用了鲜艳厚重的矿物颜料,加上飞翔的云雀、奔跑的藏獒和热情欢乐的藏族骑手,一幅表现藏族民俗活动的布画《赛牦牛》由此诞生。
在叶星生之后,陆续有西藏的画家使用亚麻布和纯棉布作画,并研究、实验各种植物与矿物颜料,甚至将油画、丙烯颜料运用到创作中,以期在画布上呈现出多样的绘画效果,布面重彩画初具面貌。
(二)发展
布面重彩画早期的发展有赖于艺术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较早创作布面重彩画的除了叶星生,还有韩书力、余友心、李知宝、翟跃飞等扎根西藏多年的内地画家。这些画家在入藏之前已有较为扎实的绘画功底,在他们的带动下,巴玛扎西、计美赤列、嘎德等藏族青年画家开始学习布面重彩画,在拉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布面重彩绘画为主的创作群体。
除了画家之间的交流学习外,西藏自治区美术家协会(以下简称西藏美协)的助力与西藏大学艺术系对藏族青年画家的培养,也推动了布面重彩画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这一创作群体的壮大。
西藏美协成立于1981年,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对西藏传统艺术的考察、整理与学习,多次组织画家下乡采风。尤其是1982年至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联和美协派出韩书力等7位画家,在西藏进行宗教与民间艺术考察,行程三万余公里,收集作品近千件,拍摄照片数千张。美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和对西藏传统艺术的广泛考察,对布面重彩画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余友心在谈到布面重彩的形成时,提到西藏画家在考察中:“对散见于广阔地域的古代艺术遗存及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艺术行为和样式,做深入的探访和汇集整理工作……伴随这一过程渐入佳境的是布面重彩画的启蒙及创作的持续繁荣。”艺术家通过深入了解藏族传统艺术,学习西藏壁画和唐卡的材料技法与造型语言,为布面重彩画注入了鲜明的西藏艺术基因与深厚的藏族文化内涵。
西藏大学艺术系成立于1985年,招收藏、汉等各民族学生,30多年来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藏大艺术系不仅对学生进行素描、色彩等现代绘画基础的训练,也非常重视对藏族传统艺术的研习,开设西藏传统唐卡课程,并且每届学生都有临摹寺院壁画的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熟悉藏族传统绘画。很多藏族艺术青年大学期间在工笔重彩与唐卡绘画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布面重彩画与西藏传统绘画的材料和技法方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他们对这一新画种有着心理上的亲切感和天然的优势,所以在开始自由创作时很自然地选择了布面重彩画进行创作。这一绘画群体不断有青年艺术家加入,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三)命名
西藏布面重彩画从80年代开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实践,而“布面重彩”这一名称的确定也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布面重彩画被称为“布画”,之后亦有“藏派丹青”“拉萨布画”等名称出现。但是,这几个名称的概念和界限都比较模糊,不足以准确定义这一绘画形式的特点。
2004年,中国美术馆举办“雪域彩练—西藏当代绘画邀请展”,展出了韩书力、余友心、巴玛扎西、计美赤列等11位西藏艺术家创作的布面重彩画。展览期间,《美术》杂志主编王仲组织艺术界和理论界的專家学者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命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最后把西藏布画正式命名为“布面重彩”画,从事布面重彩绘画创作的西藏画家群体也被称为“布面重彩画派”。这一名称准确概括了这个画种在绘画材料上的特殊性,得到了包括西藏画家在内的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展览在北京结束后,又巡展至上海、广州等地,每到一处都反响热烈,引起了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布面重彩”这一名称也随之传播开来,并沿用至今。
二、布面重彩画的特征
(一)绘画材料的独特性
布面重彩画以绘画材料命名,画布与颜料的选择是这一画种区别于其他绘画形式的核心要素。画家在创作时多使用棉布、细质棉麻布或帆布,以浓茶水均匀地涂在画布上,形成一层底色,然后以植物或矿物颜料在布面上进行创作。在颜料的选择方面,除了常规的中国画颜料外,还会使用西藏传统绘画中的朱砂、石黄、青铜矿、孔雀石等天然矿物颜料和以藏红花、大黄、蓝靛等为原料的植物颜料,来实现特殊的色彩质感和画面肌理。
由于艺术追求的不同,画家在颜料的选择上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也导致了作品面貌的差异。如李知宝偏爱岩彩,曾尝试用取自喜玛拉雅山脉的矿物颜料作画。创作于2003年的作品《如影》(图2),刻画了朝圣途中的藏女形象,画面颗粒感明显,色彩的纯度和明度较高,营造出了肌理丰富又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韩书力在颜料的运用上非常广泛,藏草药、藏植物、甚至核桃树皮都成为用色的原料,其作品色彩庄重、典雅。计美赤列则将油画、丙烯颜料与传统矿物颜料相结合进行创作,使作品色彩鲜艳厚重、富有光泽。艺术家对绘画材料的研究、探索和创新,不仅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技法和语言形式,也拓展了中国绘画的审美样式。
(二)聚焦西藏现实生活
与壁画、唐卡等西藏传统艺术为信教群众普及宗教知识、传播佛教思想的功能不同,布面重彩画是画家进行自主创作、自由抒发个人情感的载体。在题材与内容方面,布面重彩画聚焦西藏人民的现实生活,既有对传统农牧业生活和藏族风土人情的浪漫表述,又有对西藏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热情讴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
计美赤烈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现实生活来展开,体味和发掘藏族人民生活的多个层面,表现他们的爱情、亲情以及日常劳动场景,真挚地赞美了藏族人民的勤劳、淳朴、善良。《太阳与月亮》(图3)表现的是夏季的拉萨河畔,藏族男女青年浣洗衣物、谈情说爱的情景,藏女低垂的眼帘流露出含蓄娇羞的一面,充满生活情趣。画面以大面积的红、黑为主色调,令人感受到爱情的炽热与美好。2007年,计美赤列以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青藏铁路为主题创作了布面重彩画《北京—拉萨》(图4)。作品以三联画的形式,巧妙地以一列疾驰的火车将天安门和布达拉宫连接起来。近景中身穿隆重的民族服饰的藏族百姓依偎在一起,遥望远方,憧憬未来。这条雪域天路不仅让北京和西藏不再遥远,也翻开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为古老的西藏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画家以高度提炼的线条与色块来分割画面,使作品在稳定、平衡的结构中增添了节奏感与韵律感,令观者感受到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西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借鉴藏族传统艺术
藏族传统艺术包括唐卡、寺院壁画等,因其丰富多样的造型、醇厚艳丽的色彩、严格的程式规范而著称,在民族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布面重彩画扎根于西藏民族艺术的土壤,着力挖掘藏族艺术的视觉审美元素,借鉴唐卡、壁画等造型程式和语言符号,形成兼具藏族艺术特色与现代审美特征的绘画风格。
艺术家对藏族传统艺术的借鉴,首先表现在借用藏传佛教艺术的图式和造型,如神佛、曼陀罗、法器、手印等图像,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解构、重组和再创造。色彩方面则擅用藏族传统艺术中常用的红、黄、黑、白、金等,通过勾线平涂的手法使画面富有装饰美感。韩书力在创作中将佛教绘画中的图式和形象重新组合,赋予了现代的审美趣味。在《祝愿吉祥》(图5)中,侧面站立的主体人物仿佛佛像一般庄严肃穆,头部被置于一片朦胧虚化的墨痕中,面部处理受到唐卡绘画中佛像眼睛造型程式的影响,而身体部分的图案则汇集了唐卡壁画中常出现的宗教图式,如神佛、动物、树木、神龛等。作品画面庄重典雅,大面积的留白渲染了宗教般空灵而神秘的氛围,平面化与图案化的手法体现了西藏传统绘画中装饰风格的影响。
翟跃飞早期的创作深受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绘画的影响。作品中赭红的色调、朴拙的线条和独特的人体造型,都深深地印上古格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痕迹。90年代,他陆续创作了具有表现主义风格的《经典》系列作品(图6),借鉴了唐卡丰富的装裱形式,以手绘装饰图案模仿唐卡的织锦贴裱,再与画面中随意涂抹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文化内涵与形式语言的表达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是西藏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意识相互融合的结果。
(四)蕴含藏族精神文化内涵
西藏在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多重文化的交汇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西藏地区萌生了信仰万物有灵的本土宗教—苯教;7、8世纪先后从内地和印度传入的佛教与高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两种宗教相互影响,积淀了具有高原特色的精神文化内涵。藏民族崇尚自然,认为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飞禽走兽均有灵性,对自然万物有着深深的依恋。而藏传佛教的影响又使藏族人民有着顽强、超然的生命意识,相信生命轮回,尊崇众生平等,在生活中处处蕴含着智慧与善念。当代画家的布面重彩画与藏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联结,透过五彩斑斓的画面,可以感受到藏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现了画家对藏族文化深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巴玛扎西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从小浸润在藏族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对藏传佛教艺术和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因此,宗教与民俗成为巴玛扎西创作的民族文化底蕴。他的作品中有大量佛教图式,如度母、经文和咒符等,形式语言上借鉴壁画色彩的风蚀面貌,有着仿若古舊壁画一般的沧桑感和庄重气氛。他还有很多作品表现藏族节日和传统习俗,如《燃灯节》《藏历年》《恰青节》《望果节》等,这些节日或是纪念宗教领袖,或是祭奠神灵,或是赛马聚会,或是庆祝丰收,展现了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布谷》(图7)创作于2008年,画面中两头健硕的牦牛被装扮一新,它们头戴红缨,胸前挂着金色的铃铛,表现了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节,藏族人民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熟的美好愿望。作品以黑色为背景,红黄蓝三色点缀其间,整体面貌深沉秾丽,朴拙厚重,极具装饰意味和民族审美特征。
藏族女画家德珍一直以儿童、动物和女性为题材进行创作,通过藏民族的世界观和女性的视角来诠释她眼中的世界。她曾在西藏盲童学校做义务翻译,后来留在学校教孩子们藏语、汉语和绘画。她作品中的孩子常常拥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寄托着她对盲童的真挚祝愿。各种动物形象也是德珍经常表现的题材,创作于2003年的《他们还好吗》(图8)描绘了大自然中的各种生灵,蝴蝶、猫头鹰、蛇、鹿、牦牛等,它们自由地生活在梦境一般的奇幻世界里。作品中稚拙的造型和斑斓的色彩充满天真童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西藏文化中存在着各种神灵崇拜,在画家心中,各种动物都是生灵,都应得到善待,体现了藏民族对生命的敬仰、对自然的敬畏。
结语
布面重彩画是西藏现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绘画材料为突破口,根植于西藏的现实生活,借鉴和吸纳民族传统艺术,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的西藏特色的现代艺术样式。西藏布面重彩画创作群体的艺术实践和学理探索为传统艺术的继承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民族美术和地域美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