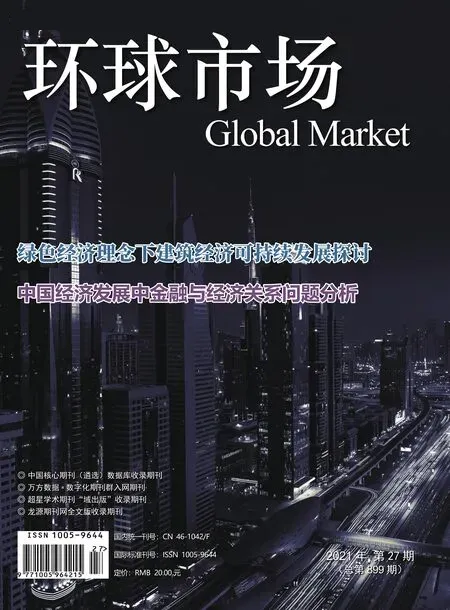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综述
邹美娟 刘蔚 江西理工大学
股权质押打破了传统有形资产担保模式下必须转移控制权的桎梏,是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张涛涛,2020)。2012至2019年,A股市场存在股权质押行为的公司从696家增长到了3432家,而质押的总市值则从0.38万亿元增长至4.27万亿元,大股东更是其中股权质押的主力军。截至2020年6月,超过80%的A股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质押行为,淮河能源、格力电器等公司的大股东甚至质押了其全部股权,整个A股市场呈现出“无股不质押”的现象(姜付秀等,2020)。短短8年左右的时间,股权质押融资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迎来了井喷式增长,市值相比2012年更是增长了11倍之多,股权质押已经成为了资本市场特别是大股东炙手可热的融资选择,也成为了大股东手中的“融资利器”。
大股东质押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表面看是其个人的融资选择,似乎不会对公司本身造成影响。但大股东的股权质押现象越来越成为公司的常态的同时,是大股东“掏空套现”、爆仓平仓的警报频繁拉响。2003年大股东周明益0.8亿元控制明星电力后利用股权质押快速套现,并开始了“隧道挖掘”,肆无忌惮的掏走公司7.6亿元(李永伟,2007)。此外,2004年德隆系、鸿仪系等资本大厦土崩瓦解;2018年3月乐视网大股东贾跃亭质押的所有股票触及平仓线并构成全面违约,公司一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上悲剧无一不与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秉祥,2006)。类似的事件为什么频频发生,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背后掩盖着怎样的暗潮汹涌?基于此,本文围绕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价值相关文献,梳理二者的作用机理,并进行了总结与评述,希望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股权质押概念及其风险
(一)股权质押的基本概念
股权质押作为权利质押的一种,是指股东作为出质人将其自身持有的公司股份作为质押担保标的,从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徐海燕,2011)[5]。股权质押并不要求股东转移股份,股权在质押后,质权人享有股票的分红、送股和派息等法定孳息,但出质人对设定担保的股权仍然享有控制权,其股东身份也没有发生变化,当质押人无法偿还已到期的借款时,质权人将享有在二级市场处置该股权并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相比动产质押和其他的权利质押,股权质押在质押关系设定担保中能更加迅速便捷。
(二)股权质押的相关风险
股权质押作为一种热门的新型融资渠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题。但其日益盛行的同时,也暴露出相较于其他贷款方式更高的风险。
1.市场风险
在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受到一方面受到外部市场供求关系和利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决策水平息息相关,具有很大的波动性(贺晖,2007),当股价越被高估时,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融资的动机也越强,该行为实际上向市场传递出股价被高估的信息,从而可能导致股价的下跌(徐寿福等,2016)。同时,在股权质押期间,股票价格下跌便意味着质权人占据的担保标的物价值下降,债权人便有权要求出质人补充担保,当股价跌破平仓线时,质权人甚至有权卖出所持的被质押股票,相应股东则丧失该股权的控制权。此外,公司的股权质押率越高,可用于补仓的股权越少,一旦股价触及平仓线,股东已无股权可继续用于补仓,如果不能及时还款,将面临被平仓的风险,公司股票将被质权人集中抛售。如果进一步作用于市场,将引起投资者的恐慌情绪,造成流动性危机,引起“股价下跌——平仓——股价进一步下跌”的连锁反应(贺晖,2007),甚至导致股价崩盘。
2.质押股东的道德风险
股权质押将引发道德风险(林建伟等,2006)。由于股价动态波动特征,在股权位于高位时,股东可以利用股权融资大量套现,所得资金甚至可以超过前期投入;股价大跌时股东又可以选择放弃股权而享有于股价高位时质押所得融资,股权质押已然成了股东迅速脱身套现的“快捷通道”(李旎等,2015)。可见,股权质押实质上就是一个套现的过程(沈仰斌,2011),同时由于股票和信贷市场存在双重选择机制,当股票在证券市场被高估以及信贷成本相对较低时,大股东将以更大的质押比例来获取更多的融资(徐寿福等,2016)。如果股东从一开始就将股权质押当作圈钱的工具,并将所得融资用于上市公司之外的股东本身的投融资需求抑或是套现脱身,这都将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也可能面临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于是便产生了质押股东的道德风险。
二、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动因分析
(一)满足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
股权质押作为融资行为的一种,可以使股东以质押担保的形式,将原本作为“经济存量”的静态账面股权转化为“经济能量”而发挥财务效用(艾大力等,2012)。频繁的股权质押行为可能了反映的是公司内部强烈的融资需求:可能是为了缓解公司目前面临的财务危机,且大股东被质押的股权比例越高,往往意味着公司面临的财务危机越严重(高兰芬等,2002);也可能许是大股东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借由股权质押融资来满足公司发展壮大的资金需求(宁宇新等,2006),以免错过高利润的投资机会。但张陶勇等(2014)通过对2007至2012期间584家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公告样本的分析发现,仅有18.5%股权质押资金投向了上市公司自身,可见为公司发展而进行的股权质押融资占比较低,所得融资主要被用于股东自身或者外部非关联的第三方。
(二)维持或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维持或增加控制权也是股权质押的主要动因(Chen&Hu,2001)。于大股东乃至控股股东来说,维持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固自己的控股地位至关重要。特别在上市公司面临恶意收购的情况下,大股东可以利用股权质押所得融资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进行护盘,等到市场相对稳定时再进行减仓操作,并以该减仓所得资金偿还股权质押的借款。股权质押在获得融资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并不影响股东的表决权与控制权(王斌等,2013),因此,股东乐于通过股权质押融通资金来增持本公司的股票,这样不仅避免了股权被稀释,还增加了自己的控制权(Cronqvist&Fahlenbrach,2009)。此外,甚至有不少公司的管理层以股权质押所得的融资大量购进本公司股票而一举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三)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大股东在股权质押获得融资后,失去了对应股票的现金流权却仍然享有的控制权优势,这大大降低了大股东侵占公司利益的成本(张陶勇等,2014),将强化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弱化利益联合效应(郝项超等,2009),使其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占用公司资产等一系列“隧道行为”来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增强(陈泽艺等,2018)。在股权位于高位时,大股东也可以利用股权融资大量套现,所得资金甚至可以超过前期投入;股价大跌时大股东又可以选择放弃股权而享有于股价高位时质押所得融资,股权质押已然成了大股东迅速脱身套现的“快捷通道”,无形中也侵占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李旎等,2015)。
三、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企业价值的机制
股权质押看似是股东个人基于其自身财务状况的一种融资选择,与上市公司没有直接关联。但结合以上部分的分析发现,由于股权质押本身的特性和大股东自身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将不可避免地使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的价值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
(一)弱化大股东的激励效应而强化侵占效应
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向来是分析大股东的两个重要概念。作为导致两权分离的重要因素之一,股权质押即使是在大股东直接控股的情况下也会导致两权分离,在不其影响大股东控制权时减少现金流权。真实现金流权的下降将强化大股东的利益侵占效应而弱化激励效应并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郝项超等,2009)。
已有研究发现,现金流权越大,股东的共享利益也越大(La Porta et al,2002),拥有足够控制权和投票权的大股东将有更大的激励优化公司的投资决策和资源配置(谢军,2006),因此大股东转移公司利润的动机也越小,反之增强企业价值的动机越大。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企业价值与大股东的现金流权呈显著正相关,证明了正向激励效应的存在(Faccio&Lang,2002)。可见,股权质押带来的现金流权的下降会引发新的代理问题,弱化大股东股权集中的激励效应。
此外,股权质押后,大股东仍然享有表决权和控制权,现金流权的下降加剧了两权分离程度。此时大股东控制公司只需要很少的现金流权,这便给大股东利用职权通过一系列“隧道行为”转移公司资产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Cheung et al,2006),使大股东更容易做出损人利己的经营决策(滕晓梅等,2016)。并且两权分离的程度越大,大股东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越强,公司的价值也越低(Faccio&Lang,2002)。
(二)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
大股东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常对通行会计准则进行规则利用,有目的地对财务报告进行操控,该行为也被学术界定义为盈余管理(王斌等,2015)。股权质押往往引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质押前,大股东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抬高公司业绩和股价,以获得更大的融资优势和更优厚的借贷条件(陈共荣等,2016)。
质押后,为避免股价下跌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Lee et al,2004),大股东会对股价的跌涨变得更加敏感。为了放大质押股票质量和价格,大股东会采取一系列股价维护手段,比如选择隐蔽性强,能持续影响企业业绩的真实性盈余管理来平滑股价(谭燕等,2013),该方式能更为缓慢得引起股价的反转,且可以完全为企业所掌握(谢德仁等,2018)。然而盈余管理会降低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并且有研究表明,存在股权质押行为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操纵销售,费用和生产等真实管理活动虚增盈余,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信度、盈余质量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也更低,并且质押率越高越显著(Chiou et al,2002)。
(三)改变公司的风险偏好
权益和负债组成了公司的净资产总额,这种资产结构决定了公司的投资损失将由股东和债权人共同承担,但投资收益却大部分归股东所有,因此公司会更加偏好风险投资,股权质押恰恰会增强大股东的风险偏好(Kao&Chen,2007)。因为投资成功后,大股东将获得相比于未进行股权质押时更多的收益。此外,股东大多选择在股价高位时进行股权质押,因此股东在前期股权质押时已经获得大部分的前期投资,甚至可以远远超过前期投资。因此即使投资失败,引起公司价值或者股价的下跌,股东也已经提前套现,故而可以选择放弃低价的股权而享有前期融资所得。如此一来,投资失败,股价下跌的风险便转移给了金融机构等质权方。正是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增大了股东的道德风险。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股权质押使大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的风险(Lee et al,2004),这使得大股东对股价的波动变得更加敏感,风险承受能力下降,将对公司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理策略。此时对大股东而言,相比眼前暂时的收益,稳固自己的控制权才是至关重要。因此大股东更加厌恶风险,会倾向于拒绝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李常青等,2018)。
四、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显示,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的确会通过其对公司投资决策、财务行为等治理活动的干预而影响到企业的价值。但其影响结果如何,却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一)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效应
大股东股权质押的负向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加剧了大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明显削弱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激励效应而增强了侵占效应(郝项超等,2009),引发的大股东的“隧道掏空”行为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占用公司资源,恶化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张陶勇等,2014)。
此外,股权质押引发的“控制权转移风险”(Lee et al,2004),也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决策和战略发展的持续性,比如通过盈余管理平滑公司业绩(谢德仁等,2018),削弱企业的创新活动(文雯等,2018);利用“高送转”股利政策进行信息炒作(廖珂等,2018)等等,这些“利己”的企业决策无疑会削减公司的发展潜力,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二)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效应
也有学者认为,股权质押会对公司产生正向的积极效应。首先,不少学者否认了股权质押下大股东的“掏空”理论(王雄元等,2018),而主张股权质押带来控制权易主的潜在风险以及股价维护的动机,将对大股东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去抑制公司对高风险项目的非效率投资,并不断改善公司业绩,减少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李旎等,2015)。另外姜晓文(2019)认为,股权质押导致企业对创新活动的削减并不意味着创新的实质失效,股权质押后大股东有更强烈的动机提高公司的创新效率来平稳度过股权质押的风险期,从而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
其次,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还体现在其引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质权人角色。质权人出于对资金安全的考虑,会通过质押股权的“激励效应”来减小信贷风险(谭艳等,201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作用,促使上市公司提高业绩(Lee et al,2004)。
五、对已有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伴随着股权质押的越发盛行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学者们对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即使它属于大股东个人的行为,但它加大了大股东个人的财务杠杆,并会通过“董事会或管理层——投资决策或财务行为——财务报告”的路径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以动因、引发的风险和对企业价值不同作用效应等为一体的研究体系,其研究结论多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及局限性,股权质押研究依旧机遇与挑战并存:
(1)股权质押融资的用途为股东个人行为,而不属于公司法层面的公司行为,因此我国监管部门并未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由于缺乏对资金真实用途的披露,限制了学者们对股东真实动机的探讨。随着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对股权质押融资用途的差异化研究无疑将进一步揭露股权质押的神秘面纱。
(2)现有关于股权质押的研究大多从上市公司的视角切入,但却很少有学者研究质权方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和收益。在目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爆仓平仓已屡见不鲜的情况下,后续的研究中加强质权方的角度对股权质押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股权质押这一资本市场的“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