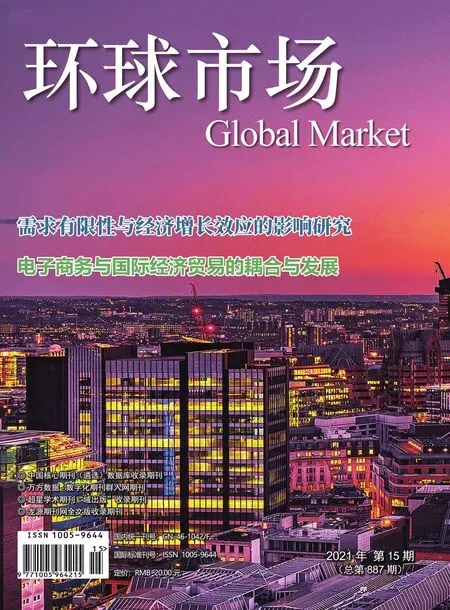对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
——基于城市地租理论视角
刘福强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一、研究背景
对城市土地进行管理与经营可以获得很多的益处:首先,可以使得城市布局更为合理、土地使用更为有效以及市区规模更为扩大;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有助于提高城市福利待遇。
因为城市土地有很多的经济价值,而对于土地利益的分配中还夹杂着国家、城市政府、土地使用者、居民等多方利益。因此,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也是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点。
本文利用城市地租理论,提出一种新型的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希望各方在城市土地利益分配上能达到一个均衡点,能够对城市土地利益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
二、城市地租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城市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及条件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绝对地租仍是土地所有权经济上的实现形式”[1]。马克思曾经的确说过:“凡是土地私有制(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存在的地方,就不支付绝对地租”[2]。而马克思只是想说明的只是无论处于何种制度体系下,只要土地所有权还存在,则绝对地租必定不会消失。
(二)城市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及条件
城市级差地租包括了两种形式,而两者不同的级差地租影响因素也是很不相同的,城市土地地段优劣影响着级差地租I,而级差地租II的决定性因素则是对城市土地进行的投资。马克思把这种投入土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以区别于作为自然条件的“土地物质”[3]。
(三)城市垄断地租产生的原因及条件
由于城市特殊位置的垄断,由此从中产生的超额利润变成城市的垄断地租。城市土地的位置才是其最大的影响因素,土地使用者通过开发土地,在城市土地上建造各种的建筑物,通过对其进行经营买卖,最终获得城市的垄断地租。
三、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有偿使用的实现方式单一
我国使用的土地有偿使用方式一直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制,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及不断地完善而日趋成熟,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显然,这种单一的土地有偿使用方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全部需要。另一方面,在没有转移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得不到这部分增值收益。
(二)土地交易行为尚不规范
据对43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协议地价平均为每平方米165元,招标地价平均为每平方米507元,拍卖地价平均为每平方米1822元,三者之比为1:3:11[4]。由此可见,使用协议出让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资产收益受损。
(三)国企改革中的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以及界定中央与地方行使所有者职能的权限。中央政府负责最主要的企业、资源以及基础设施,而剩下的则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正是由于这样的分工明确,才使得在国企改革中,有了很好的引导。
四、创新城市新型土地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家获得绝对地租
《土地管理法》指出,我们的一切城市土地都是归国家所有,因而,国家可以利用其对城市土地的绝对占有权,凭借此权而获得绝对地租。
无论什么等级的城市土地,都是需要缴纳城市绝对地租的,而且城市绝对地租的缴纳标准都是完全一致的,并不会由于土地等级与区位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缴纳标准。国家获得了绝对地租,当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国家应当尽力避免土地的实际使用者造成损失,应当好好利用这个方式,更好的将我国经济进行调节和引导。
(二)城市政府获得级差地租
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由于在城市土地的经营当中,最主要还是通过城市政府来直接操作与布局的,其对城市的布局规划以及整治等都是最主要的发力者。所以,城市政府通过将土地转让给实际使用者,因而可以获得级差地租。
城市政府获得级差地租之后,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要更加合理有效的规划城市土地,将基础设施进行完善,保护土地真实使用者的确切权益,这些都是城市政府需要做的,而这又不能直接通过中央政府来直接在城市中进行改革与引领,所以能也只能通过城市政府来引导。
(三)土地使用者通过开发土地获得平均利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一切城市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土地的使用者只有使用权,而并无真实的所有权,因而并不能获得绝对地租。在我国,国家将城市土地转让给有需要的土地使用者,然后在这块已租用土地上进行一定的投资。但是土地使用者并不能获得级差地租,因为这种必要的投资并没有改变土地的等级。所以,这些城市土地的实际使用者与其他行业一样,只能凭借投资额来获得相应的平均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