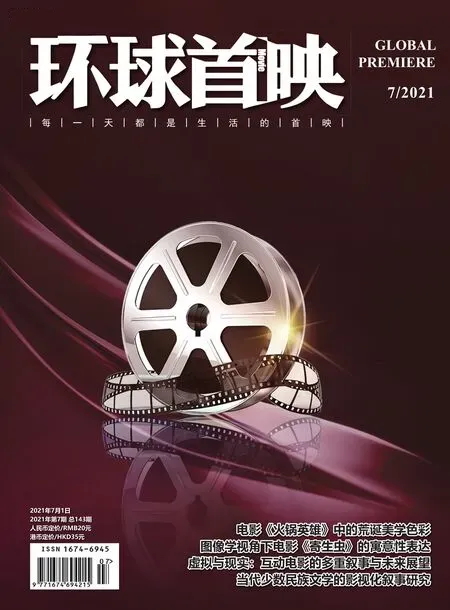谁在说话?——王昌龄宫怨诗中的发声之人及隐藏话语者
王子千 兰州交通大学
一、失宠者之声
王昌龄宫怨诗非常出色,两首代表就是这一类的典型,《西宫春怨》及《长信秋词五首(其三)》。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
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2]。
在西宫的失宠宫女无法入眠,心情难却,百无聊赖之中想要卷帘,正值春天,春色恼人,也正是这样的春色惹得宫女流连忘返。春心也无处着落,被禁锢却无人疼惜和怜爱的孤独心绪无法排解,独处深深宫闱只能依靠自己,在这样的独处中虽有难色却也不得不生活在如此的境况之下,在这样的境况中耗尽自己的一生,只能发出“红消香断有谁怜”的哀叹。心不在焉地倚着未弹的云和以一种一往情深的神态、悠长的目光望着月亮,“深见月”是宫中之人深长柔软的哀怨。诗的最后结句是诗中主人公将满腔怨恨都倾注在了昭阳殿,只看到朦朦胧胧的树影,忽影忽现,便也就随风消散吧。
这首诗是失宠宫女的怨愤之声,也是唐代宫中情事的反映。明杨慎的《升庵诗话》卷二评王昌龄的这首诗就说:“此咏赵飞燕事,亦开元末纳玉环事,借汉为喻也”[7],提到本诗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讽谏圣上,笔触鲜明不加掩饰地描述当下的社会情态。王昌龄也有借宫人之口有讽刺唐朝宫廷制度之意,所以之后王昌龄被贬,“不护细行”,就有这类宫词写作的原因。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2]。
诗的前两句紧扣班婕妤的《怨歌行》,想象班婕妤在长信宫侍奉太后、清晨扫除的情境。诗中那被丢弃的团扇就是失意宫人的象征。最后两句写空中飞过一两只乌鸦,毛羽染上了旭日的金光,人的玉颜却黯然失色,常理之下便是应该有人的美丽且分外娇嫩的脸庞但实际上却是美不如丑,人不如鸦,透着很深的怨意与无奈。
这两首都是诗人替失宠者发声,将其怨意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替失宠者怨,替不平者怨,最终会将诗人自己带入,怨着怨着倒是把诗人自己的无奈也加入其中。明面上的发声者是失宠者,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的一份情感,这是宫怨诗最常见的形式和表达角度,自然也是王昌龄宫怨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二、未得宠者之声
这一发声角度《长信秋词(其二)》《西宫秋怨》是典型代表。
高殿秋砧响夜阑,霜深犹忆御衣寒。
银灯青琐裁缝歇,还向金城明主看[2]。
长信秋词的第二首诗描写在夜深霜重的凄凉环境中,宫中女子孤独寂寞的悲惨情景。她彻夜难眠,想起进宫以来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她渴望得到君王的眷顾,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垂怜却也从未得到,在银灯下守到夜深,最后还是失望而终,日复一日,这多多少少个日夜就在指缝中溜走,却也不得不向命运低头。这首诗情感抒发较为直接,心理刻画较为生动,充分地表现了宫中失宠女子的幽怨之情。这个是还从未得宠过的宫女的心声,有所期待,但是期望渺茫,就在漫长的等待中渐渐耗尽所有的渴望,就像是盼望远征丈夫的妻子十几年如一日地期待收到讯息,却一日日增叠着失望,由希望到绝望,绝望中又升起一丝希望的心情,反反复复的寂寞与期望落空的折磨,不知这样平淡乏味的生活是福是祸,不过是苦闷的生活。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2]。
这一首也是写未得宠的期盼之声,精致的妆容以待,满心期待的盼望,激动却又紧张的心境,却在空落的良辰美景中白白等待,一次次无果。日日盼夜夜盼,期待着失落着又期待着失落着……这无穷无尽的等待却也熬得人心神交瘁,不得不放弃原本心中祈盼。这也是王昌龄在替未得宠者发声,是对更多被忽略的群体的呼喊,他对她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但也无奈于自身的渺小,也是从侧面对封建宫廷制度进行鞭挞、批判,表达不满的态度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
三、王昌龄抒己怨、暗讽谏之声
第三就是诗人自己的声音,非常明确是为了隐含自己的意愿,委婉曲折地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借宫怨之口。并且有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批判宫廷制度的不合理,批判当下社会制度的不公,批判当权者的独断,同时也是有对宫女人生的戕害。还有暗地里讽谏君王宠幸无度,无心社稷,无心黎民百姓,更多的或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之情。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中进士,时年三十二岁,入仕长安约七年左右,写作《长信秋词》等宫怨作品时已近不惑之年,而这时诗人还只是一个九品校书郎[4]。而他又自小有雄心壮志,经如此遭遇,怀才不遇是肯定的。这一点的表现上比较明显也有确切说服力的是《长信秋词(其一)》。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2]。
中国文人的一大特点是爱以宫女自况、以写嫔妃失宠表达出不为皇上所重用的滋味,这种传统是从屈原《离骚》以夫妻之情喻君臣之义起源和发展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称赞王昌龄的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谓之唐人《骚》语可。”[5]王昌龄的宫怨诗就是这种特点,并且承袭了《离骚》的传统。这首诗便有这一层独特的意味。诗中一堆意象叠加、组合到一起,勾勒出了女子无法入眠、夜听清漏的凄凉场景,暗示了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孤单寂寞,也写出了王昌龄自己的忧愁凄凉、抑郁不得志。王昌龄通过宫怨诗主要替自己说话,发牢骚也好,讽谏具体事件或者讽刺宫廷制度也好,都是他在发声,他是主要发声者,这时的宫人便是木偶戏的道具,只是用来遮掩和躲藏真实发声者的。但此时诗人也是算作隐在幕后的人,是隐藏话语者。
四、无常命运的客观之声
除了诗人在幕后的声音,还有冷眼旁观的客观世界的视角,或者是命运的角度。例如王昌龄的《春宫曲》。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
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2]。
这首诗的表层意思是写汉代卫子夫得宠的情景,但得宠与失宠只是须臾之间的事情,仿佛流星划过天空,时过境迁也留不下什么痕迹。卫子夫也是不断地得宠又失宠,这便是命运无常的暗示,就像以一个上帝视角冷眼旁观地看待这一切。貌似是喜事的存在,“露井桃”本是愉悦欢快的气息,却隐隐透出一种不安和悲怆气息,“福兮祸所伏”,乃是宫廷常态。这样的角度就将诗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极为深刻,引人深思。
五、幕后的未承宠者之声
隐藏话语者最后一个、也是最难以发现的是隐在幕后没有在舞台中央发声的未承宠者。我们还是以《春宫曲》为例——这首诗用隐藏话语者的角度用得很好,也是它出彩的地方,含蓄蕴藉,深婉之致,尽藏其中,有不尽的言外之意。《唐诗别裁集》又云:“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己之失宠悠然可会,此《国风》之体也。”[5]许多学者都认为此诗是表达了未承宠者的羡慕、嫉妒和怨愤之情。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评此诗:“失宠者思得宠者之荣,而愈加愁恨,故有此词也。”[6]虽然说这诗是否是失宠者的愁怨之声也不能妄下断论,但“不寒而寒,赐非所赐”确实是事实。有人也认为诗人是想借此诗来讽刺唐明皇宠幸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这就要归到王昌龄自己发声那块来讨论了。
王昌龄的宫怨诗“寄同情于幽闭在深宫中的妇女,道出她们的不幸遭遇和苦闷心情,从而折射出封建制度的一个罪恶的侧面,深刻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讯息,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而“唐代有不少擅长写宫怨的诗人,而其中以王昌龄最为人所推重。”[9]王昌龄宫怨诗以汉喻唐、抒己怨、暗讽谏,意象堆积聚集成春景寂寞、秋景萧瑟的意境,最为经典的场景便是环境凄清,诗中主人公无法入眠,还讽刺了封建宫廷制度,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其余尽数作废,白白流逝。皇帝顾不了那么多的女子,后宫的禁锢与闲置是怎样扼杀了无数如花的生命,毫无价值和意义的白白等待浪费了她们的一生。而王昌龄宫怨诗最为新奇有趣的地方在于隐藏话语者的存在,有王昌龄自己作主角,也有冷静客观看待的命运视角,有失宠者的声音,还有隐在幕后的未承宠者的声音等。多重声音重叠交错,不单一存在,像多声部合奏,一首诗也被赋予了各种可能性,变得更为意蕴丰富,主题也更多样精彩,诗歌也更饱满,所表达的东西也更有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