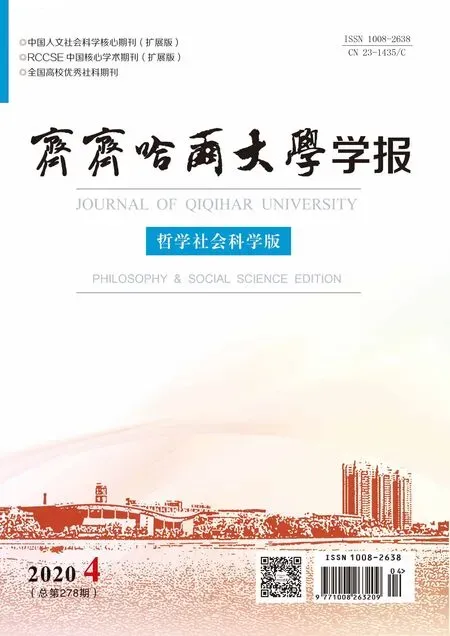中国传统“成人”视域下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思想形成
韩 旭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亳州 236800;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中国古代从“成人之道”对理想人格进行考察,而近代则从“新人”学说来探讨之。这些学说既存在其合理之处,同时也有许多糟粕的内容。冯契通过对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宏观把握,经由对“复性说”和“成性说”的会通、从传统“成人之道”中探寻自由人格的真谛、从近代“新人”中汲取自由个性力量的阐释,在实践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对这些理想人格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审视和研究,通过现代性转换,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思想。
一、对“复性说”和“成性说”的会通
对人性的考察,先哲们主要从“复性说”和“成性说”两种不同的视域进行了探讨。以儒家为代表的孔子、孟子和以道家为代表的老庄等持“复性说”的观点,而墨子、荀子以及《易传》、王夫之等则赞同“成性说”。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自我观点进行了阐发,在一定意义上正确揭示了人性论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
孔子提出了“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观点,认为人世间存在着生而知之者的圣人,即便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差异,那也是先天决定的和不可更改的事实,并以此指出了人生在不同发展阶段要完成不同使命,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些都是“天命”,人要“畏天命”,要顺命。而这种天命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锻炼和修养,方能被唤醒,从而实现天所赋予人的德性。孟子对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以为人的天性中存在善端,通过后天的教育和修养,便可“复其初”,达到圣人之境界,这就是天性。
与这种“复性说”相一致,老子主张人应该“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要顺其自然所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庄子强调“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认为自然是循天之道,人在自然面前要顺应自然,不可掺杂人为,无可妄议是非、彼此和能所之见,这样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他们以为人的自然状态是最美好的,而人为只会对自然状态附加外在压力,使之背离事物的本意。
冯契指出,孔子、孟子把人性看作是一个通过教育和培养而不断展开的过程,把人的德性与天性相贯通,“nature中即有virtue,故深造之以道,即可自得其性”[1],有其内在的依据,具有合理之处。但他们却把这种人性看作是天所赋予的,则具有先验论的倾向,尤其把“天命”作为终极目标,便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而老庄叫人们顺从命运,把“归根”于道叫做“复命”、“解脱”。这里的“命”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同时也蕴含于自然之命;把追求“逍遥”作为人之境界等,同样都具有合理的地方,因为人毕竟也是自然的产物,只有与自然为一,才会感到适从,感到自由。但主张人在自然命运面前要“无为”、“顺命”,这与儒家的天命论相通,这就把人的主观性消融在冷冰冰的规律之中,他们不懂得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是能够从“自在”逐步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辨证发展过程。
那么,人性到底为何物?是天所赋予的自然禀赋还是人为所成?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冯契对人性下了一个定义,“人性是一个由天性发展为德性的过程,它和精神由自在而自为的过程相联系着。”[2]有学者对此指出,冯契在这里是把人性看作是人的本质不断展开和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德性的培养的过程。[3]这就是说,冯契从传统天性观中不仅确认了对人性的认识,人性是人的本质内在要求,可以通过培养和锻炼得以形成,已具有了认识论的意义。同时,他还把这种培养和锻炼的人性即德性视为人的天性,就是王夫之所讲的“人之天”,也就是说,人能够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把“天之天”化为“人之天”[4],这就从本体论上对人性做了理解。一句话,冯契把认识论和本体论会通了,为其广义认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广义认识论把理想人格的培养作为认识论的重要范畴,把认识论看作是属于“整个的人”。这就打破了狭隘认识论的界限①,用中国话语方式进一步扩充和诠释了认识论,从而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巨大飞跃。
在“成性说”上,墨子、荀子、《易传》以及王夫之等是其典型的代表。墨子用素丝来作喻,感叹说人性“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亲士》)这就是说人性是善亦或恶主要在于后天的所“染”,这个“染”又与人的利相关联,“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16章兼爱下》)墨子公开讲功利主义。这样,他就把人性与人的功利、感性贯通了,不同于儒家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那样,而是把感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相连接。荀子指出人性虽恶,但经过后天的教育是可以“化性起伪”的。(《荀子·性恶》)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劝学》),而且南、北方孩子从啼哭开始时是一样的,可是后来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教使之然也”(同上),即是说,这是环境和教育的使然。《易传》则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这就是继善成性说。
冯契指出,墨子从感性上对人性做了说明,较之以儒家理性主义来说,他看到了一切活动都存在“利”的驱使,并且受到意志的作用,这是其积极的方面。但是墨子把人道原则和功利主义以此推广到自然界,以为一切自然现象也受“利”的所为,是天的意志指使,这就陷入了神学的说教。所以,如果说儒家属于先验论者,那么墨家则成为经验论者。当然,冯契也承认,墨家看到了实践经验的意义,这在认识论有其重要贡献。不过,这种实践观还是比较原始的、朴素的,具有阶级的局限性。而于荀子来说,冯契认为,他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了如何“化性起伪”,如何通过理性来通达人的德性,这有一定的意义。但荀子和孔子一样,缺乏社会实践观。“他不懂得人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实际上是把人看作生物意义上的类,以为人性这块自然的原始资料‘古今一也’。”[5]而与荀子主张的“性恶论”不同的是,《易传》肯定人有善端,这种善端有待于进一步完成。换句话说,人的德性也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强调了“习”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他们之间还是相通的。
在性习关系上,王夫之把“天人之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习与性成”之说,主要表现为他区分了“天之天”和“人之天”,并认为“天之天”可以转化为“人之天”,以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6]在冯契看来,王夫之一方面看到了人的德性生成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在此作用中日益完善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命日受,性日生”,可以不断地接受自然给予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进行自我权衡和筛选而“自取自用”以至成身成性;另一方面他的“习与性成”之说既可以使人成善,亦可以使人成恶。这是从人性的完成形态来说,人性存在善恶之别;而就其本质上来讲,这与程朱理学的“复性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人性通过不断学习、修养可达成至臻至善之德,都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7]就王夫之的“成性说”而言,冯契强调,由于他没有社会实践的观点,更不懂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但无论如何,王夫之的“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关于性与习关系的最高成就,他把这种把感性活动作为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成为“成性说”的载体,则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基于此,冯契提出了“化天性为德性”的观点,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使德性臻于完满,这就是人格的培养过程。“冯契就把人格及其培养问题作为人性研究的最高问题”[8],并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价值学说体系。
总的来说,在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继承的基础上,冯契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性中既存在天性和德性,也存在共性与个性,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人便不断地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化天性为德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德性,以此构建了融真善美和知情意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人的本质观。
二、从传统“成人之道”中探寻自由人格的真谛
理想人格(自由人格)有何标准以及如何培养?这是冯契广义认识论中的主旨,也是冯契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的核心要义,抑或者说是其终极关怀。冯契循着中国文化之源,汲取其中的营养,探寻自由人格的真谛。
先秦时期的儒家首先涉入其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理想人格做了系统的阐述。孔子认为完美人格应具有能知天、有智慧、知廉耻、善勇敢、习才艺,同时配以礼乐来美化。②即是说,完美人格应是真善美和知意情的统一,即具有仁且智的品格。这种仁且智的理想人格为冯契理想人格的实现提供了路径参考,也就是要集体帮助与个人努力相结合。[9]而于孟子、荀子来说,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不同,但在理想人格的标准上具有相通之处,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其内在要求。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四端”③,把此“四端”加以扩充、培养便能成为仁义礼智具足的像“尧舜”一样的人。他提出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的唯心主义命题。荀子则从唯物论方面加以强调,他在《劝学》篇中对理想人格这样描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他认为,具有完全、纯粹和德性、操守的人格才是真正美的人格。冯契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说,孟、荀之间的理想人格存在差别,但在如何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上,二者则有默契之处。他们都认为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修养来培养人的德性,这就为冯契关于理想人格的达成提供了可鉴之处。他不仅提出了培养自由人格的一般路径,还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明确了从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来实现人的自由的观点。[10]
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它既存在理性自觉的一面,也有仁爱的深厚情感融入其中,它是融真善美和知意情相统一的。对此,冯契首先对其采取赞许的态度。但在意志情感方面,他认为,儒家理想人格更多关注的是理性自觉,而把意志自由则置于理性自觉之下,或者说是贬低了意志自由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以后正统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看出,特别是宋明理学推崇的理性专制主义,则是把这种理性自觉推崇到了极端,把原生态的人道主义变成了反人道的了。
为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冯契对先秦墨家和道家的理想人格也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研究。与儒家崇尚伦理纲常来讲,墨家侧重于功利主义。墨家对周礼基本持反对态度,在义利观上,他们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久丧”等习俗,主张厉行节约礼仪,而不应大办特办。而道家追求的理想人格要求与自然为一,反对人为,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崇尚“逍遥游”的理想之境。老子反对儒墨在人伦中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他对“古今”、“礼法”之争持抵制态度,认为历史因道、德、礼、仁等存在而堕落,说:“失道而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又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二章》)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创造的“美”与“善”,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持批判的态度,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的观点。沿此文脉,庄子也采取“无己”的态度,认为与自然为一,才是真正的“避世”。他比较赞同老子的观点,他对现实的人类文明表示不满,主张人类应该回到远古蒙昧状态中去,过着与禽兽相通的生活,以为仁义礼乐是对人性束缚的枷锁,应该通过“心斋”、“坐忘”的工夫,忘彼此对立、忘仁义礼乐、忘能所之别,以至达到“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的境界,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儒墨尚学而至圣,道家无为而至真,这两种理想人格之说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但由于长期儒术独尊占据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这就使得以董仲舒和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成为钳制人的灵魂和扭曲人的性格的主要工具。儒家认为,道德准则是出于人的理性自觉的真理性认识,是在实践中人与自然、主观和客观、能与所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地从天性到德性演化而来的;而人的道德行为,是在理性自觉下所采取的自觉行为,不管是“舍身取义”还是“杀身成仁”都是自觉的。冯契则指出,儒家强调了理性自觉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有其合理的成分,而忽视意志自由在其中的意义,则是一种偏执之见。他认为,作为行为主体的“我”,“既是逻辑思维的主体,又是行动、感觉的主体,也是意志、情感的主体,它是一个统一的人格,表现为行动的一贯性及在行动基础上意识的一贯性。”[11]在冯契看来在造就理想人格上,必须把理性原则和感性原则相统一,而不是割裂开来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许。如萧萐父就认为,冯契高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入”亦“能出”,能够全面系统地把握中国文化,从中吸取中国文化之精髓,又不被这种文化所束缚,从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意,创作出反映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他的《智慧说三篇》就是其中的代表,把理性原则和感性原则相会通,正确回答了“王国维之问”[12]。笔者则认为,这只是触到了冯契所涉及问题的冰山一角,因为冯契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德性,这种自由德性不仅需要把理性与感性相统一,还要把真善美、知情意等相连接,这是“完整的人”所应具备的品格。这样,冯契就把人看作是有血有肉、有知情意的人格的人,从而赋予了近代“新人”平民化的身份。这既不同于章太炎的“依自说”,也有别于梁启超的“新民说”,更不同于冯友兰的“圣贤人格论”,而是实现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现代性转换。
总之,通过对冯契理想人格学说的梳理和考察,笔者发现,冯契从唯物主义视角把这种理想人格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对传统摒弃自愿原则的错误倾向应给予批判,把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相统一;另一方面对人的教育、锻炼和修养即“习以成性”的工夫来培养理想人格的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既要坚持实践和教育相互结合、世界观和德育、智育和美育相互结合以及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的相互结合,也要坚持“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的原则,从而使人的德性在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和德性自证的相互贯通下获得真正的自由,实现“显性以弘道、凝道而成德”的自由之境。
三、从近代“新人”中汲取自由个性的力量
与中国古代突出理性自觉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家、哲学家更多地强调自愿原则,强调与天斗、与地斗,突出人的意志力量、意志自由,要求人性解放,追求个性自由。龚自珍大肆宣介“风雷”精神,希冀“不拘一格降人才”,吹响了近代“新人”的号角,打响了近代“新人”的第一枪。而如何造就“新人”,他主张自我觉醒,提出了“众人之宰,自名曰我”的命题,又说“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13],以为造就理想之人,决不能像温室的花朵那样,惧怕风雷闪电,而应敢于迎接暴风骤雨,从淬厉和磨砺中不断锻造自我。魏源主张“人定胜天,造化自我”,强调人只要“用志不分,乃凝于神”[14],就能“造命”、“胜天”。谭嗣同、严复、梁启超也都从“新人”视角阐发了自己的主张,把争得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价值追求,倡导每个人都是自我生命的主宰,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获得自由的权利。
到了“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敏锐地觉察到:要实现政治上的变革,必须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个反对旧思想、批判旧道德的启蒙运动,以抵制封建传统权威主义价值观,击退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他们崇尚个性解放、追求个性自由,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在思维方式上,他们要求用科学思维方法取代经学独断论;在价值观上,坚持用近代自由主义原则取代封建权威主义;在实践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爱国启蒙运动,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冯契认为,近代这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及人道主义者严厉斥责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强调了人的尊严,强调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通过对中国近代关于理想人格的考察,冯契指出,这些理想人格不再是古之高不可攀的圣贤,不再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知下》)以及像宋明理学所讲的“醇儒”,而是一种“各因其性情之近”来培养的多样化、平民化的人格。[15]也就是他所倡导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这种自由人格有其合理性的因子,它是对人的本质要求的正确反映,深刻体现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具有真性情的时代“新人”。当然,也有学者持反对态度。如有学者认为,冯契的自由人格思想具有消解终极性或超越性的倾向,很难从现实中找到依据,以至对倡导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过于乐观[16];还有的认为,冯契对这种人格思想没有系统总结,存在偏执等。[17]而于作者来看,冯契所倡导的自由人格,虽存在不足和缺陷,但对于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来说,它是融会了百家之长,汲取各方资源而形成的更接地气的理想人格:一方面,他把意志自由作为人的重要品质,同时又把意志自由和理性自觉相统一,如他常说“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另一方面,他正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在“中国向何处去”时代主题的正确指引下,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思想。这种人格不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一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实现的理想。
正因为如此,冯契承认,中国近代哲学家确实为人的自由发展、为理想人格的实现提出了新见解、新思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具有高能力、高品格的伟大人物,这是中国近代对理想人格培养的最好解答。中国共产党秉承这些优良传统,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较为系统的理想人格理论。即“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在密切联系群众中来进行锻炼、修养,包括自我批评,这样就逐渐地使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成为教育人、培养人的组织。”[18]坚持用“共产党员”这个新人标准要求其他成员,这样有利于增强看齐意识、凝聚核心力量,也能为党和国家培养有一定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偏差:如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强调集中领导,忽视民主;强调集体精神,忽视个性解放,以至出现了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过多强调自觉原则和自我检讨,忽视了自愿原则和自我发展。为此,冯契指出,“培养人,让人能够真正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一个头等的大事,我们搞共产主义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人成为新人。”[19]一语中的。“由于人”和“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也是冯契一生所忠贞不渝的价值追求,这就是冯契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汲取中国传统“成人之道”之精华,冯契创造性地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思想,以为这种理想人格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不再是“君子”、“圣人”那样无法企及的,而是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实现的人格。而如何实现这种理想人格,冯契提出了三条基本的途径:一是坚持实践与教育的统一,二是坚持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德育、智育和美育相统一,三是坚持集体教育和个人努力相结合。这也就是说,冯契所言的理想人格是融真善美与知情意于一体,是同时具有理性自觉和意志自愿品质的自由的人。而这正是成为时代新人的应有之义。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成为时代新人这样解释道,“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要不断“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20]这样才能不断培养和造就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注释:
(1)冯契在与其师金岳霖讨论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上,提出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关于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由此,他把狭义的认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广义认识论”: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法则;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这种认识论不仅凸显了冯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深刻彰显了其特有的人格魅力。
(2)子路曾经问孔子,如何才能成人?他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具体可参见《论语·宪问》。
(3)“四端”即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以及是非都是仁义礼智的肇始,故把仁义礼智称之为“四端”。具体可参见《孟子·性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