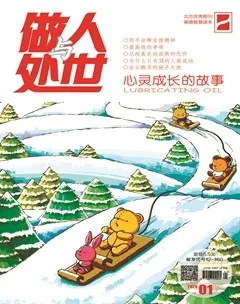此中有真意
冯娟
门罗写过一个名字很奇怪的短篇,叫《对家人的宽容之心》,以一个姐姐的口吻,叙述一家人看似普通又不与人同的生活。门罗就有这能耐,寥寥几千字,那些压抑、隐忍,没有说出口的苛责,仿佛按捺不住的火苗,争先恐后地从她的笔下旁逸斜出。
姐姐不喜欢弟弟,觉得他太不成才,读书不好,又不务正业,还啃老,靠母亲的收入过活。这其实是在哪一家都可能出现的一个弟弟,但偏偏这样浑身毛病的人,还受尽母亲的疼爱,这种愤懑,让姐姐直接对外称弟弟有精神病。姐姐因而对母亲也是怨怼的,但她自己并没有察觉。直到有一天,母亲重病住院,已发出病危通知单,姐姐守在病房外面,想起关于和母亲生活的点滴,不由得悲从中来。
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要日复一日地工作养家,她要先乘坐渡轮再坐巴士才能到工作地。但即使如此,母亲每周还会空出一个晚上带她去图书馆,回来的路上,用仅有的零钱买葡萄干给她吃。哪怕后来,姐姐结婚生子了,每周三的下午,母亲都会邀请她回娘家,一起喝杯咖啡,坐一坐,聊一聊。这些属于母亲的记忆,也是母亲对女儿的爱意,如果没有与弟弟的比较,她们该是多么温馨无碍的母女。醒悟过来的姐姐也终于明白,那些以前以为与母亲一起消磨的时间,只是为了填补时间空白,不得不做的事情,反倒构成了她们真实温馨的生活,单单追忆起这些,就已令人心碎。
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天才看过的日本纪录片电影《人生的果实》,导演以无数个缓慢写实的长镜头,向观众呈现了90岁的退休建筑师修一和87岁的妻子英子,在深山木屋里的日常生活。40多年前,热爱帆船和航海的建筑师修一,为了圆妻子的田园梦,带着她一同来到远离市区的新区,买下一块土地,开荒植树,建屋种地,一点点地修葺,搭建起了一栋充满诗情画意,又带着人间烟火的房屋。两位老人依着四时的变化,种植各样的蔬菜和果树,积肥、浇水、翻土、收获,全部亲力亲为,不假外人之手。不只如此,他们还定期外出采买日用,收拾家务,精心烹饪一日三餐,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也曾有人建议,这么大年纪了,完全可以请人来照顾你们。但他们坚持说:“我们也要努力,也要好好工作。”他们把日常的劳作,当成庄重的工作。每个晴朗的日子里,他们都会一起给果树剪枝,一起采摘树上的果实,一起收集树叶堆肥,一起收获土豆。如果有花开了,他们还要一起拍照。当时只是看着温馨,但当修一过世后,看到英子瘦小孤独的身影,站在台风肆虐过的院子里,奋力想扶起一棵被风吹倒的树干时,才终于明白,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做事,一起度过的所有时光,才是生活和生命的真意所在。
如果生計是生命的内核的话,一天天的劳作,便是包裹着它的那层厚实的果肉。这一天天的埋首,看似重复、乏味、不值一提,但好在,我们种下的每件事情,自有时间会检阅它们的价值。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