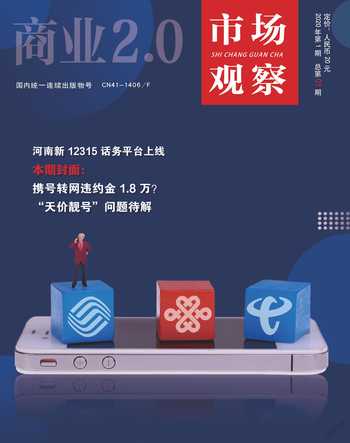金融背离实体经济与金融危机及防范政策
彭光

摘要:当前,世界金融发展强劲,促使市场层次更加丰富,金融创新产品数不胜数,金融功能持续拓展,大量人才涌入金融领域中。金融规模增长速度与扩张速度均高于实体经济,以功能与数量角度分析,和实体经济之间呈现背离发展态势。实体经济不再是金融主要依托,使得潜在金融风险增加。基于当前金融进程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背景,若是爆发金融危机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本文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工具创新关系进行简单阐述,对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下的金融危机实例进行简单分析,最后提出几点防范政策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实体经济;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
金融行业繁荣表象吸引了无数资源,使其迅速膨胀,另外在实体经济中释放“挤出效应”,进而产生数量背离。导致社会中弥漫着金融行业创造财富的幻觉,金融机构利用群众在金钱方面的渴望达成自身利润追求,粉饰、包装金融产品,在实体经济方面的服务不断减少,促使实体经济和金融产生功能背离问题。因此,通过对其相关理论实际实证进行分析,并且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为切入点讨论防范政策,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1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工具创新
以表面角度分析,金融创新使得金融脆弱性得以隐藏然而实质上其具备对金融脆弱性进行强化的能力。基于创造性因素使得传统金融衍生出全新的金融工具,虽然可以避免原有风险,然而会创造出新的风险,增加金融创新需求,使得金融数量与工具类别膨胀与金融脆弱性不断加剧[1]。基于衍生工具在风险防范方面的作用,使得金融体系中风险并未得到彻底地实时掩盖,在金融不断膨胀过程中,风险隐蔽性得到强化,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资产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个体风险被放大到影响宏观系统风险中,金融脆弱性与风险一起膨胀,导致金融风险影响力持续上升。
2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实例
2.1新兴国家金融危机
以墨西哥为例,长期以来墨西哥依靠外资促进自身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借助债券以及股票等工具进行间接投资,以达到对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直接投资目的,此种投资方式使得金融膨胀现象逐渐增加,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资本逐渐撤出。1990年,证券市场外资在总外资中的比重仅为10%,1992年则达到71.63%。证券价格进一步拉升,使得上市公司的市值显著提高,并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1993年达到39.88%。见表1。
1990—1994,墨西哥将950亿美元外资用于短期债券以及股票中,大量外资使得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并导致外汇储备与股票价格产生巨大波动,使得其金融风险抵御能力受到严重影响[2]。
自1992年之后,由于资金投入降低,使得墨西哥世纪经济开始衰退,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其没有享受到经济合作带来的福利,同时基于国际贸易逆差与竞争压力,使得其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而金融行业则非常繁荣。通过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催生出一批高价采购银行的银行家,主要开展风险业务,不断进行信贷扩张,以收回投资成本。银行个人信贷在GDP中比值持续上升,但是资产质量不断降低,1994年有8.3%贷款无法收回,高风险资产在银行净资产中的比重高达70%。并且消费者开始追捧进口奢侈品,知识信用消费日益盛行,银行将大量信用卡发放到不良部门以及个人手中,促使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持续增加。1994年,由于比索币值速降冲击,终于爆发金融危机。
2.2发达国家金融危机
以日本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邻国对日本制造业国际影响力构成挑战,并且基于石油危機余波影响,以及日本难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使得其实体行业的资金需求不断收缩。同时自由化利率导致银行存款成本增加,针对实体行业资金供需缺少平衡性的情况,1989年银行将制造业放宽比例降到20.5%,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动机开始丧失,并将目光转向房地产与证券市场。见表2。
1981年,银行对其他金融机构放款比例是3.0%,1989年上升至9.5%,导致金融泡沫与金融资产交替膨胀,使得实体经济疲软状态与金融繁荣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期货市场与债券市场萌发,一年之后即以1870万亿日元交易额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日经225股指期权交易,到1991年超越美国S&P100股指期权。同时期,日本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多,推动其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然而制造业增长动力不足,仅仅维持在5.5%增长水平。金融发酵无法在实体经济中寻找相应理由,金融膨胀使其金融风险增加[3]。
1989年,基于紧缩政策制约,日本股价出现剧烈下挫,引发泡沫破裂进而导致企业破产,使得银行的不良资产剧烈上升,金融危机由此蔓延,导致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持续低迷。
3金融危机的防范政策分析
3.1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实体经济提供基础保证
(1)对需求结构加以调整,增加消费需求。当前,消费在我国经济方面的拉动作用已经非常明显,2014年消费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率达到50%,2015年达到65%左右。然而在世界经济疲软三期叠加现实背景人,我国经济建设产生一定困难,若是消费层面缺少活力,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也会为金融膨胀提供条件,使得经济实体和金融背离情况日益加剧。
当前,中国制造克服地理困难开展市场拓展已经达到瓶颈状态,将社会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的紧迫性日益增加。应该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增加消费需求,进而为产能吸收创造需求市场,借助国内消费将产品转化为社会福利,生产要素获得报酬之后会进一步扩张生产与消费需求,通过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使得实体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4]。同时相比于受制于汇率与贸易政策因素的国际市场,可以通过消费与生产将国内市场相对稳定性向实体经济行业传递,为实体经济提供基础保障。
另外,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可以限制消费被储蓄现象替代,同时对流动性供给进行控制,减少金融膨胀条件,控制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背离程度。
然而这些过程对降低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公平性有着较大依赖性。在边际消费考察中,发现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此部分人群的投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基于实际贫富差距使得社会需求量降低,投资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之后难以实现理想的回报,进而转向金融行业,使得金融膨胀风险增加。因此,需要在保证收入差距较小与分配公平基础上,进而需求结构调整进而实现金融膨胀限制与实体经济发展目标,有效进行金融危机防范。
此方面需要政府对国内需求进行刺激,同时保证劳动力就业情况,强化扶贫力度,借助社会保障、税收等手段,充分提高低收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而达到降低贫富差距的目的。
(2)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协调发展。2015年,我国GDP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1.4%,有效提高产业结构平衡性。需要注意,我国第三产业的活力并为得到充分激发,无法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生产服务。因此,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优化的同时,需要保证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使其生产服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和第一、第二产业产生良性循环,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步稳定发展。
金融产业若是健康发展可以相关产业配置资源以及聚敛资金,同时借助宏观调控与风险分散等功能,保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然而若是金融发展快速,而实体经济缺乏增长、发展迟缓,则无法充分吸引资金,使得大量资金投入到金融行业中,使资产价格增加,金融发展就会借助资产价格增加异化成金融膨胀,并引发金融危机。
对此,需要保证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互相适应,不仅可以服务传统产业,也可以开拓新兴产业市场,保证资源得到科学分配,使产业结构充分发挥自身效能。新兴产业中中小企业中有较大比重,然而缺少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应该对相关情况加以重视,为各类企业和谐发展提供条件。金融发展需要满足第一、第二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和第三产业发展具有良好协调性,避免金融背离以及与实体经济背离等现象。
3.2优化金融监管,强化服务意识
(1)构建监管指标机制,警惕金融膨胀。监管指标机制需要包涵测量实体经济状况的指标、测度金融发展的指标,同时考虑两者联系的指标等,进而达到动态监督、管理的目的。实体经济行业,可以选择GDP、GDP增长率、工业增长值以及通货膨胀率等指标。对于金融行业,应该检测存货款指标以及M2/GDP等指标,对信贷扩张与货币供应量变动情况加以把握,促使货币市场更加稳定,并掌握金融风险情况。对于资本市场可以选择FIR、债券市场等指标。
根据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协调性,构建FIR、M2/GDP等指标警戒值,同时合理制定监管措施,在指标数值超出警戒值时,及时控制金融背离趋势。
接触长期跟踪监管指标体系,对实体经济和金融进行动态把握,在金融膨胀时予以适度监管,可以限制过多资金向金融行业投资,同时将资源分配给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潜力[5]。
金融和实体经济背离的主要表现就是数量背离,需要在数量层面构建管理机制,并开展动态监控,以提高金融膨胀警惕性,此方法在金融背离与金融危机防范方面有着显著效果。
(2)谨慎进行金融创新,优化监管法律。金融创新与其衍生工具是导致金融和实体经济背离的主要原因,监管金融创新可以将背离离心力消除,以实现金融危机防范目标。
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利润、规避监管,通过对传统工具加以创新,衍生出新兴工具,预防原有风险时也需要对新风险加以规避,进而衍生出新需求,促使金融数量工具种类等出现自我膨胀。对于金融创新,其衍生品借助基础资产和实体经济构建的联系被层层衍生与持续创新割裂,使得实体经济与金融产生脱离。
构建健全监管法律系统,借助法律强制力约束金融创新,借助法律规范性保证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础开展创新。但是金融经常在法律真空地带展开创新,在和金融创新持续“斗争”过程中,使得监管法律日益完善,所以监管法律具有一定时滞性。要求监管机构提高金融创新风险判断效率,及时研究衍生工具特点,进而提高监管法律时效性,以提高金融监管效果,控制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保证金融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服务。
在全球经济日益复杂背景下,使得实体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因此形成借助金融工具展开资产增值、风险规避以及资金融通等要求,通过金融创新,促使实体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需要得以满足,提供便利条件,创造宽松氛围。所以,监管金融创新时,应该对金融创新类型加以重视,保证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建设的创新得到稳定发展。
优化监管法律,剔除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背离的部分,以保证金融在实体经济方面的服务效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時减少金融风险隐患,达到金融危机防范目的。
结语:综上所述,实体经济和金融背离主要体现在功能与数量方面,其中数量背离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萎缩与金融过度膨胀,两者在成长速度与绝对规模方面的差异,使得金融在实体经济方面的服务自觉性丧失,进而形成功能背离。另外,基于两者背离环境,金融危机借助金融弱化性以及其他途径形成。对此本文提出对需求结构加以调整增加消费需求、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构建监管指标机制,警惕金融膨胀、谨慎进行金融创新优化监管法律等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孙畅,孙丰京,闵正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耦合研究[J].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1(03):116-121.
[2]汤铎铎,李成.全球复苏、杠杆背离与金融风险——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J].经济学动态,2018(03):13-26.
[3]王国锋.广义视角下的金融“脱实向虚”问题研究——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经常性背离关系[J].金融发展评论,2018(06):97-107.
[4]陆岷峰,杨亮.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关系及驱动思路研究[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6,36(1):3-7.
[5]蔡景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视角下的经济危机产生缘由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8(07):31-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