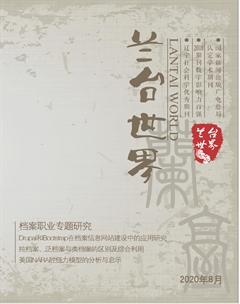《左传》“宰咺归赗”考
丁士桓
摘 要 据《左传》解释,周王于魯隐公元年遣使赠鲁惠公、仲子之丧品,但惠公死已逾年,仲子仍在世,不符合情理。考察史料及古今学人论述,可知周王赠赗时仲子已故,且早于惠公改葬,故《左传》的解释不合史实。
关键词 《左传》 宰咺归赗 仲子 丧礼
中图分类号 K877.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5-20
Abstract According to Zuo Zhuan, in the first year of Lu Yingong, the King of Zhou sent envoy to present funeral oblation to Lu Huigong and Zhong Zi, but Lu Huigong had been dea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nd Zhong Zi was still alive, so it was not log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cholars remarks show that Zhong Zi had died when King of Zhou presented the funeral oblation, which was earlier than Lu Huigongs funeral. Therefore, Zuo Zhuans explanations are not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 Zuo Zhuan; chancellor Xuan sent funeral oblation; Zhong Zi; funeral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1]17-18若诚如《左传》所言,周王赠惠公助丧品太迟缓,且送助丧品于生人(仲子),显得不符情理。古今学人就此事发表不少观点,各方争论纷呶,又均有可商榷之处,故撰拙文,敬待大方之家教正。
以《朱子语类》为例,传统观点坚持《左传》对“宰咺归赗”的解释——周王办事失礼,行事昏庸[2]2175;童书业亦信服《左传》之解释,且推得《左传》尊鲁桓公乃至尊季氏[3]231;赵光贤认为《左传》之所以认定宰咺“豫凶事”,盖因作者将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中的“夫人子氏”误作隐公元年的“仲子”[4]146;王和本赵光贤之说,证《左传》的解释非作者本意[5]87;《公羊传》解隐公元年“仲子”为“桓之母也”[6]28,解隐公二年“夫人子氏”为“隐公之母”[6]55,不存在赗生人之情况;《谷梁传》解“惠公仲子”为一人,即惠公之母、孝公之妾[7]11,解隐公二年“夫人子氏”为“隐之妻”,故宰咺归赗并非无礼[7]14;杨伯峻反驳《谷梁传》“惠公仲子为一人”之说,并引杜注及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一事以证隐公二年“夫人子氏”为桓公之母仲子[1]23。梳理上述观点,可见各方分歧源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理解差异:第一,“惠公仲子”是指一人还是两人;第二,“仲子”与“夫人子氏”是否同指桓公之母。不妨由此入手,对“宰咺归赗”一事进行考察。
一、“惠公仲子”问题
《左传》《公羊传》皆断“惠公仲子”为“惠公、仲子”,唯《谷梁传》将“惠公仲子”解释为一人。《春秋》经文仅有简短的“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一句,故单凭此句经文不能确定“惠公仲子”所指究竟为一人还是两人;《左传》默认“惠公仲子”指“惠公”、“仲子”两人,亦没有加以解释;《公羊传》以“仲子微”佐证“惠公仲子”当为二人;《谷梁传》称“母以子氏”,即仲子作为惠公之母,须冠其子“惠公”于己名前;杨士勋引《春秋》鲁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以证此处“惠公仲子”为一人:二人之赗当先书母名再书子名,一人之赗应遵照“母以子贵”原则记载[7]11。杨伯峻先生为证明“惠公仲子”实指两人,引用陈立《公羊义疏》驳斥《谷梁传》观点:“然惠公既为君矣,自必尊其母为夫人,如成风之例,何以仍称仲子?”[1]8陈立之言,源于《春秋》鲁文公四年“冬十有一年壬寅,夫人风氏薨”及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夫人风氏”即“成风”,指鲁僖公之母,虽非鲁庄公元妃,因鲁僖公为君,故礼同夫人(夫人风氏),称谥(成风)[7]95。由陈立的解释而论,“仲子”未称谥,不可能是惠公之母,故“惠公仲子”当指两人。此解释虽然说明“仲子”必不为惠公之母并证明“惠公仲子”一定为两人,但反使《公羊传》的解释陷入困境:仲子岂有资格与惠公一同受赗?
《公羊传》解“惠公仲子”,断定其非礼:“兼之非礼也。”据何休注,赗人妾“非礼”,应当“各使一使,所以异尊卑也”;“惠公”与“仲子”并列,两者地位迥异,一同受赗不符合礼法[6]32。其实“仲子”地位较为特殊,其子桓公虽不为君,但自惠公时已被立为太子,只因其年幼而隐公摄政;《左传》载“(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杨伯峻先生驳杜注“隐公奉桓公为太子”,称隐公实奉桓公为君;另据《左传》记载,时人有“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手间有‘鲁夫人字样”之传闻,充分印证“仲子”地位之特殊[1]3-4;《史记·鲁周公世家》更载仲子本将嫁隐公,惠公“夺而自妻之”,更显仲子特殊[8]1846。诚如是,仲子受赗并非不可能。
因仲子地位太过特殊,而“归赗”之事在《春秋》中记载过少,各方解释有流于“空谈”之嫌;此处“惠公仲子”并非单指惠公之母;仲子确有受赗之地位,可与惠公共同受赗;解“惠公仲子”为一人,仅凭难辨真伪的“母以子氏”之体例,证据并不充足,且惠公与仲子又非母子关系,更无他例。因此,“惠公仲子”断为“惠公、仲子”更有道理。
二、“夫人子氏”问题
《左传》认定周王给活人(仲子)送助丧品,盖因编撰者以为隐公二年“夫人子氏”为“仲子”;赵光贤、王和反驳此观点的理由为此事过于荒谬,不符合情理。但情理上的推测,并不是有力证据;更何况杨伯峻以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的记载论证“夫人子氏”当为“仲子”;单凭“常理”不足驳倒《左传》的解释,需进一步分析。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认定“夫人子氏”指桓公之母、隐公之母、隐公之妻。隐公三年,《左传》所本《春秋》记“君氏卒”[1]25,《左传》解之为隐公之母声子卒,这与《公羊传》解“夫人子氏”为声子相冲突;《公羊传》[6]59与《谷梁传》[7]15记载隐公三年“尹氏卒”,而非“君氏卒”,故无此冲突。所谓“尹氏”,均被解为“天王之大夫”。然考之《春秋》,经文中很少以“某氏”记周王卿大夫,大都称名称爵:“宰咺”“祭伯”“宰渠伯纠”“仍叔”“家父”“宰周公”“叔服”……隐公三年有“武氏子来求赙”一事,孔颖达作解,“直云武氏子不书其字,则其人未成为大夫也”[9]50,可见《春秋》记周大夫一般需详称其名。唯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1]1601、昭公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某氏”称周大夫[1]1634。但这两处“尹氏”不单指一位大夫,而是指“尹氏”一族;唯有《左传》以“尹氏”、“武氏”称呼某一位大夫,但早有学者指出《左传》史源与《春秋》不同,有一部分材料来源于他国史书[10]25,故不能因《左传》有“某氏”证鲁国记周大夫为“某氏”。况且《春秋》经文从未记载周大夫亡故之事,加之上下文均未提及此处周大夫“尹氏”为何人,此句是否为“尹氏卒”颇显可疑。《公羊传》[6]61、《谷梁传》[7]15为解释鲁国记载“尹氏卒”的缘故,提出隐公赴周王崩,又恰逢尹氏亡,桓王未即位,鲁隐公代主尹氏丧;但无任何材料能支持此说,相反《左传》载平王崩后周人奉虢公,按礼虢公主丧[9]52;《公羊传》《谷梁传》称鲁隐公主尹氏丧当为臆测。可见,《春秋》隐公三年记“尹氏卒”恐非史实。杨伯峻认为《公羊传》《谷梁传》之“尹氏卒”,盖“君”字形残而讹误为“尹”[1]26,确实有说服力,故此处作“君氏卒”更合适;既然隐公三年声子去世,那么《公羊传》解“夫人子氏”为“声子”实误。
《左传》以“仲子”解“夫人子氏”,势必面临礼法不合:仲子非为惠公元妃,其子桓公此时并未成君,怎可称“夫人”?杜预解之曰:“隐让桓为大子,成其母丧以赴诸侯,故经于此称夫人也。”[9]43此解释的可信度不高。杜预注“宰咺归仲子之赗”时曾言:“时惠公已葬,仲子未薨,因赗惠公而并赗仲子也。赗惠公而并赗仲子者皆非礼也。”[9]40可见依杜注,仲子生前不受夫人之名,死后方才得夫人名号。为何周王独赗在世的仲子而不赗在世的声子?杜注若要成立,唯有仲子地位高于声子,周王才会赗仲子而非声子。这种情况成立的可能性极低:前文已论,仲子极其特殊,但周王恐难晓鲁宫室秘辛,怎知仲子的特殊地位;《左传》载惠公元妃孟子卒后继室以声子[1]3,卑为“贱妾”[8]1844的声子虽只能享正室夫人之名,但仲子却连夫人之名都不得享;最后,周王在不知情時理当赗名分更尊的声子而非仲子。由此可见杜注实不成立。
杨伯峻先生以鲁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而古人守孝三年,反推鲁隐公二年之“夫人子氏”为仲子:“九月,考仲子之宫”[1]43,即宫室(据杜注,此处当为祭祀之宗庙)初成时的祭祀,说明此时宫室落成;隐公五年减去守丧三年,正好与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相合。但此推论存在两个问题:其一,鲁国未必严遵“守丧三年”礼仪;其二,先人宗庙不一定只能在守丧期过后立即建成,可以亡故多年后方立。早有学者提出,“三年之丧不祭不乐”之风俗,春秋时期未必存在[11]9-11。下举四例证之。鲁成公三年年初,“新宫焚”[1]886,即宣公庙火灾,说明此时成公之庙已成;考虑宫庙建筑需要一定时间,加之鲁宣公亡于宣公十八年年末,因此宣公之庙落成时很可能处于“守丧三年”期内。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1]567;鲁僖公亡于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1]539,至文公入僖公于太庙时,仅踰二年,不足三年,全然不符“守丧三年”之礼法。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1]1790,可见定公刚亡,鲁人仍举行郊祀,不守三年之丧。《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劝滕定公世子然友奉三年之丧,然友以鲁先君亦不奉三年之丧反驳孟子[12]216。上述材料说明,当时鲁国应当没有守丧三年内不祀的礼仪。至于第二个问题,例证不少,如鲁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公羊传》认定此“武宫”乃武宫宗庙[6]719,杜预认为此庙兼有祭祀武公及纪念武功之意[9]441。鲁武公为鲁孝公之父,早于《春秋》,成公年间方立宗庙,可见先人宗庙可以在先人死后多年才得立。这两个问题说明“考仲子之宫”不足以反证“夫人子氏”为仲子。
故《左传》以“夫人子氏”为“仲子”的解释不成立,仲子之死很可能在《春秋》之前,因此不见史籍;《谷梁传》以“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妻,符合当时礼法,最能说通,更贴合史实。
三、结论
《左传》以“赠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评价“宰咺归赗”一事,批评周王赠丧品既缓又赠生人。据上文分析可知,周王没有归赗于生人,“豫凶事”自然不成立。至于“赠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考之《左传》亦不成立。惠公死时,鲁宋交战,缺葬礼;隐公元年九月鲁宋停战,冬十月鲁人改葬惠公。惠公正式下葬当于元年十月,宰咺归赗并不迟缓。可见《左传》对“宰咺归赗”的解释不仅与《春秋》礼法不符,甚至上下文抵牾。这显然说明此处解经内容当为后人为解《春秋》经文所添,而非《左传》文本所固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黄士毅,等.朱子语类汇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上)[J].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期),1980.
[5]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4).
[6]何休,等.春秋公羊传注疏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7]范宁,等.春秋谷梁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司马迁,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杜预,等.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J].中国史研究,1993(2).
[11]丁鼎.三年之丧源流考论[J].史学集刊,2001(1).
[12]王弼,等.孟子注疏[M].上海:中华书局,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