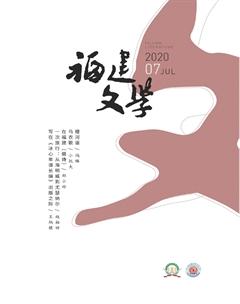写在《冰心年谱长编》出版之际
王炳根
2019年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冰心年谱长编》,之后,福州举行了一次出版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近30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福州、厦门等地。冰心年谱从开始到出版,前后十余年,字数达200多万字,1822页,从头翻一遍都不易。座谈会的一些观点先后见诸媒体,我在会上也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但由于时间原因,意见没有展开。这里,我用书面做些说明。
一、资料来源
编著年谱,史料是第一的,而新资料(包括未刊者)占有量,直接影响着年谱的价值。冰心资料丰富,自五四运动登上文坛,到1999年谢世,整整80年,而她(1900年生于福州)又与一个多灾多难、充满希望的世纪同行,一生多有作品与纪事,个体丰富的史料编织在世纪的主杆上,有种世纪叙述的意味。我充分使用了那些宝贵的史料,同时又增加了大量的新资料,使得有可能枯燥的冰心年谱既具历史感又有新颖度,成为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好读的作品。
由于冰心年谱涉事太多,编著过程便花了6年时间,电子版多次修订,最后还打印了纸质样书,做最后的修订。样书到我手上,恰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一位讲席教授来访,他翻阅了全书,惊讶史料丰富的同时,特别询问资料的来源,我告诉了他,同时在冰心年谱的前言与后记中也有交代。
1992年冰心研究会筹备成立之时,便是搜集资料的开始。当时福建师大中文系在读研究生李玲和姚向青被派北上,北京、南京、上海,一路扫来,获得第一批宝贵资料。冰心研究会成立后,即着手设计与建造冰心文学馆。这是一个作家博物馆,展览冰心生平与创作,需要大量的文字资料、图片、手迹、始发报刊、实物等,除举办两次大型展览活动而获得之外(一次是“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一次是“冰心作品书法与绘画大展”),我自己也多次外出寻访,到过福州、烟台、重庆、昆明等几处冰心生活过的地方,北京更不用说,循着冰心的足迹,每次都是收获盈箧,使得冰心文学馆甫一开张,便以资料丰富的形象面世。
1997年冰心文学馆开馆之后,我除了管理这个馆之外,便是继续搜集资料,进行研究。我先后四次访问冰心留学美国时的母校——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以及短期进修的康奈尔大学,吴文藻就读并留下冰心足迹的达特默思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查阅了她的毕业论文、成绩单、手迹、照片及校刊等;多次到日本进行访问,包括她所任教的东京大学、外交官邸以及度假的轻井泽、箱根等地,2005年还到关西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与日本学者、旅日的中国学者进行广泛的接触,找到了冰心在日本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包括她描写宋美龄的多篇文章。我对收集的资料,采取了系统的研究与使用的方式,也就是搜集、整理、研究、著文、展览同时进行,并且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命题:非文本研究。先后出版了《冰心:非文本研究》和续集,为编著冰心年谱准备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2004年2月,冰心逝世5周年之际,其家人决定将冰心生前居住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34单元的遗物,全部捐给冰心文学馆。我们用了三个10吨的集装箱运回福州。这里有冰心晚年用过的实物,各个时期穿着的服饰,全国书法家和画家赠给冰心的字画,大量的书籍刊物,冰心作品的始发刊、剪报、手稿,书信、贺年卡,尤其有冰心与吴文藻的笔记、日记、长达20多年的家庭账本等。这些都进入年谱之中。我还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作协等单位,查阅了冰心与吴文藻的档案,又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是之前完全不知晓的内容。
冰心文学馆建成后,成为冰心研究的中心,而我既是会长又是馆长。我主持过四届冰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一次的研讨会都有新发现;阅读了冰心与吴文藻发表的全部文学作品、论文与学术著作,发掘了沉睡在故纸堆里的佚文,研究过所能找到的手稿与手迹;阅读、整理、主编了自冰心登上文坛以来对冰心的评论与研究的10卷本论文集“冰心研究丛书”,主编发表最新冰心研究成果的《爱心》杂志。自1991年之后,我与晚年冰心有长达10年的接触与交谈,虽不能时常陪侍一旁,但每年必有两三次的见面,每一回,都做了详细的现场记录。
可以说,冰心年谱资料的搜集,始于由我发起成立的冰心研究会,而主持建立与管理的冰心文学馆,又为我在国内及世界各地搜集冰心资料,提供了方便。同时,冰心研究会与冰心文学馆本身也成了冰心年谱中的重要事件。整个过程,前后持续20多年,我以日记的方式,一一记录在案。
二、阅读提示
“毛茸茸的质感”。座谈会上,有学者讲到这部书是“年谱”,但详细到“日谱”的程度。“这样逐日的记载实属罕见,”冰心的儿子吴平则说,“本书资料广泛,涉及面广,笔触精细,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世纪36500天,天天有记载,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尽可能做到,尤其是使用了冰心与吴文藻的笔记、日记后。吴先生是社会学家,事无巨细都可能记录在案,冰心晚年日记,也是有事基本不落,尤其有来访者的签名本,这些都使得冰心年谱有了细到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细”与“全”是这部冰心年谱的最大特点,与我最初“追求一种主杆下毛茸茸的质感”相吻合。
家世。查海军历史资料,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于1927年1月27日被北京政府国务院摄政大总统之职顾维均授予海军中将军衔;除经常写到的三个弟弟之外,冰心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弟弟名为谢为喜。两处属新增。冰心的母亲杨福慈,之前的文字中,知道是“大家闺秀”,较为笼统,冰心年谱将近年考证坐实的详细资料,作为附录收入。
“说部丛书”。根据冰心的回忆,她11岁之前阅读到的文学作品,数量惊人,中国古典名著不用说,还有较偏的《天雨花》《再生缘》《凤双飞》等。尤其在《我的文学生活》中竟有这样一句话:“到了11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都没有深究“全部‘说部丛书”的含量,其实这是一个很惊人的阅读量。“说部丛书”是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出版的一套大型丛书。开始是政治、科技作品,之后是文学作品,从1903年开始到1924年结束,前后长达22年。“说部丛书”四集本:初集、二集、三集各100种,四集22种。总计322种。我请研究者到国家图书馆查找,不全,又到上海图书馆,两家馆都凑不齐一整套。一次在上海开文学博物馆会议,我说到这个情况,周立民先生告知,巴金故居有一套完整的,我去找了,三楼上有个专门的书架存放这套书,但也不全,重复者多。几处查找信息凑齐,得出结论:初集100种完成于光绪末年(1908年),以后的三集均为民国时期的出版物。那么,可以说,冰心在11岁之前“看完了全部”指的就是这个初集的100种。后来,冰心在她的作品中,多次提及這套丛书里的书名与内容。书没有找齐,但这100部的目录找齐了,冰心年谱作为附录收入。
处女作。关于冰心的处女作,有两种观点,一个以“女学生谢婉莹投稿”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1919年8月25日,北京《晨报》)为记,另一个用稍晚以“冰心”笔名发表的小说《两个家庭》(1919年9月18日至22日,北京《晨报》)为是。但实际上,冰心创作的诗更早,即1914年至1918年上中学时的“集龚”,就是在龚自珍的诗中,挑选诗句,重新组合,年少的冰心非常迷恋玩这种“七巧板”,“集龚”成了不少的诗,自称为“少作”。晚年的冰心还记得年少的“集龚”诗,抄了8首给严文井。《冰心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未收入,冰心年谱刊出。
《春水》手迹。因为后人整理周作人日记,冰心抄写于1922年11月、现存日本九州大学的《春水》手迹(182首,115页,大小尺寸为17.4×13.0厘米,以毛笔小楷竖行双面书写于无格宣纸,线装成册)浮出水面。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冰心手迹。冰心年谱中梳理了手迹的产生、流出与发现,梳理了冰心与周作人的书信往来等密切联系。
美欧行。1936年8月13日至1937年6月29日,冰心随丈夫、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文藻进行一年的美欧之行,但冰心留下的文字极少,研究者也只是根据冰心的文字做简单的描述。由于刘涛先生发现了冰心1937年2月14日在巴黎拉丁区中法友谊会上的演讲(留学生孙鲁生记录整理成稿,《冰心女士在巴黎演讲——由出国到现在》,5月26—29日连载于《世界日报·妇女界》),使得这一年冰心的行程具体化,内容也增多了,冰心年谱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与国民政府、宋美龄。抗战期间,冰心先在云南、后到重庆,与国民政府尤其是宋美龄有较多联系。多年来出于政治的原因,对此多有回避与遮蔽。本着对历史的尊重,冰心年谱较详细地记载了冰心与国民政府尤其是宋美龄的联系与交往,包括任职、活动、处理公务等。
“二吴二谢”起义。1946年至1951年,冰心随在盟国中华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任职的吴文藻先生旅居日本,其间,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驻日代表团曾有过未遂的起义。这个起义与吴文藻和冰心密切相关,曾有“二吴二谢”在东京密谋起义之说(另一吴是吴半农、谢为谢南光)。但由于未见当事者的文字及研究者的文章,只能是一个悬案。后来,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的档案中,找到一件当事者吴半农对吴文藻密谋起义的文字材料《关于吴文藻》(1969年2月14日),并且从曾任代表团团长秘书的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央日报》记者赵浩生、丁群《名人传记》等文章中得到坐实,冰心年谱详细记载了这次未遂起义的全过程。
东京大学任教。旅日期间,冰心曾到东京大学任教,成为“红门”第一位女教授,但具体任教时间、教职、薪金等均不详。我曾专门到东京大学走访,并委托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林敏洁进行考察,将这一段任教情况记入冰心年谱,并有专题报告。冰心离开日本回到北京,以前一般是讲受新中国召唤,而实际的情况比较复杂,冰心年谱记载了这种复杂的历史真实。
家庭账本。冰心在“文革”中,接受批斗、被抄家、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冰心年谱根据日记一一厘清。“文革”中,冰心不可能写作,但实际她的笔记却一直没有停止,这个笔记就是记载每日家庭的开支,从1968年5月至1983年5月,具体到1分钱都记录,这就是几大本的“家庭账本”。家庭账本在《冰心日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中收入了小部分,冰心年谱全部刊出。家庭账本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冰心当年的心境,而琐碎的家庭开支,则反映了那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状况。冰心年谱为保持其完整性,以附录的方式收入,篇幅达近200页。
接待外宾。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与友好人士纷纷来访中国。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是来访的重点,由于冰心的知名度、吴文藻“解放”较早,两人隔三岔五便被安排会见外宾,成了特殊时期的“中国发言人”,时间长达6年左右。吴文藻日记、笔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有关冰心及两人共同会见的部分均收入冰心年谱。此情况,之前鲜有人提及。
题字与接待。冰心晚年有大量的题字,冰心年谱无法全部收入,但大部分都有记载。80岁之后,冰心由于行动不便,不能外出,与友人及社会各界的交往,只能在家与医院中。有意思的是,冰心设有签名本,凡来访者,无论高层领导还是平民百姓,是名人记者还是小朋友,均一一签名,包括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等,来一次签名一次,有的还有留言,十几个笔记本满满当当。这些都被整理,按月份进入年谱之中,每个月的人名都是洋洋大观。按《冰心年谱长编》的体例,人名要进入索引,统计了一下,冰心年谱中的人名过万,如果全部进入索引,得要大量的篇幅,最后只能择其要者列编索引。
冰心研究会与冰心文学馆。1992年12月,冰心研究会成立,1997年8月,冰心文学馆建成开馆。作为两件文化事件,由于与冰心的生命同行,故而在冰心年谱中得到了完整而详尽的记载。
冰心葬礼。送别冰心被人称为“世纪葬礼”,冰心1999年2月28日逝世,人们于3月19日送别,其间有大量的悼念文字,发表于报刊、互联网,有的存于民间,吊唁、送别花篮、挽联等极多,这些都按日载入冰心年谱。
纠错。冰心年谱按年月日顺序编著,发现之前的全集、书信、专著中有一些错误,尤其是书信的时间落款、作品的排列顺序等,冰心年谱中纠正了大约几十处,以免以讹传讹。
三、有待补充与订正
不用说,冰心年谱存在遗漏、缺失、疏忽等方面的问题,留下遗憾在所难免。以一己之力,面对一个世纪一位名人的一生,实在有力不从心之感。仅编著者意识到的,便有四大板块。
一是1938年冰心离开燕南园66号,存放的阁楼中的资料。这批资料有十几箱,包括之前的书信(父母的家书,与吴文藻恋爱期间的情书,与作家、编辑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笔记、教案、鲁迅等赠送的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住进66号小楼,存放之物被洗劫一空,不知去向。冰心当时已有很高的知名度,焚烧与化浆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是被日本人运往日本。我曾到日本东亚文化中心等处寻访,无果,并且得知,目前日本尚有未开启的从中国运来之物。但也可能有些散失在国内。1984年初,吴文藻曾找到一本自己1923年赴美留学的日记,并说那时与冰心开始交往。但遗憾的是,这个日记本仅记下这一条与冰心有关的信息:“8月17日由沪乘邮轮赴美留学,船上没有耽几天即结识莹。”二是旅居日本的资料。冰心旅居日本5年,吴文藻作为社会学家,收集了大量的日本战后资料,记录了他们的活动,这一批私人档案,在回到北京之后,上交给了国家安全部门,作为研究战后日本的第一手资料。我曾去有关部门了解过,不知存放何处,就是能找到,恐怕也不能查阅。三是“文革”抄家时丢失的资料。四是有些资料目前尚不宜公开。
四个板块的资料,有的可能永远消失,有的则可能在日后歲月中,渐渐浮出水面。这就只能寄希望于后人了。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