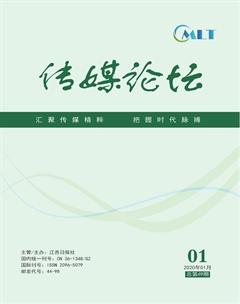探析宗族与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
孙程程
摘 要:在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引领下,保护传统古村落的宝贵文化遗产,守住民间文化净土,记住乡情,势在必行。宗族向来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范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体现了汉人特殊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1],在古村落保护与传承的进程中,宗族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根据田野调查经验和族谱等相关文献资料,以广西桂林毛村黄氏宗族为个案,旨在通过他们的文化活动来阐释宗族在传统古村落保护之路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宗族;古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01-0-03
一、引言
在我国华中和东南地区,许多村落完全由单姓人群居住,或者单姓人群占绝大部分。位于桂林市东南部的毛村,是单姓宗族聚居的客家村落。村落中黄氏宗族沿着始祖冬进公这一支血脉,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文化辉煌时期族群团结共进之路。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重视文化建设,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等政策的推进,毛村黄氏一族迎来了文化复兴的春天。村中黄氏宗亲们怀着对于家族历史的珍视以及對全族团结共进的渴望,于2013年开启了以修订族谱、修缮祖庙为代表的宗族文化重建之路。笔者将以在2018年9月~2019年6月的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相关资料,以毛村为例探析当今社会宗族与古村落保护间的关系。
二、毛村宗族文化的发展境况
(一)宗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2013年,对于毛村黄氏宗亲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可以看作是毛村恢复宗族文化建设的开端。7月17日,桂林毛氏宗亲通过召开宗亲会议,进行了关于修缮祖庙圣母宫以及四大房祠堂,保护村内石碑等历史文物和系统修订毛村族谱等事项的商讨,并倡导恢复每年回村娶亲访友、拜祀先祖的老传统,约定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为回村祭祖访亲日,届时举行盛大的祭祖大会。同年8月,毛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为受国家政策保护的古村落。国家的支持作为一种催化剂,推动了宗族文化复兴的进程。
乡民们紧锣密鼓的展开了对祭祖大会的筹划工作,经过一系列预备会议的讨论及分工。毛村于该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成功举办了首届祭祖大会,来自周边省、市、县的近800人返乡参与。第二届祭祖大会于2014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日如期而至,通过观看理事会保存的影像资料以及宗亲的现场讲解,笔者详尽的感受到了祭祖大会的盛况。大会当天,场面十分盛大,欢呼声,鞭炮声,敲锣打鼓声,声声入耳,更有本村和外来的舞狮表扬助兴。在圣母宫前,大会中安排了迎宗亲、代表讲话与共唱会歌、竞香活动与敬香仪式、节目表演、午宴、宗亲捐款、送宗亲等活动。无论是迎宗亲时的热闹繁盛,还是共唱会歌时的热泪盈眶,还是捐款时的积极踊跃,都有力的展现了黄氏宗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体现出宗亲们深切的敬祖、爱祖之心。
不可置否的是,活动的顺利推进有赖于宗族内部有序的组织——桂林毛氏宗亲理事会,理事会辗转各地开会议事,并制定章程来指导实践,为宗族文化重建做着充分的准备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忙碌,正如许烺光所指出的中国宗族特征一般,毛村建立了明确的宗族组织,明确的行为规则,形成了一个具备领导力量的会议集团,拥有了以宗亲理事会为代表的领导力量,清晰的人员工作分配名单,以世系关系为纽带的宗亲们重新团结在一起,有了更多了合作。[2]
(二)宗族文化面临的挑战
在我国淳朴的乡土社会,宗族的形成不单是一个实体的,由人情推动结合起来的功能团体,更是以世系的血缘关系与共同的祖先崇拜为纽带的结合,盛大的祭祖大会有力的展现了黄氏宗族文化中深厚的思想意蕴与内涵。
然而,2015年的第三届祭祖大会因故未能举办。不仅如此,直到2018年,毛村的祭祖大会都处于停滞状态。为何理事会章程中的“每年回村祭祖访亲,举行盛大仪式,毛村人欢聚一堂”一条成为愿景?通过多方访谈,笔者得知,宗亲们于2015年时修改计划,拟四年举办一次。而我们追问到为何四年时间已过,2018年的大会也没能举办?在被访谈理事会成员隐晦的言辞中我们了解到主要原因是活动经费不足。虽然没有举办盛大仪式,但是我们了解到,每年都会有部分宗亲回乡进行祭拜、访亲。
由此可见,即使村中无法达成八月十八日宗亲们欢聚一堂的场景,也无法隔断宗亲们敬祖爱祖之心。我们相信,祭祖大会仅仅是形式上的停滞,其中蕴含的村民们淳朴而原始的民间信仰是不会停止传承的,他根植于民众的心意与思维之中,是村落社会整合的精神动力。应当承认,这里反映出村落中宗亲们面临着一些由现实性问题带来的挑战。那么八月十八回乡祭祖的惯习,在未来的时间里还会延续下去吗?或是如昙花一现,消失在村落历史发展长河中呢?问题的答案仍取决于宗族核心组织——理事会的规划方案,由此引发了笔者关于毛村黄氏宗族在村落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思考。
三、以宗族为核心的村落文化保护
(一)宗亲理事会的凝聚作用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向来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范式。水有源,木有根,“围绕家、宗族以及祖宗的观念,塑造了传统乡民在家庭价值和行为方式的基本逻辑”[3],在毛村黄氏宗族中也体现了这种由先祖血缘纽带联结而成的和谐状态。
而一切和谐的背后都因有人在默默奉献。正如毛村宗亲理事会“爱国爱家,尊祖敬宗,敦亲睦族,弘扬祖德”的行动宗旨所言。宗亲理事会作为群众拥护的宗族组织,在黄氏宗亲一方来看,该组织对内处理本地域、本族群的事务,对外协助完成各项服务。这都是对宗族以及宗族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再创造,有利于培养宗亲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宗亲的集体认同,为宗族文化保护注入了精神力量,宗亲们募捐的善款支撑着祭祀活动的延续,是提供了物质力量。在这样由同姓聚集而成的古村落,发扬宗族文化,实际上顺应了毛村文化传承的需要,而且以实际的行动回应了国家振兴乡村社会的号召。
(二)文化遗产修复的作用
“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灵魂”[4],宗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保护与传承村落文化的力量之源。关注前人研究我们发现,数年前,对毛村黄氏宗族进行文化研究时存在的一大问题是谱系记载不完整、不明确,可资参考之文献不足。而重修族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经过三年的悉心打造,理事会呈现给人们“正统化”的、官方的谱系图,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更有力地消解了由于族群内部由于族谱说法不同而引发的纷争。
修订族谱更为村民带来了潜在的发展契机,宗亲血脉承载着人脉,在人际沟通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人脉中实际蕴含着无限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宗亲们互帮互助是先祖的心愿,每一位宗亲都团结奋进,共创美好的未来,是宗亲们的共同夙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是文化复兴,在毛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黄氏宗亲参与下的毛村的文化复兴,便是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优秀民间文化的复兴。如今,重点保护毛村“船家人”独特的精神财富和以祖庙、宗祠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是毛村文化保护的必由之路。
四、宗族与古村落的现实境遇
(一)“后宗族时代”的难题
传统古村落面对着城镇化飞速发展的现状,使得保护村落存在着许多难题,宗族内亦存在着外界无法想象的困扰。宗祠、族谱等物质外显形态是宗族文化传承的载体,理应珍视。但笔者通过聚焦于宗族这个群体的状态,思考其实际存在的作用,并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发现,村落中老齡化较为严重,处于青壮年的宗亲们大都去了桂林市里或周边其他地域谋职、定居,且毛村黄氏宗亲的地域分布呈现分散状态,仅逢年过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才会归乡团聚。宗族内势必面临着参与活动人数减少,举办祭祖活动难度加大的挑战,这是不利于村落整体发展的趋势。
面对此种境况,早有学者提出了相关见解,钱杭提出了“后宗族时代”的概念引人深思,实际上毛村正是迎来了它的“后宗族时代”。“后”宗族,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这一性质的父系世系关系与宗族传统的聚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5]。与前宗族时代有聚合无世系的特征相比,这里的宗族,确实具备着更多的文化象征意义。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等时代浪潮的推进,宗族文化依旧是我们研究古村落保护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千百年来的传统,所以即使是后宗族时代,宗族也存在不绝的生命活力,守护着千年的古村落。
(二)宗族与村落保护
1.利益——保护村落的驱动力
基于如此现实的文化生存危机,根据前人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持功能需求论的学者们认为,“乡村宗族的强化,其原因在于村民理性地选择了血缘关系与家族作为实现他们利益的手段。[6]这里存在对于宗族文化的重利主义的论调。王铭铭认为宗族文化的复兴,旨在农村互助关系的复兴,强调了宗族对血缘家族势力的强化作用。
在与村落的互动关系中,宗族是村落自然发展的产物,具有保护村落文化的义务。然而在如今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毛村是否存在正如曾国华指出的 “宗族搭台、经济唱戏”[7]的宗族运作模式?我们还是要回到毛村文化重建之路的起点来看。通过调查我们现在,国家颁布保护传统古村落的政策成为一个契机,直接推动了毛村以宗旨文化复兴为代表的守护文化之路。着力建构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合法化”地位,进而建构宗族在国家历史中的 “正统化”地位,[8]村落与当地村民能够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例如,宗族在一系列活动中募得数万元的捐款,全部投入了乡村建设。当地老人们面对近年来不断去访问的媒体与各高校学者,都是积极的配合,语调中洋溢着自豪感与归属感,可以看得出他们期盼着自己的家园能够因此而受益。通过访谈与收集到的资料,都体现出宗亲们在积极的当宗族文化的推介人,担起了为村落谋发展的任务。
2.情感——保护村落的内核动力
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演化使得中国宗族具备复杂性与独特魅力。除却经济利益的作用力,水有源木有根,“宗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通过对其具体的时空脉络进行考察研究可以发现[9],在毛村人员的是以冬进公一支血脉相传的四房子孙构成,历经600年风风雨雨,经过文化的兴衰进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开放前,被破坏的只是宗族外在的文化形态,如祖庙等,其内在的深层结构并未遭到实质性的破坏。而我们看到的其一系列的文化修复活动,也应该认清物质形态,不是必要的条件。基于毛村“传统亲属制度的层结构”,在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作用下,从宗族派生出来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是一种本体性需求。[10]人们对于保护生存环境的诉求,对集体记忆的珍视,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是长久以来支撑宗亲们进行文化的重建和再创造的契机,也是村落文化得以传承的内核动力。
五、结语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毛村“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特征。”[11]而这对传统古村落保护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在“后宗族时代”与“后乡土时代”的双重作用下,毛村的古村落保护之路充满着挑战。毛村黄氏宗亲理事会作为宗族的权威组织,对内具有处理各项宗族事务的话语权,对外是毛村黄氏宗亲的代表,组织性质决定了其承担着保护和传承宗族文化,带领宗亲守护家园,开创美好生活的职责。而面对现如今一系列不利于文化传承的现实问题,是时代在潜移默化中消解着宗族内部机制,他们是否依然想要改变这样的境遇?如何能更好地进行文化建设?答案是肯定的,同时是村民们正在不停思索的[12]。尽管有一系列的阻力,但以宗族文化为依托,以黄氏宗亲的需求为发展动力,无疑是保护毛村文化生态,实现村落良好发展的关键路径。
参考文献:
[1][2]钱杭.论汉人宗族的内源性根据[J].史林,1995:1-15.5,3.
[3]陈靖.追根认祖:一种国家与乡民关系的文化建构——一个壮家宗族复兴的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14:75-82.75.
[4]新浪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http://k.sina.com.cn/article_1708763410_65d9a91202000jahx.html,2019年2月18日.
[5]钱杭.论“后宗族形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1:80-84.80.(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6][9]周建新.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J].民族研究,2006:93-101+110.98,97.
[7]曾国华.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J].思想战线,2004:114-119.117.
[8]陈靖.追根认祖:一种国家与乡民关系的文化建构——一个壮家宗族复兴的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14:75-82.78.
[10]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148-156.151.
[11]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人文杂志, 2010:161-168.163.
[12]郑土有.“自鄙”、”自珍”与”自毁”——关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