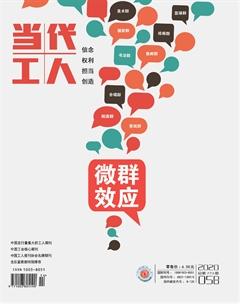时间幻觉
汪磊
时间是什么,时间之前是什么?
宇宙大爆炸始于奇点,奇点之前是什么?一种说法,奇点之前没有时间,时间是大爆炸的产物,一种高维度空间。
另一种说法,时间从未存在过,是想象的产物。不同人想象力不一样,感知的时间就不一样。同样的一年,对有的人漫长,对有的人短暂。同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下感知的时间也不一样。快乐的时候时间快,痛苦的时候时间慢。
“广义相对论”得到验证后,世界掀起了一股讨论时间的风潮。有记者采访爱因斯坦,怎么理解时间的快慢,爱因斯坦说:“坐在炽热的火炉旁,时间就过得慢,和漂亮的女士聊天,时间就过得快。”
30岁生日那天,我在一艘散货船上,机舱里柴油机咆哮,轰鸣,震动。下午茶时间(3点半左右),集控室中,轮机长不在。大管轮在看监控器,说某个缸排气温度有点儿高。二管轮带一个机工在备件间找备件,准备检修发电机。机工长去甲板抽烟了,另一个机工坐电脑前看邮件。我和电机员坐在控制箱旁的沙发上,我端着有裂纹的白色瓷杯,说:“怎么感觉从20岁到30岁嗖的一下,30岁到40岁也这样吗?”比我年长10岁的电机员笑道:“呵呵,是,也是嗖的一下。”
梵典《僧只律》记载:“一刹那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现在补充一条:十年为一嗖。
之前的10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像被谁偷去了。如果不是和电机员的“深刻”对话,那一天很可能也会淹没于茫茫记忆中,成为下一“嗖”中微不足道的三十须臾。
回首往昔,物是人非,感慨人生如白駒过隙,只不过是我们的记忆消退了。曾经耳鬓厮磨、亲昵无间的人,现在语境生疏、形同陌人,不是时间过得快,是我们的大脑清除了那些记忆。
丢掉了记忆,就丢掉了时间。两人坐在公园长椅上默默发呆的那个下午,何其悠闲、漫长,它去哪儿了?
我们感受最真切的时间是“现在”,“现在”这个概念其实莫名其妙。如果有一门语言里没有这个词语,反倒更合理。这门语言只有三种时态:过去时,完成时,将来时。“现在”是区分“过去”和“将来”的一个假设条件,它并不真实存在。当你说“现在”,指的是半秒钟之前,还是现在?
科学家另有一套解释时间的理论——人类大脑“缺陷”的产物。我们太容易遗忘,让时间有机可乘,填充空洞,将我们的思维困住。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后改编成电影《降临》)借此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外星文明在3000年后需要人类的帮助,该文明具有操控时空的能力,答应回到过去报答人类,传授人类理解时间的能力。传授的方式是学习他们的文字,对语言的理解,直到影响人的世界观。女主角最先理解了外星文字,突破思维藩篱,理解了时间,能够同时感知一生中的所有时刻。
对外星文字的理解,弥补了人类大脑的“缺陷”,突破了思维束缚。这篇小说中,作者认为人被时间的秩序束缚,可记忆是自由的。还有另一套诠释这个故事的角度,时间是幻觉,记忆是一个实体,人被大脑“缺陷”限制,束缚于记忆的秩序中。
假设我们有一个功能无限的大脑,能即时存储和调取信息,时间就消失了。我们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是一块硬盘上不同文件名的信息资料。6岁生日那天下午,天气燠热,我和小宝跑后山玩耍,右手中指被一只蚂蚱后腿扎出血,火辣辣的刺痛,知了在头顶的栎树上聒噪,空气是温热的黄瓜香……只需调出资料,永远不会遗忘。我们既活在过去,又活在未来,唯独没有现在。
我们毕竟没有被外星文字启发,虽然一生也在同一块硬盘上,只能通过一个固定的秩序读取资料,体验生活,这个秩序就是熵增——宇宙毁灭的过程。
熵增,热力学概念,一个从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总体不可逆,终点是宇宙灭亡。时间和文字一样,纯粹是人类的造物。文字用以记录,传达信息,时间的本质则是描述熵增。时间的终点必然是人类的灭亡,虽然没人知道人类什么时候灭亡,但一定在“热寂”(宇宙的死亡状态)前。所以,即便每个人对时间的想象不同,也可以对时间的本质达成共识,时钟就是共识的具体形式。
熵增总体不可逆,生命却是例外,它是熵减的过程,由无序向有序。我们相爱,亲热,生育,从混沌中创造新的生命,建立新的秩序。我们在迈向死亡的同时,也在对抗死亡。不仅是自己的死亡,也是宇宙的。
我的猫“鲍伊”有时间观念吗?它看见墙上的时钟,会感慨岁月如梭吗?以我对鲍伊的了解,它从不知时间为何物。猫的生活由吃喝拉撒睡等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组成。以猫的视角感知外界:看见前面有只老鼠,走过去,继续走,慢点,俯身,扑上去,咬住……它只是去行动,而不耗费时间去思索关于时间一类的虚幻事物。这样的一生无所谓虚度。其他生物同样无法想象时间,也无法通过时间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比人类短,更没有“去日苦多”的悲怆情怀。人是唯一需要用到时间的生物,这恰恰是我们许多悲苦的源头。
起先,我以为手机那头不是她本人,渐渐明白,那是她,但也不是——她的本质因为后来的存在改变了。她将我们一起的美好时光遗忘了许多,留下了的尽是不好的,对我当然变了。我对她也变了,我的记忆里尽是好的。
爱情也是幻觉,它存在于记忆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中,那些有趣的交谈,亲密的举动,伤心的误会……有的人怀旧,沉溺过去,被他人嘲笑。他们可能只是大脑功能更强大,普鲁斯特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挖掘记忆的天才,写出了不可思议的《追忆似水年华》。
或者,有的人只是执着地反复读取、拷贝、粘贴,记忆信息反复增强,不会丢失。他们的生活反复倒带,播放,活在“过去进行时”中。
如果她记得,一定会像从前一样爱我,但是她忘了,我和她说的那些记忆,对她只是幻觉。好在爱能改变时间,爱是扭转熵增的力量。给我点儿时间,让我赢回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