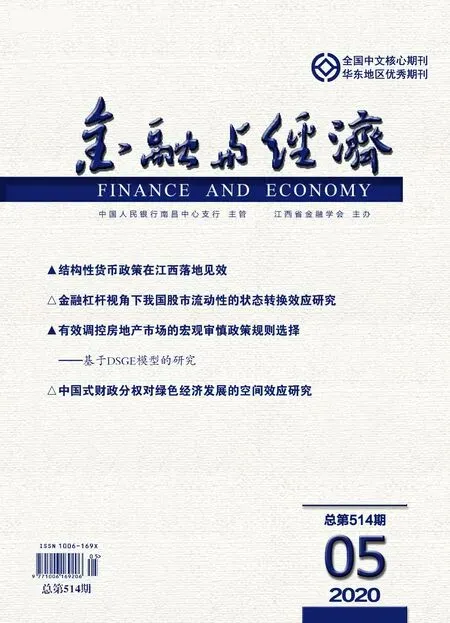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选择
——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
■ 杨 羽,谷 任
一、引言
自1998年实行房地产商品化政策以来,我国房地产业飞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从长期来看,房地产名义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1998年,我国房地产名义开发投资完成额为3580亿元,到2018年,房地产名义开发投资完成额达到120263.51亿元,是1998年的33.6倍。此外,在1998年至2018年之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除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下降外,一直呈持续上涨的趋势,到2018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达到6.65%,再考虑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建筑业,两者的产业增加值占2018年GDP的比值达到13.51%。若进一步考虑房地产业对其上下游产业的影响,2018年房地产业对GDP可能在20%以上。此外,考虑到:第一,我国人口一直持续上升,且国家开放二胎政策,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也会增加。第二,我国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截至2018年,城镇化率达59.58%,以后进入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而各地大学生落户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城市住房的需求。第三,许多收入较高的群体对房地产的需求不同于第一和第二点形成的刚需,他们对住房的舒适度有更高的要求,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形成了改善性住房需求。因此,我国的房地产业在总量上还有上升的空间。

图1 1998—201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
但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累积了不少问题。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得我国大部分家庭都无法一次性付款购买住房,家庭需要以所购住房为抵押品,并支付国家规定的最低房款比例(即购房首付比),向银行申请余下房款的方式购买住房,大量资金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到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25.75万亿元,相比于1998年的不足1000亿元竟增加了250余倍,涨幅相当惊人,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当年GDP的28.6%。这不仅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火热,也说明房地产市场发展占用了金融机构过多的信贷资源,抑制了其他行业发展。此外,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我国房价,居民购房成本越来越高,生活负担加重,为了获得住房,许多家庭不得不改变其消费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助推了房地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抑制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一些投机者也瞄准房地产恶意炒作,导致房价持续上涨,投资房地产的回报非常丰厚,投资者不愿投资其他行业,如此一来,我国经济增长也依赖于房地产发展。此外,房价畸高严重损害了刚需群体的利益,长期发展下去会不利于社会稳定。国际经验也表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可能以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而告终,会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如何制定政策以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不仅关乎国民经济增长,也关乎民生稳定,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都一直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都非常重视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出台了多项宏观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其中货币政策被讨论得最多,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但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货币政策受到了各界的严厉批判,宏观审慎政策受到极大关注,促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开始实施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我国虽然在近几年才提出这一思想,但多年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时所使用的第一和第二套房最低购房首付比、第三套及以上住房不允许贷款、商业用房购房首付比、以“商住两用房”名义申请贷款的购房首付比等政策,都是典型的房地产市场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至2002年,我国政府通过调低最低购房首付比来刺激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有效的促进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此阶段中我国房价节节攀升,高房价最终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心,政府陆续出台提高第一和第二套房首付比,商业用房购房首付比不低于50%,以“商住两用房”名义申请贷款的首付比不低于45%等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适度调控。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至2015年,国家为实现稳经济、稳房价的目标,反复调低或调高第一和第二套房首付比、停止发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虽有一定效果,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依然起着支柱性作用,但房地产业的萧条也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第四个阶段是2016年至今,“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词,政府紧扣房地产“房住不炒”的定位,结合“因城施策”思想和首付比工具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
现今,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进入“因城施策”的新阶段,但学术界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时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的具体设定形式鲜有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成为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审慎管理的关键和难点。笔者将通过构建多部门的DSGE模型对此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积极关注房地产市场,并对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少研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流分析方法,在这方面的运用也非常广泛。Aokiet al.(2004)认为,房地产作为借贷的抵押品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Iacoviello(2005)发现,住房抵押放大了外部冲击对房价和需求的影响。Iacoviello&Neri(2010)认为,住房需求、住房技术和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的住房投资和房价波动影响显著,而住房市场的波动又会进一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何青等(2015)发现,房地产偏好冲击和抵押率冲击是影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房地产市场和借贷约束间相互影响,加大了各种经济冲击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表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放大宏观经济的波动,但是学术界对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房地产市场作出反应却一直存在争议。
Iacoviello(2005)认为,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作出反应对于稳定产出和通胀并没有明显的效果。Chen et al.(2012)发现,使用货币政策来稳定资产价格通胀需要在波动性和经济活动水平之间权衡。Gelain et al.(2013)研究表明,虽然利率对房价增长或信贷增长作出响应可以稳定一些变量,但它会显著放大其他因素的波动性,尤其是通货膨胀。Sun et al.(2014)认为最优利率规则应该对房价通胀作出反应。Notarpietro et al.(2015)认为,当房地产价格变动由住房需求或金融冲击引起时,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作出响应。肖争艳和彭博(2011)发现,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的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胀持续上升,以及产出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值。王云清等(2013)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是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来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应温和地盯住房价波动。侯成琪和龚六堂(2014)认为,盯住房价的货币政策能显著降低房价波动,进而降低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
在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爆发次贷危机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货币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对危机爆发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反思,人们意识到:仅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经济稳定,特别是当经济失衡是由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诱发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是更好的政策选择。而在此次危机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欧盟等都更加重视房地产市场管理,纷纷引入宏观审慎政策而不是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房地产市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贷款价值比(LTV,在数值上LTV=1-首付比)被各国频繁使用,我国政府也频频变动购房首付比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学术界逐渐加大对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研究,并且研究大多支持了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Bruneau et al.(2016)认为反周期LTV比率,特别是盯住房价的宏观审慎政策,比对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更好地稳定住房市场。黄志刚和许伟(2017)发现,相对于仅实施货币政策的情况,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可以使住房市场波动性下降,而产出波动性和福利损失并不显著增加。张婧屹和李建强(2018)构建带有房地产生产部门的DSGE模型,探讨了不同外生冲击下金融杠杆的最优规则及社会福利效应。孟宪春等(2018)认为,盯住广义信贷偏离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显著降低社会福利损失。
这些研究为探讨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有限,且对于不同经济条件下,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具体设定形式的研究更少。鉴于此,笔者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同时引入受信贷约束的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将LTV动态化,并借助福利损失函数,探讨不同外生冲击下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的选择问题。这一研究不仅能填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而且对于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DSGE模型的描述
(一)家庭
参考Iacoviello(2005),将家庭细分为耐心家庭和非耐心家庭,耐心家庭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非耐心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只能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购房。家庭主要通过决策当期消费Ci,t、住房需求Hi,t、劳动供给 Ni,t来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

其中,i∈{1,2}分别代表耐心家庭和非耐心家庭,η为劳动供给弹性的逆;βi表示家庭的贴现因子,且β1>β2,jt为住房偏好冲击。
1.耐心家庭
耐心家庭累积房地产 H1,t用于居住,将 B1,t用于储蓄,并从零售商取得实际净利润。耐心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Ih,lt=H1,t-(1-δh)H1,t-1、Rt-1B1,t-1/πt、W1,t和 Rt分别为耐心家庭t期的新增住房投资、利息收入、实际工资、存款名义利率,δh和Qt分别为房地产折旧率和实际房价。
2.非耐心家庭
非耐心家庭的预算约束和借贷约束为:

其中,Ih,2t=H2,t-(1-δh)H2,t-1、W2,t、B2,t、、bt和 m2,t分别为非耐心家庭t期的新增住房投资、实际工资、实际借款额、名义贷款利率、信贷冲击和贷款价值比,1-m2,t是非耐心家庭购房要支付的最低首付比,同时也是银行在非耐心家庭违约时处置抵押品的成本。非耐心家庭的借贷约束机制具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m2,t的大小度量了银行能提供给非耐心家庭有限信贷的程度,m2,t越大,可实现的杠杆越高。当外生冲击引起房价波动时,房价波动通过借贷约束机制放大其他变量的波动,这些变量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对房价产生影响,从理论上分析,如果监管部门对非耐心家庭的贷款价值比进行逆周期管理,可以降低房价波动通过借贷约束机制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二)企业与零售商
1.企业家
企业家生产中间产品,其生产函数为:

其中,At为技术水平,Kt-1和He,t-1、N1,t和 N2,t分别为企业家投入的资本和房地产、雇佣的耐心家庭和非耐心家庭的劳动,μ和v分别为资本和房地产的产出弹性,α为耐心家庭的比例。借鉴Iacoviello(2005)和Iacoviello&Neri(2010)的设定,假定两类家庭的劳动完全互补。
企业家在预算约束和借贷约束下通过决策当期消费Ce,t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


其中,Be,t、Ie,t=He,t-(1-δh)He,t-1、It=Kt-(1-δk)Kt-1、分别为企业家的实际借款额,房地产投资、资本投资、投资资本的调整成本和贷款价值比。企业家的借贷约束也具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实践中,监管部门对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的调控往往是有区别的。
2.零售商
参照Bernanke et al.(1998)的设置,用z∈(0,1)来度量零售商。零售商从企业家购买中间产品,并将中间品转化为最终品,再以一定的价格加成出售Yt(z)。参照Calvo(1983),假定每期有(1-θ)的零售商能重新制定价格,则:

结合以上两式推导,并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可得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其中,k=(1-θ)(1-β1θ)/θ,ût为成本冲击。
(三)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以存款利率Rt吸收耐心家庭的储蓄B1,t,以抵押贷款利率贷给非耐心家庭 B2,t和企业家 Be,t,信贷总量为 Lt=B2,t+Be,t。商业银行需要将 eB1,t比例的存款上缴中央银行,e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四)房地产生产商
借 鉴 Christensen et al.(2016)和 Mendicino&Punzi(2014),假定房地产生产商每期从零售商购买最终产品,并与现有房地产存量结合生产新的已安装的房地产,生产过程受调整成本约束。房地产生产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房地产总存量为 Ht=H1,t+H2,t+He,t,其遵循如下运动规则:

(五)宏观政策当局
1.货币政策
假定货币政策制定遵循如下泰勒规则:

其中,ρr、aπ和aY分别表示政策利率对各变量的反映系数,êr,t是一个iid的白噪声冲击。
2.宏观审慎政策
LTV是一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广泛应用于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并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中将LTV动态化,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下对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区别调控的思想,参照Angelini et al.(2012)和孟宪春等(2018),设定了三种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
第一种宏观审慎政策是非耐心家庭LTV盯住家庭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企业家LTV盯住企业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其对数线性化形式设定为:

第二种宏观审慎政策是非耐心家庭LTV盯住家庭房地产信贷的信贷增速,企业家LTV盯住企业房地产信贷的信贷增速,其对数线性化形式设定为:

第三种宏观审慎政策是非耐心家庭LTV和企业家LTV分别盯住实际房价稳态偏离,其对数线性化形式设定为:


其中,ρm2和ρme分别为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LTV的平滑系数,Xm2和Xme分别为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LTV对盯住变量的反应系数。
(六)市场均衡
当市场达到均衡时,所有市场的最优化条件都得到满足,相应的资源约束为:

(七)外生冲击
笔者引入了5种外生冲击,除货币政策冲击外,其他冲击均服从AR(1)过程:

其中,x分别是j、A、b和u,ρx表示AR(1)冲击的一阶自相关系数,êx,t是均值为0,标准差为σx的白噪声过程。
四、模型参数确定
(一)相关参数的校准
文中部分参数的具体校准值如表1所示①限于篇幅,这里不给出具体参数取值依据,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后文收敛性检验的多变量诊断图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此类似。。

表1 参数校准值

表2 先验分布与贝叶斯估计结果
(二)贝叶斯估计
选取我国2005—2018年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银行间7天期的同业拆借利率、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的季度数据。在将数据转换为所需实际数据后,进行季节调整、取对数和去趋势处理得到贝叶斯估计中使用的数据。贝叶斯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收敛性检验的多变量诊断图,度量指标均值、方差和三阶矩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逐渐趋向收敛,表明参数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效果分析
(一)福利损失函数分析
传统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仅考虑通胀和产出缺口变动,未考虑与金融稳定相关的因素。Angelini et al.(2012)认为,宏观审慎政策应以金融稳定为核心目标,同时兼顾抑制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因此,为了确定能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参考孟宪春等(2018),在福利损失函数中加入实际房价的波动,具体形式为:

系数kπ、kY和kQ的取值也与孟宪春等(2018)一致,分别为1、1和0.1。
接下来,以上文的DSGE模型为约束条件最小化福利损失函数,计算不同外生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反应函数中各参数的最优值及对应的福利损失值。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参数与福利损失

续表3
由表3可知:一是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盯住相同变量的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参数值和对应的福利改善情况各不相同,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与冲击来源相关。同一外生冲击下,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带来的福利改善不同,选择合适的宏观审慎政策才能显著降低福利损失。二是在住房偏好和技术冲击下,相比于体制1,体制2和体制3并不带来明显的福利改善,而体制4福利改善情况较显著。住房偏好冲击下,体制2和体制3会增加通胀波动性,体制4下通胀波动性减小。技术冲击下,体制4通胀波动性高于体制2和体制3,但与体制1相比,通胀波动性并没有增加。三是在信贷冲击下,体制2和体制3能非常显著的降低福利损失,且体制2效果更佳,但对于体制4,在Xm2和Xme不小于0的限制下,最优规则为不对房价作出响应(下文将进行解释)。四是在成本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能带来福利改善,体制4福利改善最明显。另外,体制2和体制3的通胀波动性高于体制1,体制4下通胀波动性减小。比较4种体制下房价的波动性发现,体制4略高于体制2,但仍显著低于体制1,这里使房价整体波动性最小的宏观审慎政策并不能显著降低福利损失。五是在货币政策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降低了福利损失,但房价的波动性均高于体制1,且福利损失明显降低的体制2和体制3通胀和房价的波动性也最高。
(二)脉冲响应分析
1.住房偏好冲击
如图2,正的住房偏好冲击增加了社会对房地产的需求,导致房价上涨,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推动企业扩大生产,经济增长表现过热,促使央行提高利率。企业扩大生产的需求使资本和生产性房地产投资增加。此外,房价上涨增加了房地产的抵押品价值,借贷约束放松,信贷额扩张,但抵押贷款购房所需支付的房款最低首付比也增加,非耐心家庭增加当期住房投资的同时减少普通商品消费。耐心家庭的住房偏好虽然也增加,但耐心家庭是全款买房的群体,在房价及存款利率都上升的情况下,基于终生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增加当期储蓄,减少消费及房地产投资。家庭部门消费减少使得物价水平下降。
由图2发现,体制1、体制2和体制3的脉冲响应图表现基本一致,体制2和体制3下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仅对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总投资起到非常轻微的平滑作用,对产出的平滑作用也不明显,还增加了通胀波动性,不能明显改善福利。因此,体制2和体制3下的宏观审慎政策都不是经济体受到正的住房偏好冲击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最优政策。相比之下,体制4的产出、通胀、房地产价格、两类家庭的消费、利率、资本投资、房地产总投资的波动性都更小,并更快回到稳态附近,结合表3还发现,相较于体制1,体制4的福利损失明显降低。随着冲击消失,体制4的通胀更低,产出、总消费和资本投资水平更高。这表明体制4下宏观政策当局盯住房地产价格对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的贷款价值比进行逆周期管理能更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价格,减弱房价上涨通过信贷约束机制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即体制4的政策为住房偏好冲击下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最优规则。

图2 不同体制下住房偏好冲击脉冲响应图
2.技术冲击

图3 不同体制下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如图3,技术冲击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使得产出增加,物价和利率水平下降。利率下降促使两类家庭都增加当期消费,耐心家庭同时还会增加当期住房投资,并推动房价上涨,进而增加了非耐心家庭和企业的购房成本。非耐心家庭会减少房地产投资,企业减少消费、资本投资及生产性房地产投资,进而导致企业缩减生产规模。从图2还发现,技术冲击下房价上涨幅度明显高于产出。技术冲引起的房价上涨显著增加了非耐心家庭和企业的购房成本,房价上涨通过借贷约束机制的金融加速器作用,使得企业缩减生产规模,且随着冲击消失,产出逐渐下降到稳态以下。
由图3可知,体制2和体制3的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总投资几乎不能起到平滑作用,体制4的宏观审慎政策在前4期会导致房地产价格波动性加剧,但此后房地产价格波动性低于其他几种体制,且更快回到稳态。对于耐心家庭消费、利率和资本投资,与体制1相比,体制2和体制3下这些变量的波动性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体制4下,在经历4~8期较高的波动性后,变量的波动幅度会低于其他体制,并更快回到稳态附近。而对于产出、非耐心家庭消费、总消费,体制4下这些变量的波动性明显较低,也更快回到稳态附近,在体制2和体制3下,这些变量的波动性与体制1相比没有明显差异。另外,由于体制4下产出波动性显著降低,使得体制4的福利损失也明显更低,进一步比较发现,体制4下产出在长期中更高,其他几种体制则低于稳态。因此,体制4的宏观审慎政策是技术冲击下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最优规则。
3.信贷冲击
如图4,扩张性的信贷冲击使非耐心家庭和企业获得更多抵押贷款,购房更容易,因此他们增加持有房地产。信贷扩张使得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增加消费,带动总消费增加,企业增加资本投资,扩大生产,同时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这两者促使中央银行提高利率,进而导致耐心家庭增加当期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并减少持有房地产,非耐心家庭减少的房地产超过了非耐心家庭和企业需求的增加,因此房价一开始下降了,经济中房地产总投资减少。
由图4知,体制2和体制3下几乎所有变量的波动性都明显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于体制2和体制3的宏观审慎政策分别盯住信贷稳态偏离和信贷增速,当信贷冲击引起信贷快速膨胀时,宏观政策当局立即降低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的LTV,从而有效抑制了由于信贷扩张带来的经济中各宏观变量的大幅波动。据表3和图3发现,体制2的福利损失更小,随着冲击消失,体制2的宏观变量更快回到稳态附近,且最终产出、总消费和资本投资更高,通胀更低。因此,体制2的宏观审慎政策为信贷冲击下的最优规则。

图4 不同体制下信贷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在表3中,信贷冲击下体制4的最优规则是不响应房价:信贷冲击导致非耐心家庭和企业信贷额增加,并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体制4的LTV规则如果对房价做出响应会提高LTV,会使非耐心家庭和企业的信贷额进一步增加,加剧经济波动。
4.成本冲击

图5 不同体制下成本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如图5,成本冲击推高了物价水平,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减少资本投资,缩减生产规模。物价水平的上升使非耐心家庭和企业的借贷约束也更宽松,债务实际价值下降,这使得他们增加持有房地产,减少消费。企业和非耐心家庭增加房地产投资的行为使房地产价格上升了。此外,成本冲击使央行提高了利率水平,但利率增加的幅度小于物价水平,面对经济中物价水平、利率以及房价的上升,基于终生效用最大化原则,耐心家庭选择增加当期消费,减少持有房地产。
由图5可知,体制1、体制2和体制3下各主要宏观变量的波动情况比较一致,但体制4则表现出较大差异。结合表3,与体制1相比,体制2的房价波动性最小,但由于轻微增加了通胀波动性,对产出的平滑作用也不明显,因此福利改善不显著。体制3下几乎所有变量的波动性都没有明显降低,因而福利改善也不显著。体制4下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波动性略大于体制2,但由于产出和通胀波动性明显降低,社会福利显著改善。从表3来看,体制2和体制4下房价标准差没有明显差别,但图5中房价的脉冲响应图差异明显,体制2下房地产价格最终不能回到稳态,体制4下房价短期内波动更加剧烈,但在约20期后,房价较快回到稳态。耐心家庭消费和房地产总投资也表现出与房地产价格相似的特点。此外,体制4下总消费和资本投资的波动性也更小。
因此,虽然体制2下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总投资的整体波动性更小,但考虑到体制4能较明显的降低大多数变量的波动性,明显降低福利损失,且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总投资在一定时期较明显的波动后回到稳态,体制2的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效果并不理想,体制4的宏观审慎政策才是成本冲击下的最优政策规则。
5.货币政策冲击
如图6,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冲击提高了利率水平,增加了非耐心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信贷规模下降,两者减少持有房地产,并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缩小,产出下降,进一步使得资本投资也减少,社会总消费下降,物价水平降低。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减少购房的行为还使得社会房地产总投资减少,房价下跌,耐心家庭在低房价时增加房地产投资,并推动房价和房地产总投资逐渐上升。这种房价的上涨通过信贷约束机制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最终使得其他变量向稳态水平靠拢。

图6 不同体制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结合表3和图6可知,体制2、体制3和体制4下房价波动性均大于体制1,体制2下房地产总投资的整体波动性略小于体制1。进一步分析图5发现,体制4对大多数宏观变量都没有平滑作用,体制2和体制3的宏观审慎政策使13期之前房地产价格波动更明显,在13~30期房地产价格波动减缓,且体制2减缓更明显,但整体上房价波动性仍增加了。此外,体制2和体制3下产出、总消费、两类家庭持有的房地产和资本投资的波动性明显减弱,且体制2表现更优,同时还因为产出波动性显著减弱,体制2的福利损失最低。这些分析表明,体制2的宏观审慎政策对于稳定房价的效果并不好,还会增加通胀波动性,但能显著降低产出波动性,明显降低福利损失。这表明,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降低社会福利损失与稳定房地产市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冲击使产出和房价都下降了,且产出下降幅度更大,为改善福利,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要发挥房价波动通过信贷约束机制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来影响其他变量,使产出向稳态靠近,因而房价整体波动变大。进一步分析图6发现,体制2下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产出波动性的作用仅表现在前8期,此后随着房价波动性的逐渐减弱,产出低于其他几种体制,且低于稳态水平,通胀波动性也增加。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笔者选择了4个可能影响结论的参数进行稳健性分析:β2、β、ψk和ψh。参考已有研究的取值,设置了β2=0.96,β=0.975,ψk=ψh=2.5和β2=0.97,β=0.985,ψk=ψh=5的两组值,重复上文的计算过程,模拟得出不同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图。根据所求结果分析得到的结论并没有明显改变,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DSGE模型研究在面对不同外生冲击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的选择问题。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变量和最优政策反应参数与冲击来源相关,选择合适的宏观审慎政策才能有效降低福利损失。
第二,住房偏好、技术和成本冲击下非耐心家庭和企业家LTV分别盯住房地产价格稳态偏离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显著降低福利损失,且在长期中产出更高,住房偏好和成本冲击下能降低通胀波动性,技术冲击下最优宏观审慎政策会轻微增加通胀波动性。成本冲击下这种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不能使房价整体波动性最小,但由于能较显著的降低产出和通胀波动性,降低福利损失,房价整体波动性与最低情况相比仅轻微增加,且在长期中房价和房地产投资都能回到稳态,这使得非耐心家庭LTV盯住家庭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企业家LTV盯住企业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的宏观审慎政策没有明显优势。
第三,信贷冲击下非耐心家庭LTV盯住家庭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企业家LTV盯住企业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显著降低福利损失,且产出在长期中更高,通胀和房价偏离稳态的程度也更小。
第四,货币政策冲击下笔者设定的三种宏观审慎政策均不能抑制房价波动,但非耐心家庭LTV盯住家庭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企业家LTV盯住企业房地产信贷稳态偏离的宏观审慎政策能较显著地改善福利。这可能是因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使产出和房价都下降了,为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要发挥房价波动通过信贷约束机制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来影响其他变量,使产出向稳态靠近。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的对策建议有以下几点:第一,面对不同外生冲击,宏观政策当局应选择适当的盯住变量并调整反应强度,更好地调控房地产市场,并尽可能避免增加通胀波动性,稳定产出,降低福利损失。第二,货币政策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面临降低房价波动性与降低福利损失的不一致,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发挥房价波动通过信贷约束机制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显著降低了短期中产出的波动,改善了社会福利。但在更长期中,随着房价波动性减弱,产出负向偏离稳态的程度更大,通胀更高。并且,现实经济更为复杂,当局在实际制定政策时考虑的问题也更多,因此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财政政策、保障房分配和房产税等政策,也许能更有效地调控房地产市场,实现经济稳定。第三,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前处在“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新阶段,中央近年一直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运用文中结论时也不能脱离此背景。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力度应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对于初次购房和购买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的购房者应适当放松调控力度,合理引导市场参与者对房地产的需求,有效满足房地产的刚需,抑制投机性需求,实现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