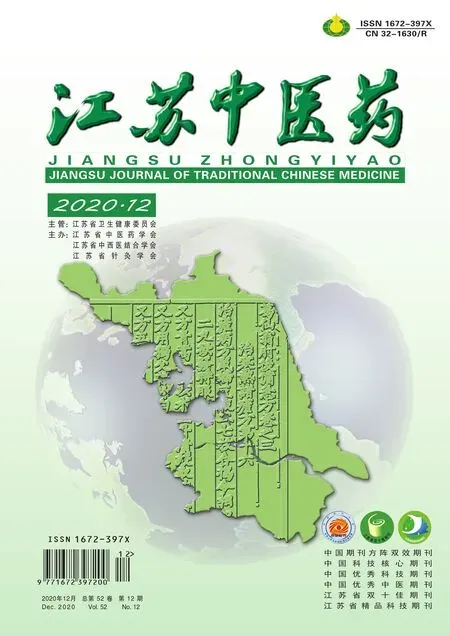章朱学派治疗水肿病用药经验探赜
高国栋 朱 泓 孙 伟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京210029)
水肿是指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水液在组织间隙潴留的一种临床表现,按照病因主要包括心源性水肿、肾源性水肿、肝源性水肿、营养不良性水肿、黏液性水肿、特发性水肿、药源性水肿、老年性水肿等。近代中医师承历史上,由章次公、朱良春两位大师以及众多弟子形成了章朱学派[1]。笔者有幸跟随朱良春先生入门弟子孙伟教授学习,并与朱良春先生之孙女朱泓医师共事,对章朱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并研究相关文献,兹将章朱学派治疗水肿病用药经验探析如下。
1 利湿消肿,分清缓急
水肿为病,有虚有实,虽有阳水多实,阴水多虚之说,然临床过程中虚实夹杂方为水肿病之常态,当明辨何为主要矛盾,何为次要矛盾,然无论如何,利水消肿总是第一要务。
章次公先生临床上喜用葫芦瓢、冬葵子、泽泻治疗各类水肿[2]302。葫芦瓢甘平,入肺肾二经,功善利水消肿,《神农本草经》谓之“主治大水,面目,四肢浮肿”,用药时一般用量宜大,常用24~30 g;冬葵子甘凉,归大小肠及膀胱经,善清热利尿,《本草经集注》谓之“主五脏六腑,寒热羸瘦,五癃,利小便”,《肘后备急方》更以此药单用治疗关格胀满,小大不通;泽泻甘淡而寒,入肾与膀胱经,利水渗湿能力尤强,并能泻热化浊,《雷公炮制药性解》称其“治小便淋涩之仙药,疗水肿病胀满之仙丹”。此三者行水力强,且药性不甚猛烈,常配伍统治诸水。若水湿泛滥,一身皆肿,小便不利,大便不通则加大黄攻下以逐水,如再不效,可取舟车丸或十枣汤之意攻逐水饮,先伏其所主,再予其他方药善后。
朱良春先生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在治疗急性肾炎水肿时,尤喜益母草,益母草辛苦微寒,归心、肝、膀胱经,为治疗妇科疾病的要药。朱良春先生在临床中发现益母草有清肝降逆、活血利水而不伤正的作用,若取其活血利水作用治疗水肿,用量需大,用至60~120 g方见良效[3]11;对于水肿势重难消、小便短少者,朱良春先生常喜用蟋蟀、蝼蛄、琥珀、沉香制成胶囊,于汤剂外另服[3]13。蝼蛄性寒,逐水力强,《玉揪药解》谓之“利水消脓,开癃除淋”,注意炮制时去头、足、翼,否则无效;蟋蟀性温,作用稍缓。蟋蟀、蝼蛄虽有寒温、强弱之别,朱老认为二者合用利水之力更佳[4]202。
2 重视阳气,治病求本
水与津液同源,在其位周流不息则为津液,停则为邪,《灵枢·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可见水液的运化尤其依赖肺、脾、肾三脏之气化,肺脾肾三脏阳气虚损,则易气化不利而水湿之邪成。而脏腑之“气化”主要是指阳气的功能,即所谓“阳化气”[5]。故而水肿,尤其是阴水,阳气不足往往是其重要内在因素。
章次公先生治疗水肿时尤重肾阳肾气,在临床时常用真武汤、肾气丸类方。然章次公先生用附子治疗水肿,常用小剂量制附子(多在6~9 g之间),而不宜大剂量生附子[2]302。究其原因,因肾性水肿并非四逆汤证之阳气衰微,寒邪大盛,急需大剂量生附子回阳救逆,乃是取其温振肾阳肾气之用,故不需要使用生附子,且常规剂量使用即可[6]。
朱良春先生在继承章次公先生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更重视脾肾气虚为其发病的内因[7]394。临床上重视黄芪的使用,黄芪甘温,归脾、肺经,功善补气升阳、益卫固表、利水消肿,为补气要药。近年亦有学者认为黄芪亦有补肾的作用[8]。在治疗肾炎水肿时常需大量(30~60 g),常配伍咸寒通络利水之地龙,使补通并行,寒温并用。又常用黄芪配附子、淫羊藿,并认为除舌质红绛、湿热炽盛者外均应选为主药[9]。《备急千金要方》记载“附子……畏黄芪”,有研究证实黄芪可以减轻附子对心脏的毒性,并与黄芪的剂量呈正相关,故而此配伍温振脾肾阳气的同时又可减轻附子的毒性,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10]。
3 活血化瘀,不可忽视
活血化瘀作为中医治疗水肿病的方法之一,可追溯至《黄帝内经》时期,“去宛陈莝”即活血化瘀之意。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血不利则为水”的观点,指出血和水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血证论》提出“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中医认为,津液中的精微部分在心的作用下化赤为血,故而血与津液实则同出一源,而水饮之邪则是津液代谢不利的产物,可见血瘀与水肿关系密切。
章次公先生在治疗肝硬化水肿时常用活血化瘀类药物,如地鳖虫、桃仁、丹皮、牛膝之类,常能收到满意疗效。朱良春先生在肾性水肿治疗中重视活血化瘀法的应用。研究证实,活血化瘀法在改善蛋白尿、延缓肾功能进展方面有效,并且有助于水肿消退。泽兰、茜草、益母草均为活血利水之品,常被辨证用于各类肾炎水肿。穿山龙亦是朱良春先生发现的治肾良药,其苦而温,归肝、肾、肺经,功善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清肺化痰,原并未记载治疗肾炎水肿之效果,朱良春先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其配伍治疗慢性肾炎和肾功能不全有较好的疗效,但用量30~60 g方能收到良效,小于20 g几乎无效[4]250。对于病程日久,邪入孙络者,此非一般活血化瘀之品能及,需用虫类药物进行治疗,他临床喜用水蛭,《神农本草经》谓之“咸平,主逐恶血,瘀血,月闭。颇血瘕积聚”。现代亦有研究证明水蛭有抗凝、抗炎、抗纤维化及保护细胞作用[11],亦有报道水蛭制剂有保护肾功能的作用[12]。
4 单方验方,亦有大用
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名医如繁星璀璨,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积累了许多经典名方,民间的铃医串雅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良春先生发现了许多单方验方流于市井之中,对某些疾病或症状可有奇效。张志远先生年轻时亦曾于铃医处习得许多单方验方,临床疗效颇佳,如秘方二味汤治疗吐血、三回头治气郁证等[13]。
章次公先生临床中对水肿势大或难消者亦重视民间单方验方的应用。如用杨氏家藏方治疗浮肿喘闷,方用大冬瓜一枚切盖去瓤,再用赤小豆填满,纸筋泥封晒干,再用糯糠入冬瓜内煨,火尽取出切片,同豆焙干为末,水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冬瓜子汤送七十丸,日三次,以小便利为度。其他又如镇坎散、化龙丹、遇仙丹等数十首,皆辨证用于临床[2]90。
朱良春先生临床中亦用单方验方,并且在章次公先生的基础上常有创见。比如治疗肾炎水肿小便难下,喜用蝼蛄、蟋蟀、琥珀、沉香制成胶囊配合汤剂服用。此方为章次公先生治疗轻度肝硬化腹水时所用之土狗散变化而来,原方蝼蛄七枚、将军干(即蟋蟀)4枚焙干研为细末,分三次服[2]91。因其利水而对正气损伤较小,朱良春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常用蟋蟀、蝼蛄、琥珀各2 g,沉香1.2 g,取干品共研细末,为1日量,分2次服用,有利尿、消胀之功[3]13。琥珀甘平无毒,归心、肝、膀胱经,《本草经集注》谓之“消瘀血,通五淋”;沉香辛苦温,归脾、胃、肾经,可行气、止痛、降逆调中、温肾纳气,《本草经解》谓之疗风水毒肿,去恶气。四药融温肾、行气、化瘀、利尿为一炉,以助消水邪。当然,在使用单方验方时因其来源颇多,出方之人水平高低不一,一定要注意考证其来源,查其组方是否合乎医理,辨证选用,切忌人云亦云。
5 日常调养,贵在坚持
水肿之病,尤其阴水,往往病程较长,虚实夹杂,经治疗好转后必须重视日常调养,以巩固疗效。章、朱二位先生都主张水肿病人应当限盐,这与现代医学的认识一致。病情稳定时可长期服用丸药以巩固疗效,偏阴虚者可用六味地黄丸,偏阳虚可用肾气丸,如经济条件允许可用虫草煎汤或制成胶囊服用,取其滋肾保肺,可提高免疫力,减轻体内炎症反应,现用人工养殖虫草代替亦可。饮食方面宜清淡,避免过咸及过度辛辣;生活中要注意动静结合,既不可一味卧床静养,也不可过度运动劳累,要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户外活动,以增强抵抗力,避免感冒。朱良春先生提倡水肿患者常揉太溪穴,太溪穴为足少阴肾经之原穴,有补益脾肾之效,可以改善疲劳、腰酸、水肿等症状。按揉1日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以自觉酸胀为度,不可用力过猛[7]395。
章朱学派治疗水肿效果显著,其治疗多从益气、温阳、利湿、活血入手,且于药量上颇多讲究,其宝贵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医临床仍有指导意义。对比章、朱两位先生的用药我们亦不难发现,朱良春先生在继承章次公先生经验的同时常常又结合自身临证体会与认识进一步发展改进,这种“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精神正是章朱学派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