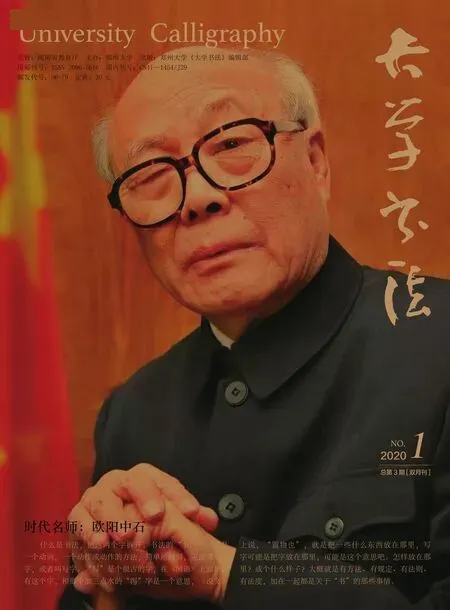苏轼《致季常尺牍》中人物关系及社会背景刍议
⊙ 沈速
苏轼的书法作品《致季常尺牍》(图1),又名《一夜帖》,是苏轼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封日常书信。据考证,这件尺牍作于苏轼被贬谪黄州之时。黄州古时属于巴楚地域,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很多诗词、书法作品及来往书信墨迹。苏轼著名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帖》就作于此地。
关于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背景,国内已有不少考证及论著。这件作品从艺术风格上,有朱以撒先生的《笔调从容,坦荡平易—苏轼〈致季常尺牍〉赏析》。朱以撒先生在文中以扁势、斜势、竖式三种笔式分析该帖的字势特点。另外,又从笔法上分析了苏轼此作用笔清瘦坚挺,不同于《游虎跑泉诗帖》《致若虚总管尺牍》等苏书肉多伤骨的风格特征。文中援引清代书家吴其贞“惟此肥不露肉,人莫能及”之论,认为该作乃苏轼简札中清瘦坚挺之代表。整体风格似清风徐来,绿柳婆娑,有微风拂面之感。
从苏轼交游信札来看,有江苏科技大学喻世华先生2012年发表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一文。喻世华先生结合《宋史》中关于苏轼交游的记载,详细考证了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关系。另有关于苏轼往来信札的文献研究,如暨南大学硕士杨银娥的《苏轼书信研究》、延边大学硕士马明玉的《苏轼贬谪期间书信研究》,分别从书法文献的角度及书法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苏轼书信进行了梳理与研究。文中对苏轼与陈季常的信札往来都有提及。本文从苏轼与陈季常信札的内容,来分析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的交游、人物关系以及苏轼的人设。
苏轼作《致季常尺牍》的时间,应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据延边大学马明玉硕士论文《苏轼贬谪期间书信研究》所述,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和朋友共有311封书信往来,其中,与陈季常十六首中第十一至第十四首往来时间都在这一时期。
通过对这件尺牍的审读,我们发现在这封信里,一共提到了四个人物:苏轼、陈季常、王君和曹光州。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件尺牍中人物的关系。“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关于“黄居寀龙”,一说“黄居寀龙”是一幅画,另一说黄居寀所作“龙”为一幅画。在这里,笔者认为“龙”为一幅画比较准确。“黄居寀(933-993),字伯鸾,成都(今属四川)人,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画家黄筌的第三个儿子。擅长画花竹禽鸟,勾线精致,用笔工稳劲健,设色喜好华丽的重彩,他的花鸟画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所绘怪石类山水画甚至超过他的父亲黄筌,和他的父亲同在后蜀为官,任翰林待诏。”[1]黄居寀曾经和他父亲黄筌合作绘制了大量的殿廷壁画以及宫闱屏幛。《宣和画谱》和《图画见闻志》载黄居寀为黄筌的季子,《益州名画录》则说他为黄筌的次子[2]。其兄居实、居宝都有画名,但英年早逝,名声不及居寀大。
到了北宋时期,因为宋太宗非常看重他,授黄居寀为光禄丞,并委以重任,让他搜访历代名画,鉴定后分类列目,在当时颇有影响。为适合宫廷绘画风格的需要,黄居寀画格富丽浓艳,并在宫廷画院居主持地位,引领了当时宫廷画风的方向。当时想要加入宫廷画院的画师,纷纷效仿黄氏画风。淳化四年(993)黄居寀61岁,奉命出使成都府,在圣兴寺时,绘制了《龙水》《天台山》等壁画。在宋代《宣和画谱》的著录中,黄居寀的作品有《春山图》《桃花山鹧图》等300余件。传世较为经典的作品有《竹石锦鸠图》册页、《山鹧棘雀图》轴,后一图上方有宋徽宗赵佶御题“黄居寀山鹧棘雀图”8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居寀,按出生年月考证,应早于苏轼。所以,这位在宫廷处于引领地位的画家,在苏轼那个年代是已经过世了的。因此,他的画作也极为珍贵。从苏轼在信中所提看,应该也是极为珍视的。苏轼找了一夜黄居寀《龙》图,突然想起来是被曹光州借走摹拓去了。曹光州是信中出现的第二个人物。按苏轼所提的人物关系来看,苏轼和曹光州应该是关系较为不错的朋友,不然也不会将半个月前自己收藏的名画借给他去摹拓,而且答应一个多月后才还。而“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这里两句话出现了两个人物:王君和季常。由于担心王君怀疑自己翻悔,才仔细和季常说清楚。这里“细说与”,是倒装句,是与子细说的意思。这句话信息量很大,王君提出向苏轼借画,苏轼想必是曾经答应了的,但是真到了借画的时候,苏轼翻箱倒柜翻了一晚上,突然想起来被曹光州借走了,还要一个多月才还回来。但苏轼并没有直接和王君解释,而是写信给陈季常细说此事,并且说只要曹光州把画还回来,马上就会借给王君。可见苏轼和王君并不熟,而之前答应借画,笔者在这里推测也是苏轼口头承诺,或者是酒后失言,并不是真想将自己珍藏的名画借给并不熟悉的王君。

图1 苏轼《致季常尺牍》 纸本 行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曹光州是谁?据李之亮先生《宋代郡守通考》载,曹光州,即曹九章,字演甫,时为光州太守。《苏轼文集》卷七三《朱元经炉药》:“故人曹九章适为光守。”同书卷一七二《记神清洞事》:“曹焕游篙下中,途遇道士,盘礴石上,揖曰:‘汝非苏辙之婿曹焕乎?”[3]苏辙《架城集》卷二三《光州开元寺重修大殿记》:“朝散大夫、彭城曹公作守,复新于元丰癸亥。”元丰癸亥即元丰六年(1083),知是年前曹九章即为光州太守,与苏轼元丰五年(1082)赠诗相吻合。
东坡《吊李台卿并序》里称“曹光州演甫”。本集杂记《朱元经炉药》中载:“故人曹九章,适为光守。”其子涣为苏辙婿。《乐城集》有《祭亲家曹演甫文》,叙述“东坡在黄州,因与结姻之事,而作合者,则李公择也。光、黄接壤,九章正守光州,故往还密熟。”[4]可见苏轼和曹光州是相当熟的。因此,借画摹拓之说是站得住的。
“王君”者,疑是秀才王齐万。东坡元丰三年(1080)有《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一诗,王文诰《苏诗总案》:“王齐万,字子辩,嘉州犍为人,乃齐愈字文甫之弟。”东坡《南行集》中亦有《犍为王氏书楼》一诗,乃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氏父子还朝沿长江南行之记录。犍为王氏世有藏书之癖,“塞江流柿起书楼”,使东坡二十余年后记忆犹新。陈季常亦是蜀人,与王齐万自然有同乡之谊,且寓居一地,他受“王君”之托向东坡催借黄居寀《龙》图,而此《龙》图又为曹光州借去未还,东坡怕王齐万误会“疑是翻悔”不愿借与,便由此札拜托陈季常代为解释,“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为了聊申忱意,还“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为了寻画,翻腾了“一夜”,还怕别人误会,搭上一饼团茶先行送去,由此处看,似乎颇显东坡交友之诚。王君齐万也有藏书之好,所以向东坡借画或为“摹搦”收藏,亦属合理。笔者在此不太赞同苏轼与王君的借画结交之说。且这一王君,是否就是秀才王齐万也犹未可知。苏轼寄礼物给友人也是他的一贯做法,在和陈季常的往来书信中,常有提及二人互寄礼物的信息。
团茶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制作工艺上经过了最初的加香料到后来不加香料的历史演变过程。团茶须煎饮之。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笔者认为,这里苏轼用当时仅供宫廷的较为名贵的团茶赠送,其实还是不想借画给王君。因此,在这里也不能说苏轼寄团茶就是结交之意。我想他之所以拖着不借,无非是因为以下原因:
首先,担心借走不还或还回赝品。宋代摹拓临伪之风盛行,宋代书家米芾就是一个临摹大师,很多经典名作都被疑为米芾临仿之作。比如《中秋帖》就有人认为是米芾的仿本。明代顾复认为:“《中秋帖》,硬黄纸,三行,二二字,气味与《舍内》略同(顾复认为《舍内》乃唐人摹本)。”徐邦达也认为《中秋帖》是宋人仿作:“《中秋帖》笔肥墨饱,很像米芾书《秋深帖》真迹,此与前述王羲之《大道帖》是一类的米氏临书应无疑义。”杨仁恺同样认为《中秋帖》是米芾的临作:“细察此帖书法既不同于《廿九日帖》,又与《鸭头丸帖》异趣,虽说风貌近《舍内帖》,惟痛快有余,而沉着凝练不足,用它与米芾书法核对,不难发现有米氏的笔迹。”作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的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中秋帖》为宋人米芾的仿摹之作,在当今书画鉴定界基本上能够取得一致的认识。
米芾所藏的书画作品存世至今的究竟还有多少,笔者曾做过如下简略统计,兹列举如下:
王羲之的行楷书《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公认乃米芾仿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大道帖》;褚遂良临摹王羲之《兰亭序》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孙过庭的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等。
据《画史》米芾自云:“余家收古画最多,固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精绝,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显然,米芾所藏之书画数量可观,质量亦属上乘。
因此,在宋代,但凡珍贵的书画作品,是不会轻易借人的。熟人都防不胜防,更何况并不熟悉的朋友。因此,苏轼不愿将黄居寀《龙》图借给王君,亦属合理。但苏轼之前又满口答应,如若不借,似乎又说不过去,所以寄去一饼团茶,聊表歉意。一个月以后,在宋代交通不便书信往来缓慢的情况下,基本上也就不了了之了。从这里看,苏轼从内心来讲有点后悔答应将《龙》图借给王君,可又碍于王君和季常相熟,为了面子上过得去,才给季常写了这封信把这个事仔细解释了一番。其实就是翻悔了,可自己是鼎鼎大名的苏大学士,答应别人的事怎么能不兑现呢。碍于面子,还是要和好友季常说清楚了,免得好友说自己小气,不讲信用。
从苏轼此作所描述的人物及事件,我们不难推测出如下人物关系:
在这几个人中,苏轼和陈季常是好友,苏轼在信中向陈季常提到曹光州而未做介绍,陈季常和曹光州应该也是认识的。而王君则和陈季常较为熟悉,不然苏轼大可不必写信给陈季常解释此事,直接告诉王君即可,因此苏轼和王君并没有陈季常和王君熟悉。而黄居寀是五代入北宋的著名画家,《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选登》(2013影像技术)将黄居寀列为五代十国著名画家,顾平将黄居寀列为北宋画家[5]。苏轼出生时黄居寀就已经离世,因此和这些人无直接关系,只是因为他的《龙》图,把这几个人物串在了一起。
苏轼在黄州时期,陈季常是和苏轼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苏轼与陈季常的日常往来书信很多,在《与陈季常十六首》中,其第一至第十四首都是苏轼在黄州时期写的。大量的书信使苏轼与以前的好友保持着精神上的交流,和与他相距不远的陈季常,更是往来频繁,诗酒唱和。
苏轼有关陈季常的诗文,大都写于黄州时期,特别是《岐亭五首》对他们在黄州的交往作了总结,再现了相互之间的交往和深厚情谊:“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复往见之,季常使人劳余于中途。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后数往见之,往必作诗,诗必以前韵。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独至九江。”苏轼离开黄州,“送皆止慈湖,而季常独至九江”,[6]反映了双方情谊的深厚。

表一 苏轼在黄州期间往来诗文
从表一可以看到苏轼与陈季常在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七年(1084)这段时间里,经常一起吟诗作赋,互通书信。而这段时间正是苏轼被贬黄州,最郁郁不得志的日子。
林语堂先生说,陈季常是苏轼在黄州时最好的朋友,好到可以随便开玩笑。比如在《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有这样的描述:“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7]这四句描写的应该就是某次苏轼去探望陈季常时的情景,两人同处一室谈天说地,乃至彻夜不眠。陈季常的妻子柳月娥遂朝陈季常大喝一声,他被吓得拄杖应声而落。
苏轼和陈季常,算是密交。在这封信中,苏轼向密友季常转达自己对王君的愧疚之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苏轼在处理和自己不熟悉的王君借图这个事时,没有选择直接和王君写信说明,而是向好友季常表明自己的歉意,使季常向王君转达自己的意思。通过苏轼和王君与季常关系的对比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在被贬黄州时期的交游情况以及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的态度。
总之,书法作品,其主要功能是用来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我认为在古代,书法的艺术风格尚在其次,主要还是日常表达的一种需要。中国传媒大学书写文化研究院刘守安教授最早提出了“书写”的概念。书写是多元的,它涵盖了汉字书写过程中的各种元素:传播、记录、明理、宣告包括艺术等等。仅仅将艺术功能抽离出来的书法,是单薄的,是缺少文化积淀的。我们在欣赏一件书法作品时,不应该仅仅关注作品的笔法、结字、用墨、章法等表面特征,更应该多关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注释:
[1]乐仁.宣和画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197.
[2]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顾之川.苏轼文集(卷73)[M].长沙:岳麓书社,2008:172.
[4]胡可先.宋代郡守通考补正举例[J].北京:文献(季刊),2003:3.
[5]顾平月.中国宫廷画院历史沿革考略(夏商周至宋代)[J].南宁:大匠之门,2013:47.
[6]王文诰,冯应榴.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4.
[7]倪培森.“河东狮吼”为何指明“河东”[J].咬文嚼字,1999(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