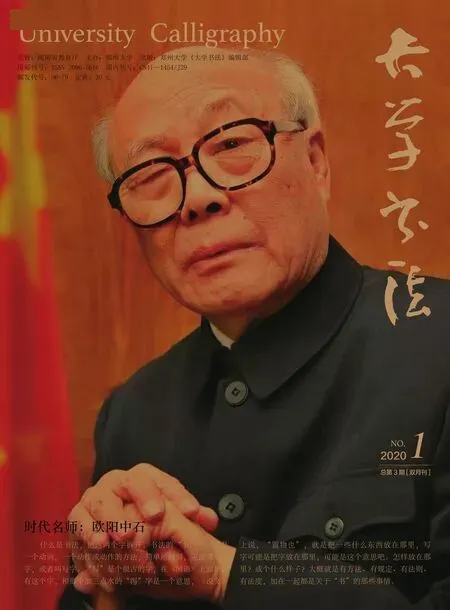苏轼的佛教渊源与书法审美意象生成
⊙ 刘超
2015年《书法》杂志第11期,刊有尹吉男教授的一篇名为《贵族、文官、平民与书画传承》的文章,其中观点认为宋代文官身份的书家在书法传承方面与唐代有别,苏、黄、米、蔡等,在小的时候学习书法大都以阁帖为临习对象,一般家庭接触不到法帖真迹。并且划分出了世袭贵族政治与科举文人政治时代下的书画传承方式以及书画家们的艺术生态环境。[1]笔者由此得到启发,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宋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不乏有出生寒微者,如果连翻刻阁帖也见不到的话,其书法学习之路是怎样的呢?无疑,书院私塾教学的师徒相授是主要的传习方式,除此之外,寺院也潜在地担当着文化传播的职能,寺院提供读书场所、寺院藏书或者说佛教典籍对文化的传承、传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地域环境里,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确实对人存在着显现或潜在的影响,其中佛经抄写在书法历史的长河中也激起过朵朵浪花。下面我们以苏轼为例,探其书法学习的来源,揭开苏轼宦海沉浮的人生际遇下的宗教艺术审美。
一、苏轼的佛教渊源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一代文豪。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文学上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称誉,于诗、词方面造诣非凡,并晓音律、通绘画、精书法,其成就涉及文艺领域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儒、道、释三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得到体现并相互融合,成为后世文人在入世、忘世、出世等不同人生阶段中参照与选择的典范。
苏轼与佛教之间的渊源颇深,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和家庭环境都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
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之乱,宋太祖改变了后周周世宗对佛教的限制管理,他以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对待佛教,允许适度发展。宋太祖最初普度童行八千人,到太宗朝曾一次普度童行十七万余人,特别是在真宗朝佛教一度兴旺。据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时,僧众人数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众人数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寺院四万余所,是宋代佛教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2]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此时儒、释、道三教并用,佛教文化融汇儒、道二家思想精华得到发展,特别是禅宗思想被世人广泛接受。
从苏轼出生至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进京赶考,其间19年的时间,苏轼一直生活在四川。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巴蜀本土文化深深影响了他的认识观,特别是对苏轼哲学观和文艺观的形成种下了种子。蜀地的经济发展在唐朝时已占有重要的比重,“扬一益二”说的就是扬州、益州(成都)两个城市的繁荣程度。佛教发展到唐代中期,各派理论体系已较为完善,其中蜀地佛教氛围甚为浓厚,并以宣扬禅宗思想为特色,如资州的智诜(五祖弘忍的弟子)、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什邡的马祖道一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后来随着唐末五代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诸多高僧入蜀避难宣扬佛法,蜀地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水平以及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进入北宋,蜀地佛教文化更为兴盛,比如佛经雕刻印刷方面,《开宝藏》又称《蜀藏》是我国第一部官版大藏经,刻于宋初益州(今四川成都)。少年时期的苏轼生活在眉山,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距其家乡很近,所以在苏轼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难免会受到佛教的影响。他许多年后还能记7岁时遇到眉山老尼一事,并在《洞仙歌》序中记:
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俱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独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耳。[3]
故事缘起与故事内容是否真实,无考,但从某一侧面可以看到蜀地存在浓厚的佛教氛围,并已影响到了七岁孩童时的苏轼。
从家庭氛围方面来看,苏轼与佛教渊源很深。苏轼50岁时所作《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回忆道: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询、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4]
父母双亲“崇信三宝”“爱作佛事”可以说苏轼是生活在一个信仰佛教的居士家庭。父亲苏洵与蜀地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惟简禅师时相往来,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直接影响,苏轼初来成都即结识了成都大慈寺的惟度(文雅)、惟简(宝月)两位法师。苏轼在《中和胜相院记》中回忆道:
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5]
这是他未进京赶考在蜀地与僧人直接往来活动的记录。母亲程氏信奉佛教与苏轼的外祖父有很重要的关系,《十八大阿罗汉颂有跋》中苏轼记录自己外祖父程公少年时游学京师,回四川的时候遭遇蜀乱受困,蒙十六位僧人相助赖以归家,后来四处寻访僧人不得,自视十六僧为阿罗汉,从此在家供养佛像。不仅仅是苏轼的外祖父、父亲、母亲崇信佛教,而且他的夫人王闰之、妾王朝云以及自己的弟弟苏辙也信仰佛学。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中说:
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6]
自己讲述随父读书,除必修的儒家经典外,年少时的读物中还接触了佛、道书籍。
二、苏轼人生际遇中的佛经抄写与书法探源
中国士人对佛教的接触有别于普通百姓在烧香拜佛中的盲目信仰,他们大都是以研读佛经和交游僧禅为路径。苏轼在一生中与许多高僧有过交游,最早是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的惟度、惟简,还有大觉怀琏禅师,在黄州期间结交到安国寺僧继连,后来与东林常总长老同游庐山,两任杭州时,又与梵臻、契篙、慧辩、辩才、惠勤、惠思、可久、宗本、诗僧清顺等吴越高僧广泛交往。历代文人士大夫在与高僧交往答和中,更多的是着力于佛学思想义理和禅宗美学境界方面的探索与体悟,他们多“以文字而做佛事”,在佛经抄写的过程中研读佛法。
苏轼一生中所抄写的佛经很多,如《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楞严经》《圆觉经》《八师经》《摩利支经》等,其佛经抄写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生历程,并且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轼最早涉猎佛经的抄写大约是在其十五岁时,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记录此事并认为此时的抄写更多的是以佛经(《金刚经》)为练字习书的范本。[7]这一材料为我们重新认识苏轼书法的早期取法问题提供佐证,用佛经当作习字范本的观点在以往分析苏轼书法作品与风格形成的文著中很少提到。学者们往往较多地引用和信服黄庭坚的论断,即“少学兰亭”,如: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颜鲁公、杨疯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8]
这不仅把苏轼书法定为“学《兰亭》”,而且梳理出了早、中、晚三个取法对象的分期。中岁学颜鲁公之说确凿不疑,只是“少学兰亭”似乎不能使笔者完全认同。苏轼在嘉祐四年(1059)二十三岁时所书写的《奉喧帖》(图1),字迹清雅、笔力圆劲、体势开张、重心下移,并无《兰亭》左右映带、字势挺立、笔意飘举的魏晋神采。熙宁二年(1069)的一幅墨迹尺牍《治平帖》(图2)已初露苏轼书法执笔“单钩把笔”“斜握”的端倪。斜执单钩式的书写用笔法在苏轼三十多岁时已技艺娴熟,这与他的日常实用书写相关。一是前面我们说到的抄佛经以习字的书法入门方式,六朝、隋唐抄经生们大都采用斜执单钩握笔法;二是苏轼喜欢以抄书代阅读,速度与法度需要在书写中完美协调,行书书体最为简易方便。所以苏轼在二者之中相互交融,寻找到了一种具有自己审美意趣的书法风格。
苏轼佛经抄写方面的活动与其人生际遇同步演进。在苏轼三十岁以后,特别是晚年(五十岁至六十六岁),佛经抄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七月,因“乌台诗案”入狱,同年十二月底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元丰四年(1081)在城东荒坡建农舍数间,遂自号“东坡居士”。在黄州期间,苏轼经常来城南安国寺事佛,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云: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9]
苏辙也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10]我们可以看出,黄州的苏轼经常在寺院焚香默坐参禅或杜门深居留心翰墨,并且在元丰四年(1081),应友人之请抄写了《摩利支经》。四年后,苏轼又受友人张方平之托抄写了《楞严经》,此次经文抄写完毕并刻板印行,此事在《苏轼文集》六十六卷中有所记载,可见东坡居士对佛经抄写与印行之事相当重视。《黄州安国寺记》中他自云“归诚佛僧”,所以经历黄州谪居宦海苦旅中参禅学佛的生活体验后,苏轼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自己成为一名虔诚的学佛居士。元祐二年(1087)、六年(1091),苏轼又分别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八师经》,这两次是为自己所抄写的,其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抄写两遍,从起初应友人、僧侣之请抄写发展到为自己抄写,可知苏轼已经把佛经抄写活动融入自己日常生活之中。佛经抄写活动一直伴随着苏轼的晚年生活,特别是在惠州、儋州时期的他多次为身边亲朋抄写佛经。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自己人生最后一年的光阴里,为悼念母亲程氏抄写了《楞严经》中的《圆通偈》:
轼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今者北归,舟行豫章、彭蠡之间,遇先妣成国太夫人程氏忌日,复以阻风滞留,斋荐尤不严,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圆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11]
笔者认为苏轼书法实践存在两种路径。第一,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以抄书为内容的日常书写,其追求自然、简便、自适、实用,既符合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动机,也符合“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无意于佳乃佳”的气韵风神。第二,是指苏轼因慕其人而学其书的“书品人品”观念下的学颜路径,主要以楷书作品最为突出,如《颍州听琴帖》《醉翁亭记碑》《丰乐亭碑》《宸奎阁碑》(图3)等。前者属于发乎本真的情感流露与自然书写;后者属于儒家范式中正威仪之风的展示与修炼。前者贯穿于苏轼人生书写脉络之始终,只不过在面貌上有肥瘦、轻重、急缓的变化,或者有二王、颜柳、杨疯子、李北海等诸家之元素,主体气质神采还是苏轼抄经味道下的书写表述;后者就不同了,它是程式化的范式表达,苏轼学得来,蔡襄、米芾也学得来,甚至说南宋楷书家们学得更好、更卖力。济南市博物馆馆藏一块苏轼的书法碑刻作品,《齐州长清县真相院舍利塔铭》(图4)书刻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是苏轼自撰并亲自书丹的小楷精品。铭文凡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每字一厘米半,笔法淳净,雍容有度,沉着端方,撇捺开张,具有六朝、隋唐抄经之遗韵,笔画连带、灵活飘逸,同时参有手札笔意,可堪苏轼小楷第一。此塔铭也是苏轼书法取自佛教抄经之说的最佳代表力作。

图3 苏轼《宸奎阁碑》 拓本

图4 苏轼《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 拓本
三、佛经抄写活动对苏轼书法风格与审美意象的塑造
佛与道在中国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观中起到了调和作用,佛家的圆融无碍、随缘自适与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世观找到了出口,他们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仕途荣辱后,或“由儒入禅”或“由儒入道”。
苏轼的佛经抄写活动伴随其官宦生涯之中,并且佛经抄写以及诵读研习对他人生观的塑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上文中,我们得知苏轼抄写的佛家经文有《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楞严经》《圆觉经》《八师经》《摩利支经》等,或为亲人祈福,或应朋友嘱托,也有为自己所抄。他在佛经抄写、打坐参禅的体验活动中自然也对佛法经义有了自己的体悟,其中“人生如梦”观是他在谪居黄州亲近寺院生活时所确立。行书《黄州寒食诗帖》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其书法风貌与审美趣味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钱泳云:“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腆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坡公之书未易学也。”[12]坡公之书温润不俗,如华严法界,丰腴而有禅机,自然与佛禅大有渊源,这一特点当时就已经引起世人的注意。
苏轼书法成就以行书最为突出,虽然小楷和楷书的水平不错以及草书也偶有临习,但最具东坡文人精神者还属尺牍手札一路的墨迹作品。这种“东坡文人精神”表现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参禅问道、游戏笔墨的书斋生活与尚意自适的日常书写中,更是“一种集士大夫学问、道德与文人审美于一体,融合儒、释、道三家哲学内涵,既受文人敬仰又亲近生活的状态”[13]。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亲近大自然,远离朝廷,加上他旷达豪放的性格,对自己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重新认识和评价,很快从感伤中解脱出来。仕途的不幸与挫折,客观上促使他愈发深求佛理,向往佛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生活。苏轼学佛主要是要悟得物我皆亡、身心皆空之理,求得静心,即心灵的安静宁谧,使自身解脱烦恼,超然物外。因此他写诗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病中游祖塔院》)“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钱道人诗云直须认取主人翁作两绝戏之》)“散我不平心,洗我不平心。”(《听僧昭素琴》)后两句也是求安心的意思,以安静的心境和泰然的态度,来对待外物、外界对自己的干扰,以安静的心境和泰然的态度,来平衡自己不平的心态。
宦海沉浮荣辱与佛道禅理洗礼,使得苏轼在现实磨难中悟到了空,在虚空中又悟到了充实。精神与肉体的磨难使他体悟了“人生如梦”的空的思想境界,反过来又在梦幻的空境里培植出了实的书法美学意象。这就像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开篇“雄浑”所言:“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14]苏轼书法以清雄为审美基调,行书手札气韵贯通,字体欹倾而神奇横溢,可谓“出新意于法度当中”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充分体现。笔者把苏轼书法之“实”归结为三点。第一,下笔之实。黄庭坚在《跋苏东坡水路赞》中记载了苏轼枕腕作书的卧笔书写特点,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15]这种执笔方式无疑是来源于他早期从事抄书和抄写佛经的习惯影响。虽然苏轼曾说“把笔无定法,要是虚而宽”,但是我们细细推敲,苏轼的字形结构多左低右高的倾斜状,就是其枕腕作书的缘故。他强调“虚而宽”是说手掌形虚、笔势走势宽绰横向,并不是指写字空灵超虚,相反更需要笔力下注枕腕实书。我们在分析古人书法审美观与书法实践观时往往会遇到感觉自相矛盾处,能“于矛盾中见不矛盾,方是究竟了义”[16]。第二,落墨之实。苏轼的字中年得颜真卿、徐浩之厚重,用墨喜浓黑,故而浑厚有力,“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17]。通过《渡海帖》(图5)与李邕的《李思训碑》相比较可证此言不虚。笔力“豪劲”,落墨厚实,再加上颜体的雄浑与“北海如象”的力感,形成了苏轼用笔用墨特有的浑雄气象。第三,体势沉实。体势之实表现在字形扁、重心低,撇捺开张,类似六朝、隋唐佛教抄经的结构,再加上墨肥而黑,就验证了苏、黄二人书法互评的一则小故事: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18]

图5 苏轼《渡海帖》 纸本 行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是戏言似的讥讽,所以流传久远,为人津津乐道。仔细品味“石压蛤蟆”一词,其中虽有趣、形象,但还是没点中要害。笔者引申佛教词意以“香象截流”代替“石压蛤蟆”。“香象截流”源自成语“香象渡河”,故事出自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本来是比喻悟道精深而彻底,后来也用以比喻评论文字精辟透彻,亦作“香象绝流”,[19]与“羚羊挂角”一类,在宋代以来多使用于文学诗词评论。这里进一步阐发此义,用来表达苏轼书法雄强而内敛、郁郁而勃发的精神气魄,与苏轼本人磨难中坚毅而豁达的人生境界相合,这也是他融合儒、释、道三家特别是在佛经抄写中提炼出的“勇猛精进”归于敦厚透彻的宗教艺术精神。
金人赵秉文在《跋东坡四达斋铭》中评价道:
至于字,外匠成风之妙,笔端透具眼之禅,盖不可得而传也。观其胸中,空洞无物,亦如此斋焉四达。独有忠义数百年之气象,引笔着纸,与心俱化。[20]
进入“无物”的书写状态,由书写境进入禅定境。在贯穿苏轼一生的荣辱际遇中,我们可以看到佛经抄写活动伴随他至黄州、惠州、儋州,并且为其豁达人生观的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贬谪苦楚生活中得以安放身心。唐人亦有书论曰:“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21]如书《金刚经》《赤壁赋》等,温和典雅,平静而能见忘我内心达到无限的充实之境。
四、结语
苏轼书法的取法后世多引用赞同黄庭坚的“少学《兰亭》”说,并且又把苏轼学书历程分为三期。但是仅凭黄庭坚此说,我们在苏轼的书迹中找不到印证,虽然有一些学者引用:苏轼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在蜀为父苏洵服丧期间,得苏辙带回河朔本《兰亭序》,逐字展玩研习,反复临摹推敲。[22]这也恰恰证明,在此之前苏轼没有或者很少有机会得到《兰亭序》摹本或者临本来进行书法训练的,黄庭坚的“少学《兰亭》”说自然就难以站得住脚。
笔者通过考察苏轼少时生活环境、读书习惯和入仕后人生际遇中的一系列抄经活动,以及对其流传下来的书迹及运笔、用墨特点进行推敲,分析得出:苏轼书法取法很大程度上受早期所熟练的抄书笔法影响,即十五岁前后以佛经(《金刚经》)为练字习书的范本,从小读书以笔抄书的阅读书写习惯,形成苏轼书法执笔“单钩卧笔”的书写特点,加上宦海沉浮中伴随其一生的佛经抄写活动,最终形成字形左低右高“似欹而实正”的结构和字势横向“香象截流”的体势力量之审美意象。以上如有偏颇与不妥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尹吉男.贵族、文官、平民与书画传承[J].书法,2015(11):93.
[2]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241.
[3]苏轼.洞仙歌序[G]//苏轼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327.
[4]苏轼.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G]//苏轼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674.
[5]苏轼.中和胜相院记[G]//苏轼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701.
[6]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G]//苏轼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218.
[7]参见刘金柱.苏轼佛经抄写动因探析[J].佛学研究.2003(4):204.
[8]黄庭坚.山谷题跋(卷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62.
[9]苏轼.黄州安国寺记[G]//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6):4776.
[10]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G]//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10):7019.
[11]苏轼.跋所书圆通经[G]//苏轼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821.
[12]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宋四家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9:291.
[13]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兼论“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J].荣宝斋,2019(4):143.
[14]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38.
[15]屠友祥.山谷题跋校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122.
[16]乌以风.问学私记[G]//马一浮全集(第1册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772.
[17]屠友祥.山谷题跋校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125.
[18]曾敏行.独醒杂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于朝兰.“香象渡河”源流考[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185.
[20]李福顺.苏轼书画文献集[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103.
[21]毛万宝、黄君.中国古代书论类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7.
[22]李利仁.苏轼书风探源及影响[D].南京:南京大学.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