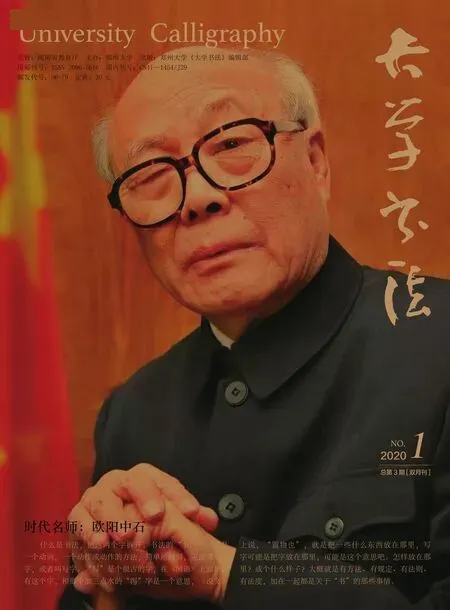南天水暖北斗星高
——欧阳中石先生书学教育思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远影响
口述人:张法亭(珠海中国书学院院长)

一、出访澳门
澳门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西方的宗教、绘画、科技等很多由澳门传入内地,内地人也从澳门看到了西方世界。1997年,北京市政协书画家联谊会应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邀请到访澳门,老师(欧阳先生)担任访问团团长。澳门著名书画家以及来自北京、广州、香港的四地书画名家济济一堂,进行学术及艺术交流。新华社澳门分社宗光耀副社长、宗德路部长等有关领导,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会长苏树辉、理事长霍志钊,广东中华民联文化促进会方代庆等出席活动。在澳门访问期间,老师在澳门大学为中文系研究生进行了书法文化讲座,途经珠海时在珠海书学院为师生讲学。
1999年,老师和师母在澳门回归前夕再次应邀来到澳门,到访新华社澳门分社并为新竹苑贵宾餐厅题写了横幅书法“调和鼎鼐”。社长王启人说道:“欧阳老寓意深刻啊!从字面看是讲烹调,实际上又是讲治理国家。”老师为新竹苑莲竹厅题写的另一横幅书法是“不染高节”,因为澳门市花是莲花,莲花自古被誉为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气节。2月6日晚,老师应邀在碧丽宫与颐园书画会林近先生等一起挥笔泼墨,尽兴雅集。出席活动的还有一位是在澳门享有较高声望的崔德祺先生,已是88岁高龄,恩师即刻为崔老题赠条幅“惟德乃祺,既米期茶”。老师解释说:八十八叠摞起来就是一个“米”字,中国人称88岁为“米寿”,更长寿的是“茶寿”。“茶”即“艹”加“八十八”,是108岁。
2月8日晚,93岁的梁披云老先生宴请老师一行,梁老清晰地回忆起1985年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老师首次见面的情景。梁老90岁寿辰恰逢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老师与书法界朋友共同在中国文化书院为梁老祝寿。老师在出席宴会上极为称赞梁老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并书写条幅“拔地高山捧日,支山大树披云”为梁老祝寿。
在谈及对澳门感受时,老师讲,澳门是个文化多元又和谐的地方,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接受西方的文化。澳门林则徐纪念馆很有历史意义,澳门人同样有着中华民族的情怀。他在参观澳门博物馆时讲,馆中文物展示了澳门的历史,澳门人过去的生活场景及生活工具都有再现,这对于后人和外来人了解澳门很有帮助。在澳门访问的第三天老师来到澳门最大的寺庙观音堂参观,在院内露天平台上有一个圆形的石桌,石桌的中间位置有一条裂痕,形成东西两个部分,这就是当年清政府与美国签署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石头桌子。老师在签字处,以挥手的姿态留影,并讲道:“我所表达的是即将回归更令我激动,因为澳门离开家的日子太久了。”
2009年4月,老师再次受到澳门文化社团的邀请来澳访问,受到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的会见,同澳门专家学者会面交流,并走访了圣若瑟大学多个知名学院。老师谈到,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缺少中西物质的交融,我们要用健康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的交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是隔绝的成分将越来越少,心胸有容量,心襟更开阔,就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天涯有限心无限,碧落披襟抚九州。”老师以自作诗句来表达对于改革开放的无限情怀。
途经珠海时停留几日,我陪同他到孙中山故居中山翠亨村(中山以北,靠近珠海)参观。其间,老师讲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和学问,并仍然保持着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事风格和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当老师得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是珠海唐家村人时,老师说道:“那也是我的老师啊!”语气中充满崇敬之情。

欧阳中石 行书手批
二、书教笔记
老师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逻辑思想史,是逻辑学科班出身,深得金岳霖先生真传。老师的书法,少年时期师从武岩法师,手临魏晋隋唐书法;年轻时师从吴玉如先生,着意“二王”书法,以及到后来的章草,是成体系的学习和研究,漫漫书法历程,更是专业的科班了。
老师博大含宏的书法教育思想,儒雅厚重的书法境界,古风涵泳的诗词歌赋,凝重深沉、神态自如的京剧艺术,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探求。
跟随老师多年,受到许多教导,现犹庭训在耳。根据当年的笔记选抄几则,对于研究老师的教育思想将有帮助。
1. 书法不仅是门艺术,同时更是一门学问,之所以成为艺术而生生不息,就因为它的背后有很深厚的一门学问在支撑着它,它走得越远,随之而来的学问也就越深越厚。要求注重传统,注重传承,书法必须“字面文心”“文从字顺”,如果只限于写字那是远远不够的。书法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把其他行道的东西硬往书法里套。如果只凭自己的主观感受把书法作为一门玄奥的东西,势必走向歧途。至于那些写得让人看不懂的似是而非的作品,历史曾经做过评判,如果偏不信,那么历史会再给你做出评判。
2. 什么是保守?什么是创新?我们认为,喊保守的人未必是真保守,喊创新的人也未必真创得了新,那种人人都会弄的东西能叫创新吗?规律性的东西大概都有一个原则,如果不在写好的规律中走,就很可能走进写坏的规律中去。人的五官位置并没有大的差距,基本都长在同一个位置上,由于细微的不同,在审美上却有着美和丑的很大差别,所以不要费大劲儿去大拆大卸。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想到前人在说这句话时所处的环境和位置,他们又是处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
3. “临帖无我,自作靡人”。在学习中汲取,在学习中否定自己,在学习中更新自己。只有学习那些好的,自己才会变好、变得丰富起来。老师不主张不得法的“苦用功”,并认为拼功夫就是拼命,那不值得。肯于否定自己,否定最初的基础,不断地学习,就是在打破昨天的基础,从而获得新的提高。写字是思想的认识问题,用手写字只是一种掌握运笔的能力,把所想的表达出来,书法最终还须提高学问,以极短时间获得更多的知识。
4. 现在一个艰难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在前进,产生了新的思潮和新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能不能定下来,这不是今天就可以有定论的,但可以有个办法,就是从历史上找个证明。历史在评判标准上是无情的,不好的扔掉,好的保留,不管当时你有多大权势,不管当时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潮。每个朝代都经过了这样的浪淘沙,保留下来的比较来看都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历史的,也是比较明确的。
5. 从汉代赵壹《非草书》看,历史已经做出过选择,否定了那些胡写乱抹的。大概每个朝代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家,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创造,我们所想到的事情,古代贤者未必没有想到。他们是那段历史的书法高峰,在那个时代创造了他们的辉煌,而我们在今天未必是今天的人杰。我们不要对历史视而不见,不要以为他们都是腐朽落后的,应该把历史上那些好的学到手变为己有。因此,要想超越过去,必须先赶上去,而不是把先贤们打倒。
6. 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这是针对当时书法风气弊端来讲的,也是从他自己所达到的那个水平来说的,必须考虑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他的方法对我们是否适合。我们写的是字,就要有一定的写字限制,任何艺术都是在它的法则之中充分发挥创造力,合乎法则创出新意。在谈艺术个性的时候,不妨先服从共性,学习历史上那些好的东西,只要我们付出劳动和努力就会取得回报,在共性之上形成个性。
7.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观点,就是学习别人,学习我们昨天不会的东西、不懂的东西、不同意的东西。当我们把别人好的东西学会的时候,必能有足够的条件超过那个学得好的。艺术创新是必要的,到了该创的时候不创也不行,到时想保守也保守不了,达到了那个程度,想不变都不可能。书法有两种追求创新的方式,一种是把人家的变成自己的,另一种是把自己的变成人家的。为了充实自己,还是把人家的变为自己的好。
8. 学习也应有慢速、中速、快速三个阶段。初学楷书既能学什么像什么,但又要有主次之分。临字的时候不要大篇地临,要从中找出几个代表性的,临得尽可能地像。如果能写好一个字,绝对像,写第二个字时,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但我们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影响到学习的效果。一本帖能选出几个字,在每个字上下功夫,能一个个写好就不得了。对于初学者来讲先写像再说别的,有些话说早了反而有害处,在没有继承之前,强调创新就是如此。
9. 1990年老师在书房与几位同学座谈时讲,我们开办这个专业抱着一个不负于祖先、无愧于子孙的信念。书法专业有我们的一套制度,我们这个教学体系和师资队伍,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如果不是培养“书匠”,就必须加强中文系的课程,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最近出版了一本当代史学家、数学家、词学家的书法集子,里面的作品并不比当今几位书法大家逊色。
10. 字写得好,不仅要有功夫,还要有艺术境界,关键是要有学问。学习的关键问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对于多种艺术形式的创作,要谨慎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诱惑,应该冷静地分析分析,涂有毒药的糖葫芦很容易让人上当。
11. 老师的要求是严格的,人往往是当面给你的分数高,背后的分数却很低,而后者却是真实的。但是,学习要有个正确的标准,不管别人说好还是说不好,都要坚持方向。练字不是练手,而是练心,手能达到掌握笔的能力,再把心里想的表现出来。书法最终表现的仍然是人的思想,眼睛只是一种媒介,把观察到的准确地反映在头脑里,再由眼和心支配手,书法最终还是体现在学识修养方面。不仅要接受当面的好话,也要接受背后的批评。不仅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看问题,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