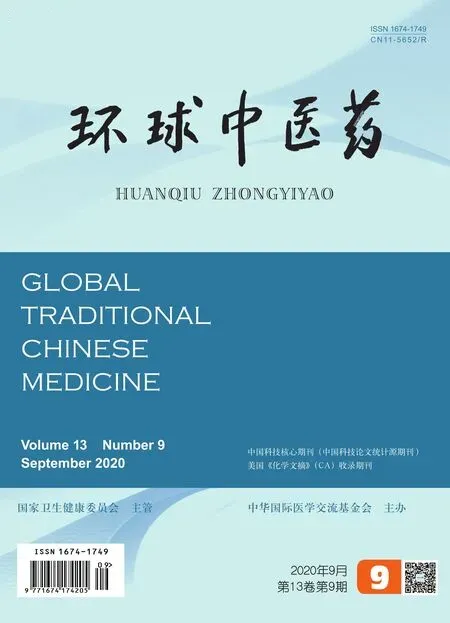应用大柴胡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经验
郑娴 王凤荣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如冠心病、高血压病等,严重威胁着人们健康。为提高临床疗效,笔者多年来致力于AS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与实践,笔者注意到少阳枢机不利对AS有较大影响,遂将《伤寒论》“和解少阳,内泻热结”之大柴胡汤应用于AS性疾病的防治。从现代研究角度看,大柴胡汤有确切的抗炎、降脂作用,与AS的炎症反应发病机制相吻合。但具有上述作用的中药和方剂数不胜数,为何大柴胡汤用之取效,必然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是方证相合使然。
1 少阳枢机是血脉通畅的关键因素
在中医理论中,血脉由心所主,理论来源于《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云“心主身之血脉”,《素问·平人气象论篇》云“心藏血脉之气”,《素问·五脏生成篇》亦云“诸血者皆属于心”。经后世医家总结,便形成了“心主血脉”的认识,认为心气推动和调控血液在脉道中运行。然而,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的功能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AS性疾病,虽为心主血脉功能的异常表现,但这种异常除与心的功能密切相关外,其它脏腑的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少阳枢机”就是血脉通畅的关键因素之一。
1.1 心主血脉功能须赖肝胆、三焦气机之运转
“枢”的原意是指门轴,古人认为枢机为“制动之主”。可见,枢机主要与“动”有关。而有规律的“动”,才是人体健康生命活动的体现。以枢机为中心的运动,就是维持这种规律运动的机制之一。枢机是以枢转气机为基础的沟通阴阳、气血、表里上下的枢纽。人体的枢机主要有开阖之枢,即少阳和少阴,及脾胃升降之枢等。
笔者认为AS的发生主要与少阳枢机不利有关。《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云:“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胆与三焦同属少阳。一方面胆配属于木,主阳气生发,与肝相伍,肝胆疏泄正常,畅达气机,若转枢不及,则气机郁滞;另一方面,三焦具有通行诸气的作用。《难经·三十八难》曰其:“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言:“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可见,三焦主通行元气,使元气布散全身,达腠理以抗邪,运行诸气以调节气机。三焦亦是人体津液代谢和水谷运化布散的道路。《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若转枢不利,则汗出、胸中满而烦,津液疏布不利则出现咽干、口渴等[1]。此外,手少阳三焦之脉,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
因此,心血欲流畅无阻,亦须赖肝胆、三焦气机运转自如,若肝胆失疏、气机失常,则气血闭阻、心脉不畅、心失所养。少阳开合得宜,升降自如,则气血得以通畅,少阴水火也能够相交。若邪犯少阳,枢机不利,三焦不畅,气血运行障碍,则易生痰、成饮,致脾胃升降受阻,进而血滞为瘀、津凝成痰,造成膏脂等有形实邪积聚,或郁而化火、痰热上扰,或痰瘀互结、变生热毒,因果循环,不断恶化[2]。
1.2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临床表现类似少阳证
笔者认为,AS虽为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可引起多器官受累,而不同器官的病变在临床表现上却多体现出了类似少阳证的特点。如冠心病心绞痛、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的间歇性跛行等疾病,呈发作性发病,类少阳证“往来寒热”之性;在症状累及部位上亦与少阳相关。如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时多表现为前胸、两胁、心下、左臂等部位的疼痛,而这些部位多为胆经循行部位。这与《黄帝内经》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篇》云: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胸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此外,在症状上亦有相似之处,如高血压病,患者多见头痛、眩晕、眼花、耳鸣耳聋、项强、心烦、易怒、口干口苦、便秘苔厚等症,与少阳提纲证“口苦、咽干、目眩”的表现基本吻合[2]。
2 大柴胡汤斡旋枢机,畅通血脉,切中动脉粥样硬化中医病机
目前,关于AS病因病机的认识尚无统一性论述。但综合各家之言,其病机不外虚、实两面。如王椿野等[3]通过检索5年与AS相关的文献,对证候要素进行频数、频率的统计分析,对AS的中医病机做了相对系统的总结。由医家论点文献提取的频率在50%以上的证候要素有血瘀、痰浊、气虚,提示AS为本虚标实之病。然而,临床上单一病机少见,多为“虚实夹杂”之证。如痰瘀常并见,痰瘀阻滞日久,不仅可耗散心气,又可化热伤阴,形成恶性循环。
大柴胡汤中几个非常精妙的配伍,给笔者提供了重要的治疗思路。从《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的加减法可以看出,方中黄芩、人参、半夏、生姜、大枣均可去,唯柴胡、甘草不可去,可见小柴胡汤的核心是柴胡、甘草。而大柴胡汤中没有甘草,因此,笔者认为,大柴胡汤并不是小柴胡汤的变方,它的组成有其独特的组方思路。
2.1 柴胡与黄芩一表一里、一升一降条畅少阳枢机
少阳枢机不利,治当以“疏气转枢为先”。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云:“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和解少阳的代表方剂是小柴胡汤,方中柴胡配黄芩为和解少阳之主要配伍[4]。大柴胡汤承袭了这一配伍,且二者用量亦与小柴胡汤相同。柴胡味薄气升,故《本草备要》云柴胡:“主阳气下陷,能引清气上行,而平少阳、厥阴之邪热,为足少阳表药。”《金镜内台方议》云:“柴胡味苦性寒,能入胆经,能退表里之热,祛三阳不退之邪热,用之为君;黄芩味苦性寒,能泄火气,退三阳之热,清心降火,用之为臣。”柴胡、黄芩合用,一表一里、一升一降,外透邪、内泄热、疏肝气、降腑浊、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使少阳枢机得以通畅条达[5]。
2.2 通腑泻痰实之标、健脾抑生痰之本
痰浊阻塞脉道是AS的重要病机之一。而大柴胡汤中大黄苦寒,善泻热毒、破积滞、行瘀血;枳实苦、辛,微寒,可破气、散痞、泻痰、消积,与大黄配伍具有活血行气、泄热散结的功效;半夏辛温,善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6]。因此,大柴胡汤对脉中“痰浊”可谓是有的放矢。
由于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所载大柴胡汤方药组成相差一味大黄,所以,对于大柴胡汤中有无大黄的问题,成为后世医家争论的焦点。不知是仲景有意为之,还是在后世的传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7]。对于大黄的应用,笔者认为,学习和运用古方关键是把握药理,了解配伍每个药物的目的,并不必拘泥于古方的固定形式。大黄味苦,性大寒,入脾、胃、大肠、肝、心包经是其作用基础。仲景善用大黄,从大柴胡汤中大黄的剂量以及用法上来看与泻下剂明显不同。大柴胡汤中大黄用量仅为二两,而在代表性泻下剂大小承气汤中,大黄均为四两;在用法中也没有采用后下的方法,而是用了“去滓再煎”的煎服方法[7]。正如徐灵胎言:“再煎则药性和合,能使经气相融,不复往来出入。”可见,仲景之意不在攻下。
大黄与破气散结的枳实同用,使大柴胡汤中融入了小承气汤的精髓,在“和解”之法中,又加入了“下法”之意。这一点从仲景原文中可以得到证实。《伤寒论》103条云:“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金匮要略》云:“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但并非针对热与肠中燥屎互结之少阳兼阳明腑实之证,所采取的攻下之意,而是取其通腑泻热之功,给邪热以出路。笔者赞同《医宗金鉴》和《名医别录》的观点。《名医别录》言大黄:“平胃,下气,除痰实,肠间结热,心腹胀满,女子寒血闭胀,小腹痛,诸老血留结。”《医宗金鉴》言本方:“少加大黄,所以泻结热也;倍生姜者,因呕不止也。”因此,笔者认为大柴胡汤中大黄与枳实的用意在于除痰实泻热,也常于临证中遵原方配伍比例使用。
此外,生姜和大枣在大柴胡汤中虽作为使药应用,但却有顾护脾胃的重要作用,还可调和诸药,并有防止诸药攻伐太过之弊。“脾胃生痰之源”,生姜和大枣的使用,可谓标本兼顾,既健脾抑生痰之本,又可与半夏配伍,增强化痰作用。诸药配伍,既可疏利肝胆之气滞,又可通腑泻浊,使痰浊去、脉道通、血运无阻。
2.3 药入血分,祛瘀之力强
AS形成后,管腔狭窄,常表现为血液流变学异常,形成“痰瘀互结”的复杂病变。因此,在治疗中常配伍活血化瘀之法。大柴胡汤与小柴胡汤相比加大了血分药的比重,具有较强的活血化瘀之功[8]。
大黄始载于《神农本经草经》被列为下品,主要因其药力迅猛,非大补之药。但《神农本草经》就已记载其广泛的功效,即:“味苦,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癥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可见,大黄第一大功效就是“下瘀血”。加之其清血分之热,又能防止郁热耗伤营阴,使血热得散、郁热得除。《日华子本草》言大黄:“通宣一切气,调血脉,利关节,泄壅滞水气,四肢冷热不调,温瘴热候,利大小便,并敷一切疮疥痈毒。”[9]枳实配大黄,一入气分,一入血分,能引阳明之热下行,功可泄热导滞、通利积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
白芍苦、酸,微寒,善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与大黄、枳实相伍,可增强行气活血之功,又可防诸药苦寒伤阴。故《本草经疏》言其为:“手足太阴引经药,入肝、脾血分。”《本草备要》言:“白芍补血,泻肝,涩,敛阴,苦,酸,微寒……泻肝火,安脾肺。”由此可见,大柴胡汤对于痰瘀互结的有形实邪结聚血脉之证,不仅可使痰瘀破,并可导邪外出。
3 大柴胡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临证要点
虽也有专家认识到少阳枢机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如程丑夫教授以小柴胡汤为基础,采用和解少阳、疏通气机之法[10]。而笔者注意到AS性疾病往往病程较长,“火热”之象明显。如冠心病患者,症状以闷痛多见,由血瘀所致的刺痛相对少见,而热毒内蕴症状多见,如口干、口苦、口臭或口舌生疮、不思饮食、脘腹胀满、心烦、便秘等,同时可见舌红、苔黄厚腻、干燥,脉多滑数[11]。故治疗宜注重清热化痰之法,而大柴胡汤清热之力较小柴胡汤更强,因此,主张用大柴胡汤加减以和解少阳、调理气机、清热降火,可谓独辟蹊径。
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共有4条原文提及大柴胡汤。以“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为辨证要点,也说明了大柴胡汤证的病变性质为热郁[7]。除与少阳枢机不利、气郁化火有关之外,亦与相火妄动有关。相火的本质是人体阳气,根源于肾、命门,寄位于少阳三焦、心包之处,通过少阳三焦而通行全身。各种原因所致的少阳三焦郁滞均会影响相火的正常输布,相火妄动会扰动心君之安宁,出现情志方面异常[12]。
大柴胡汤中柴胡“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神农本草经》)。黄芩主治烦热,与柴胡相配,可和解少阳、清解胆热。大黄配伍枳实除痰实、泻热结,又避免闭门留寇。正如王宗柱[13]观点:“和解少阳,通腑泻热是大柴胡汤的基本功效;邪结胆腑,病居心下是大柴胡汤证的病位重心;少阳枢机不利,胆腑热壅气滞是大柴胡汤的本证。”
笔者以大柴胡汤为主方,取其和枢机、解郁热、达三焦、畅气机之效,理法得宜,辨治准确。善从临床实际出发,确立大柴胡汤主要适用于实证偏重、热象较为明显的AS性疾病患者。
4 大柴胡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科学依据
在本研究团队开展了多项大柴胡汤的基础研究,分别观察了大柴胡汤的调脂、抗氧化、抗炎以及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等作用。结果显示:大柴胡汤能调节血脂;可通过降低脂质过氧化物的含量,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磷脂氢谷胱甘肽过氧化酶活性,促进自由基清除,起到抗氧化作用;抑制血管壁平滑肌细胞表型的变化;可阻抑原癌基因c-mycmRNA在AS斑块内的表达;可通过降低C反应蛋白水平,抑制核因子-κB、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细胞间黏附分子-1、白介素-8、淋巴细胞表面抗原CD40及其配体、细胞表面趋化因子受体2、基质金属蛋白酶2、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1等炎性因子mRNA和蛋白表达,起到抗AS作用。 以上研究成果,证实了大柴胡汤具有多靶点、多层次的作用,为大柴胡汤防治AS性疾病提供了科学依据[6,14-17]。
5 结语
经方是中华民族的原创,传承至今几千年,依然活力四射[18]。当今,经方已为许多疾病的治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思路。AS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形成过程,随着病变阶段和体质的不同,病机定会随之发生变化,很难用固定的病机来概括,临证时应结合患者临床实际表现灵活辨证。笔者结合大柴胡汤在临床中的证治体会,认为大柴胡汤所治是“少阳枢机不利,胆腑郁热过甚”所致之证。大柴胡汤立方主旨在“和”与“下”,和解与通下并行。乃寓疏利肝胆之气于通腑泻浊、化痰祛瘀之中,使气通而不滞,散而不郁,气机和调,经络通利,津液输布运行无阻,血行无滞,脾健胃和,痰浊、血瘀散而不结,脉道通畅,血运无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