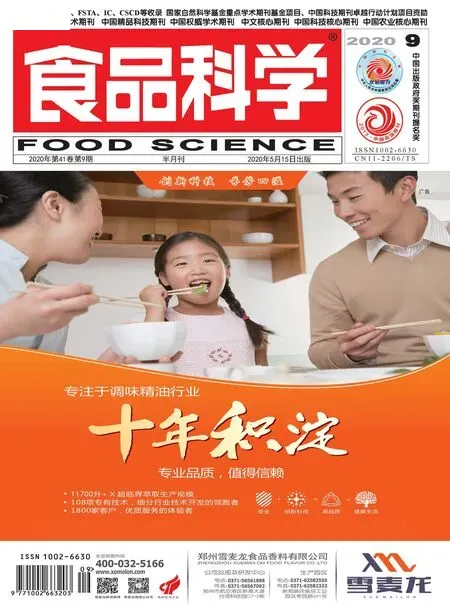细胞壁多糖与酚类物质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易建勇,赵圆圆,毕金峰*,吕 健,周 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综合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植物细胞壁的骨架是一个由多糖大分子组成的三维矩阵,其中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等结构大分子,以及少量糖蛋白、酚酸酯、可溶性蛋白和金属离子。细胞壁是一种不均一的、动态的大分子单元,这种结构中纤维素包埋在由果胶、半纤维素、结构蛋白质和一些酚类物质组成的复杂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类似三维矩阵的刚性结构[1]。酚类物质广泛存在于各类植物组织中,包括一系列具有复杂结构的化学物质:单酚的基本结构包括一个苯环,由此衍生出各种酚酸和酚醇;多酚是一类含有芳香环和苯环的植物次生代谢物,包括酚酸、香豆素、黄酮、异黄酮、木质素、芪类和酚聚合物等[2]。研究表明,酚类物质与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神经性疾病、肿瘤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都有密切关系[3]。细胞壁多糖与酚类物质可通过共价键、氢键等多种形式结合,这种结合与酚类物质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和生物利用息息相关,也影响着多糖和酚类物质的营养健康功效,还与果蔬食品的色泽等加工品质紧密联系。所以明确细胞壁中大分子物质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加工中的变化与果蔬制品质构特性的关系仍然是一项颇具挑战的工作。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多糖与酚类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以及两者相互作用对营养功效、人体健康和食品加工的作用,探讨了多糖与酚类物质相互作用的研究趋势。
1 影响多糖和酚类物质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
1.1 多糖结构对其与酚类物质相互作用的影响
首先,细胞壁多糖的来源和种类显著影响其与酚类物质的结合能力。Padayachee等[4]研究发现,增加纤维素和果胶复合物中果胶的比例,可提高其对胡萝卜汁中花青素的吸附,表明果胶物质对多酚类物质的结合能力强于纤维素。Ruiz-Garcia等[5]发现细胞壁多糖对花青素的表观吸附常数从高到低排序为果胶、木葡聚糖、淀粉和纤维素,纤维素和木葡聚糖的构象也有利于其结合更多的多酚类物质;而果胶由于空间位阻,其结合酚类物质的总量相对较低。在果胶分子形成凝胶的过程中,可形成疏水的袋状结构,这也有利于其吸附更多的花青素分子。此外,细胞壁物质提取过程中经梯次洗脱出来的不同组分与酚类物质的亲和能力不同。Ruiz-Garcia等[5]还分别采用环已烷二胺四醋酸(1,2-cyclohexylenedinitrilotetraacetic acid,CDTA)和不同浓度NaOH溶液顺序洗脱分离,得到了葡萄皮中不同组分多糖,发现不同细胞壁物质对原花青素的结合能力有显著性差异。例如,粗提细胞壁物质可结合质量分数54%的原花青素,而用CDTA溶液去除其中的聚半乳糖醛酸组分后,其结合原花青素的能力大幅下降;半纤维素组分也表现出对原花青素较高的亲和力,但梯度洗脱后剩下的以木质素和纤维素为主的残留物对酚类物质的亲和力则相对较低。Padayachee等[4]研究表明,不同于果胶和纤维素的复合物,在最初的1 h内纤维素对绿原酸、咖啡酸和阿魏酸有较高的吸附能力,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们对多酚物质的亲和力则与单纯的纤维素体系没有显著差异,推测多糖结构和组成差异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Simonsen等[6]研究发现,虽然从燕麦和大麦中提取的β-葡聚糖的组分、结构和流变特性存在差异,但它们对21 种不同香兰素衍生物的结合能力却极其相似。总之,细胞壁多糖自身的化学结构是影响其结合多酚的重要因素。
果胶分子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细胞壁中的多糖,果胶分子的化学结构和构象对其结合多酚物质的影响近年来备受关注。通常高酯化度果胶对原花青素的结合能力更强,这表明疏水作用对两者的结合起到主要作用[7]。酯化度的提高可以增加果胶分子链的自由度,有利于其与原花青素分子相互结合。Gonçalves等[8]研究发现,不同种类多糖与原花青素的结合能力不同,亲和性从高到低依次为黄原胶、多聚半乳糖醛酸、阿拉伯胶和果胶。此外,不同类型的多糖在溶液中的构象存在差异,例如黄原胶和多聚半乳糖醛酸可通过凝胶作用将酚类物质包埋,而阿拉伯胶和果胶的构象则不能产生包埋作用,导致无法结合原花青素。Watrelot等[7]发现,柑橘果胶和苹果果胶与原花青素的结合方式明显不同,即当柑橘果胶分子中有更多的鼠李糖基团时,会提高其构象的自由度,这将有利于其与多酚物质的结合;但由于空间位阻的影响,中性糖侧链可能不利于果胶和原花青素的结合。他们还通过研究果胶支链结构中鼠李半乳糖醛酸,发现不同果胶与原花青素的结合能力依次为鼠李半乳糖醛酸支链、阿拉伯聚糖、I型半乳聚糖-木糖聚半乳糖醛酸混合物、I型半乳聚糖、阿拉伯聚糖-II型半乳聚糖混合物和阿拉伯聚糖[9],推测果胶分子中的线性主链骨架可能具有聚集或结合较多的原花青素的能力;此外,由阿拉伯聚糖组成的侧链比由半乳聚糖组成的侧链在空间构象上更加灵活,这限制了果胶与原花青素的连接;II型半乳聚糖含有较多的分支结构,所以其与花青素的结合能力也较低。II型鼠李半乳聚糖醛酸聚糖对花青素的结合能力较低,这一结果与Riou等[10]的研究结果不同,推测是实验条件差异引起的。已有研究在提取细胞壁多糖组分时常采用透析去除小分子物质,但经透析提取后的细胞壁多糖组分与多酚物质的结合特性可能与真实食品体系中两者的相互作用特性不同[6]。另外,由于多糖组分的复杂性,以细胞壁粗提物为对象开展研究难以从机理上深入解释两者的相互作用,因此有必要将其中的果胶、半纤维素、纤维素和木质素等不同组分分离纯化后,构建模拟体系深入研究。
其次,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由化学或物理作用引起的多糖结构变化也可显著影响多糖与多酚的结合能力。例如,在100 ℃下干燥72 h后可降低苹果细胞壁物质的孔隙度,同时提高其吸附酚类物质的总量和单位面积的表观亲和力[11]。这可能是因为高温干燥过程可破坏纤维素的物理结构,使得多酚物质更容易与多糖结合,进而促进了细胞壁多糖相互交联,提高了细胞壁物质表面的疏水性。Simonsen等[6]发现,大麦中的β-葡聚糖酶解可降低其结合香兰素衍生物的能力。加工是许多食品制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这些理化过程对多糖、酚类物质结构的影响,及其对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研究还较为缺乏。
1.2 酚类物质的结构和含量对其与多糖相互作用的影响
酚类物质的种类及分子结构是影响其与细胞壁多糖相互作用的另一个因素。不同果蔬原料来源的花青素、单宁、黄酮和酚酸等不同类型的酚类物质以及不同体系状态下两种物质的相互作用被广泛研究。Padayachee等[4]研究表明,不同种类酚酸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能力不同。其中,浓缩胡萝卜汁中的阿魏酸、绿原酸和咖啡酸等酚酸物质与果胶-纤维素复合物的结合能力较强,而单纯的咖啡酸则表现出较低的亲和力。此外,在包含羟基苯甲酸型和羟基肉桂酸型等13 种不同类型的酚酸中,甲基化程度与其对燕麦可溶性β-葡聚糖的结合能力呈负相关。Wang Yuxue等[12]比较了3 种不同结构的肉桂酸对燕麦β-葡聚糖的亲和力,发现邻羟基肉桂酸对燕麦β-葡聚糖的亲和力高于间羟基肉桂酸和对羟基肉桂酸。黄酮、黄酮醇、黄烷酮和异黄酮这4 种酚类物质与燕麦β-葡聚糖的结合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与多糖的结合能力由低到高的顺序为黄酮、黄酮醇、黄烷酮和异黄酮。当黄酮类物质具有3 个或少于3 个羟基时有利于其与细胞壁物质结合;而当羟基数量为4 个或更多时则不利于两者相互作用。此外,糖基化对其与细胞壁物质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这主要取决于黄酮的种类。Padayachee等[13]研究证实,无论酰基化与否,花青素与纤维素、纤维素-果胶复合物的结合能力均无显著差异。Gonçalves等[14]发现葡萄酒中的花青素可与酒中的细胞壁大分子物质结合,特别是当花青素与香豆素基团或者乙酰基团结合后,其与细胞壁大分子的亲和力要强于没有上述基团的花青素分子,表明疏水作用可能在花青素与多糖结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该项研究的结果与Le Bourvellec等[15]的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则说明了酚类物质的结构在多糖和酚类物质相互结合中的重要作用。Fernandes等[16]通过研究花青素-3-葡萄糖苷和飞燕草素葡萄糖苷与柑橘果胶的相互作用,发现含有3 个羟基基团的飞燕草素-3-葡萄糖苷与果胶的亲和力更强,表明羟基可能通过形成氢键参与了两者的结合。研究发现,来自葡萄、苹果和梨中的不同类型原花青素对细胞壁多糖也表现出不同的亲和力。Le Bourvellec等[15]发现酚类物质的结构和组分显著影响了原花青素与苹果细胞壁物质的结合,即原花青素的分子质量、聚合度以及儿茶素单体在原花青素结构中的数量都与其对细胞壁物质的亲和力呈正相关性。与聚合度相比,原花青素的分子质量对其结合细胞壁物质影响更加明显。此外,花青素可能有多个位点可以同时与果胶结合,因此,分子质量较大的原花青素容易拥有更多的结合位点。在此基础上,Bautista-Ortín等[17]研究了表儿茶素、表没食子与儿茶素混合物、表儿茶素与没食子酸酯混合物、表没食子儿茶素与没食子酸酯混合物、没食子儿茶素与没食子酸酯混合物以及儿茶素等不同种类的茶多酚物质与β-葡聚糖的相互作用,发现氧化可提高花青素对细胞壁物质的结合能力,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表现出了较高的亲和力。Wang Yuxue等[12]研究表明,花青素与β-葡聚糖的结合能力与没食子酸的酯化度呈负相关,与儿茶酚的聚合度呈正相关。Tang Huiru等[18]通过研究24 种不同类型的酚类物质与纤维素的相互作用,发现酚类物质的分子质量、疏水性、聚合度与其结合细胞壁多糖的能力呈正相关,并进一步证实了疏水作用在两者相互结合中发挥了作用;此外,还发现没食子单宁与纤维素的结合能力远不如鞣花单宁。Simonsen等[6]研究了21 种香草素衍生物与β-葡聚糖的结合特性,结果表明酚类物质上的糖基很少参与其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当苯环上有一个羟基与醛基形成对位时,这种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结合能力,相反地,引入其他的基团则会降低其与细胞壁物质的亲和力。Wang Yuxue[12]和Phan[19]等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分析了不同类型酚类物质的结合能力,结果表明阿魏酸、没食子酸、绿原酸、儿茶素和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具有相似的结合方式,酚类物质自身带电情况与酚类物质-多糖结合的程度无明显相关性。此外,与羟基肉桂酸和表儿茶素相比,原花青素与苹果细胞壁的结合作用更强。Bautista-Ortín等[20]研究发现,通过向结合有单宁的细胞壁物质中加入花青素可以提高该体系中单宁的提取率,表明花青素和单宁与细胞壁物质的结合是竞争性的。Wang Yuxue等[12]较为系统地研究了36 种具有不同化学结构的酚类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能力,但未发现明显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已有不同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其相互之间可能不具有可比性,因为酚类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能力还与实验所用到的细胞壁多糖种类和结构相关,并且实验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1.3 环境因素对多糖与酚类物质相互作用的影响
酚类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的物质的量比、pH值、离子强度、温度和反应时间等环境因素均可影响细胞壁物质与酚类物质的结合作用,这些环境因素与食品的加工过程和食物在体内的消化过程是息息相关的。
pH值是影响酚类物质与多糖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Phan等[19]发现pH值(3.0~7.0)是影响纤维素与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阿魏酸和儿茶素等多酚物质相互作用的最主要因素,而这一影响又与酚类物质的种类相关。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与纤维素的结合能力随着pH值从3.0升高至5.0而提升,随后直到pH值升高至7.0的过程中两者的结合能力呈下降趋势,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花青素的化学结构随着pH值的变化而改变所引起的。Lin等[21]也发现pH值(2.0~4.5)可显著影响花青素与果胶的相互结合作用,且在pH值为3.6时两者的结合作用最强,而在其他pH值下两者的亲和力相对较弱。Goto等[22]发现,花青素中的醌型化合物更有利于其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且当pH值达到7.0时,花青素更易降解;提高pH值可以增加阿魏酸与多糖的结合能力,但对儿茶素的影响较小。Wu Zhen等[23]发现,在pH值为6.0的条件下茶多酚与燕麦β-葡聚糖的结合能力最强。Le Bourvellec[15]和Renard[24]等发现pH值在2.0~7.0范围内变化对花青素与苹果细胞壁物质的结合能力影响不大,推断离子或静电相互作用对这类分子间相互作用影响不大。总之,pH值对酚类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结合的影响还与酚类物质自身的种类和特性相关。
温度是影响酚类物质与多糖结合的另一个关键因素。Phan等[19]发现温度从4 ℃提高至37 ℃可引起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和阿魏酸两种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能力下降,但儿茶素则几乎不受影响,表明氢键可能参与酚类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的结合。Wu Zhen等[23]发现温度从20 ℃提高至60 ℃,显著降低了茶多酚与β-葡聚糖的结合作用,表明氢键可能参与两者的相互结合。
离子种类及其浓度也显著影响酚类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结合。Le Bourvellec等[15]研究了不同溶剂对花青素与苹果细胞壁物质结合的影响。例如,加入乙醇或二氧杂环乙烷显著降低了溶液的极性,进而扰乱了花青素和细胞壁多糖的结合,表明疏水作用也参与了两者结合;加入尿素可显著抑制两者的结合。因为尿素可破坏氢键结合,由此可推断氢键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Gao Ruiping等[25]发现提高NaCl和乙醇浓度显著降低了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与β-葡聚糖的相互结合,证实氢键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Le Bourvellec等[26]发现,随着离子浓度提升至1 mol/L,苹果细胞壁物质与花青素的结合能力也逐渐提高。Phan等[27]将溶液的浓度提升至0.5 mol/L,发现茶多酚与β-葡聚糖的结合能力降低,表明疏水作用对两者相互结合所起作用有限;在0~100 mmol/L浓度范围内,NaCl对多酚物质的结合能力无显著影响,但这可能是因为该研究涉及的溶液浓度范围相对较小。此外,Gao Ruiping[25]和Le Bourvellec[26]等均发现花青素与苹果细胞壁物质的结合在一段时间内(6 min)就能达到饱和;Renard等[24]则发现在1 h内两者的亲和力无显著变化。
当酚类物质与细胞壁物质结合后,通过改变环境条件可以将其从复合物中释放出来,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对两者结合的影响。Padayachee等[28]将花青素、酚类物质与胡萝卜细胞壁物质结合后,研究了酚类物质在不同条件下的释放情况。结果表明,加入酸化甲醇可以释放30%的酚酸和20%的花青素;与之相比,经过体外模拟胃和小肠消化后,仅有2%的多酚类物质被释放出来,未释放的酚类物质将会进入大肠消化阶段。
2 多糖和多酚物质的相互作用对多酚生物利用及功效的影响
近年来,食品中活性物质的生物利用在食品科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一方面,酚类物质自身理化特征是决定其生物利用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多糖与酚类物质的作用也显著影响其生物利用。
一些研究表明,细胞壁多糖与酚类物质的结合作用会导致其生物利用度降低,即多糖将酚类物质紧紧吸附在其分子上不能释放。Adam等[29]采用Wistar大鼠模型研究了谷物全粉和精粉对阿魏酸生物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阿魏酸在体内可能与阿拉伯木聚糖和木质素等膳食纤维紧密结合,导致其生物利用度降低,但通过破坏麦麸结构可提高阿魏酸的释放率。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增加多糖可以提高酚类物质的摄入量。例如,Schramm等[30]研究表明,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可显著提高黄酮的生物利用度,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碳水化合物对胃肠消化阶段中生理特征的影响或者通过激活了碳水化合物-黄酮载体而引起的。
多酚物质与细胞壁多糖类物质紧密结合后,其生物利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从多糖物质中的释放率,而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包括多酚物质的自身结构、多酚与多糖的结合方式及紧密程度、外源酶的作用等。那些经历胃肠消化过程后未被释放的酚类物质,也对人体健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酚类物质与多糖的相互作用在大肠消化阶段具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例如,酚类物质可通过这些结合体运载抵达大肠,进而在大肠的复杂酶系和菌群的作用下被释放[30]。
细胞壁多糖和酚类物质在有蛋白质存在的情况下可形成聚合物,这3 种物质的聚合也会影响酚类物质的生物利用度。例如,Oliveira等[31]研究发现果胶和β-乳球蛋白可与花青素-3-葡萄糖苷或儿茶素形成共聚物,并通过体外胃肠消化模型的验证发现,这种共聚物的形成可提高酚类物质的生物利用度,而且这种共聚物的形成会受到pH值、温度和离子强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能抵达大肠消化阶段的酚类物质,主要是在胃肠消化阶段未被小肠吸收的酚类物质或与食物中大分子物质紧密结合的酚类物质。多糖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载体,同时还能有效阻止消化过程中酶与酚类物质接触,有利于其被运送至大肠消化阶段[32]。事实上,诸如多糖等许多细胞壁大分子都起到了食物中抗氧化物载运体的作用[33]。Tuohy等[34]综述了包含整体植物组织的食品、酚类和膳食纤维等不同物质对大肠微生物菌群的影响,许多研究证实大量酚类物质在大肠消化阶段被释放出来并参与代谢,这些酚类物质将进而影响肠道生态;例如,通过发酵黑麦、小麦或燕麦麸皮,可破坏其细胞壁结构,促进了酚酸的释放,增强了微生物对酚类物质和膳食纤维的利用效果,而这种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酚类物质的代谢。Rosa等[35]发现小麦糊粉层中的酶解也有利于酚类物质的代谢。酚类物质在大肠中的代谢物常具有抑菌、抗炎症、解毒和植物雌激素等活性[32],也与糖尿病、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密切相关[36-37]。结合在膳食纤维上的酚类物质可增加脂类、蛋白质、水分和排泄物的量,同时对脂肪代谢、降低总胆固醇、降低血液中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水平等都有积极作用,并能提高肠道内的抗氧化水平,这对人体健康具有积极的意义。
3 多糖和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对食品加工的意义
多糖和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对一些食品品质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酿酒和果汁加工中,细胞壁多糖和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与酚类物质的含量密切相关。一方面,酚类物质与果蔬皮渣中的细胞壁物质紧密结合而不能进入食品体系中,将导致酚类物质在加工过程中大量损失[26,38]。由于酿造过程中酚类物质与细胞壁物质紧密结合,在发酵后的葡萄酒中仅残留25%的原花青素,而葡萄籽和酒渣中则吸附了48%的原花青素[39]。Hanlin等[39]研究表明,分子质量较大的原花青素更容易与细胞壁物质结合,这也解释了葡萄酒中为何缺失了那些原本存在于葡萄中的分子质量相对较大的原花青素类物质;另一方面,在加工过程中,食品中的酚类物质还会因氧化或者其他环境因素发生降解,而其与细胞壁物质结合可降低酚类物质的降解率。Buchweitz等[40]研究发现,向草莓酱中添加果胶可显著提高体系中花青素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与细胞壁物质、多酚的种类及多酚的结构相关,表现在添加苹果和甜菜果胶可以提高花青素的稳定性,但添加柑橘果胶则无这一效果。此外,虽然加入苹果和甜菜果胶可提高原花青素的稳定性,但这两种果胶的添加却对天竺葵-3-丙二酰葡萄糖苷没有作用。Bourvellec等[41]研究发现,细胞壁多糖与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也与桃罐头的粉红色消褪有关。即桃中的原花青素降解成花青素后与细胞壁多糖结合后显出的色泽非常稳定,即便在后续的提取和酶解过程中也难以去除,推测这种结合可能与两者间碳原子的共价结合有关。
多糖、酚类物质和蛋白质是食品体系中常见的物质,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与食品品质关系密切。例如,蛋白质与酚类物质的结合及引发的沉淀现象也受到体系中的细胞壁多糖的影响。通常,多糖会降低蛋白质对酚类物质的亲和性,这可能是因为形成了蛋白质-酚类-多糖聚合物,或者是由于多糖结合酚类物质而对它们与蛋白质的结合形成了竞争作用。Oliveira等[42]研究表明,当草莓和酸奶混合后,因可溶性蛋白和酚类物质相互结合,它们的含量均降低;添加卡拉胶可进一步降低蛋白质含量,推测是蛋白质、酚类和细胞壁物质三者相互作用所引起的。Soares等[43]发现果胶、多聚半乳糖醛酸与唾液蛋白、胰淀粉酶、缩合单宁共同形成了多元共聚体,这阻碍了蛋白质和多酚的相互作用。阿拉伯聚糖可与蛋白质竞争性地结合酚类物质,而酚类物质的结构也会影响上述3 种物质的相互作用。例如,多糖对牛血清白蛋白与原花青素结合的抑制作用随着原花青素分子质量的提高而降低,表明增加原花青素聚合度可增加其与蛋白质结合的位点数[44]。Mateus等[44]认为蛋白质种类和结构与上述聚集体的形成关系密切;例如,虽然酚类物质和多糖对几丁质酶聚合的影响较小,但在含有多糖和酚类物质的红酒体系中,酚类物质却显著影响索马甜类蛋白异构体的聚合行为及其聚合程度。
在果蔬加工过程中,可利用多糖和酚类物质相互作用来遮掩酚类物质的收敛作用。Troszyńska等[45]研究表明,多糖和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可以提高物料的黏度,这有利于减轻酚类物质引起的收敛口感。不同种类多糖类物质对收敛口感的掩盖能力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羧甲基纤维素钠、瓜尔胶、黄原胶和阿拉伯胶,且这种效果与多糖的结构关系密切。
酚类物质在人体内的生物利用度一般比较低,可利用多糖与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构建传递系统来调控酚类物质生物利用,例如采用多糖来包埋酚类物质或制备微胶囊。通过这种方式,可有效地将酚类物质与环境隔离,从而保护特定消化阶段中的酚类物质,也可有针对性地控制酚类物质的释放和其生物利用。Liu Jia等[46]研究发现,利用燕麦β-葡聚糖与辛烯基琥珀酸结合制成微胶束系统,可用于对姜黄色素的包埋,包埋后可显著增加姜黄素的稳定性和溶解性。Moonhee等[47]利用麦芽糊精将茶多酚制成微胶囊,发现这种微胶囊的制备工艺明显增强了茶多酚缓解心血管疾病的效果。
细胞壁物质和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还可被用于制备可携带茶多酚的生物载体。Shi Meng等[48]研究发现,大米麸皮可有效结合茶多酚,这一结合过程的热动力学可以用Langmuir和Freundlich模型拟合;纤维素酶、蛋白酶处理、脱脂处理都会降低大米麸皮与酚类物质的结合能力。因大麸皮富含β-葡聚糖等细胞壁物质、脂肪和蛋白质等多种成分,这种结合可能非常复杂。Jakobe等[49]综述了酚类物质与多糖、脂类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认为多糖、蛋白质和脂类物质与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都可影响酚类物质的释放。
4 结 语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关于多糖与酚类物质相互作用的研究,重点分析了影响其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包括多糖与酚类物质的种类、化学结构和环境因素等。多糖与酚类物质可通过多种作用力相互结合,例如疏水作用、氢键、离子键等,二者的相互作用不仅对酚类物质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和生物利用度有显著影响,还对果酒、果蔬汁等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品质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问题尚未研究清楚,例如气体环境及压力等其他环境因素对多糖与酚类物质结合的影响;不同种类多糖物质对结合酚类物质的协同或者竞争作用;淀粉、蛋白质和脂肪等其他食品组分对两者结合的影响;加工方式和加工过程对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细胞壁多糖与酚类物质的相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特别是两者结合对酚类代谢、生物利用度、肠道微生态及肿瘤、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的影响;从机理上认识这些问题对于食品加工和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