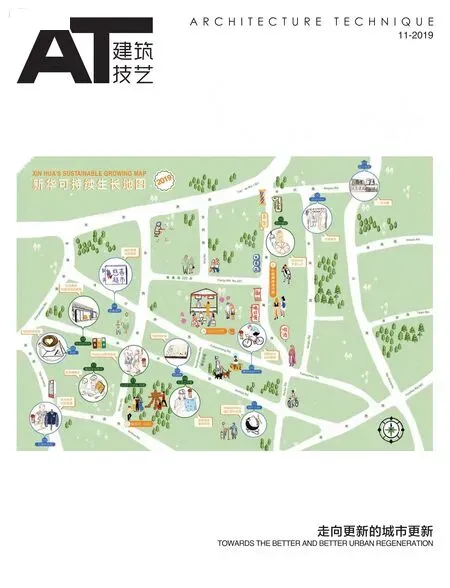高层建筑“空中街道”的公共价值认知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探析
扈龑喆(通讯作者)郑攀 陈泽胤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新长宁集团
高密度城市背景下,“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人们将高层平面不断地向空间复制。在城市空间立体化的过程中,高层建筑“空中街道”是一种常见的有效实现方式(图1)。自它诞生以来一直具有两方面特性:一方面回应了人们在高空中对地面街道生活的社交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作为组织城市高空多维路径的交通方案(图2)。
“空中街道”是高密度条件下城市空间立体化的产物,它所形成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与地面街道相似而又不同的功能、结构与空间元素,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高层建筑单体或群体为实现载体;在本质上表现为组织水平、垂直立体维度的交通;从功能上表现为保持街道活力的复合性,作为“次级地面”承载人们在空中的交往生活;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别于空中平台、空中庭院的连续性路径空间。
当下丰富的“空中街道”现象,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三个历史源头(表1)。可以看到三个历史源头既联系紧密又相互独立,共同影响了当下高层建筑“空中街道”的形式与功能原型。

1 高层建筑“空中街道”形式图解

2 行走城市中的“空中街道”连接
1 高层建筑“空中街道”的公共价值认知
本文重点对“空中街道”的公共价值进行剖析,分析其所面临的挑战及解决之道。“空中街道”的公共价值将通过“从交通到促进交流交往”“提升疏散效率”“增强协同效应”三方面展开。
1.1 从交通到促进交流交往
许多高层建筑“空中街道”的方案在设计之初便把促进交流交往作为重要的社会人文目标,为不同程度的社会往来提供机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并能处于心理自在状态。高层建筑“空中街道”对交流交往的促进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1)多样化功能。“空中街道”根据不同类型往往植入了复合性功能,其中包括相对必要性功能如邮局、办公、酒店、银行,购物(如马赛公寓商业街)等;或提供咖啡厅、展览、阅读等休闲功能(如当代MOMA)等。人们在舒适良好的高空环境中能够自在地休憩、发呆、散步等,与之相伴的交流交往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图3,4)。
(2)多层次空间。优质且成功的高层建筑“空中街道”通过建立不同层次的空间以满足不同交往程度的需要,人们可以更为惬意地选择自己最舒适的社交状态。在很多案例中,交通空间是公共性最强的空间,为点头、打招呼等基本交流提供机会;一侧的休憩空间通过绿化、座椅的限定或围合创造出略微私密的空间,供人们进一步小坐、闲聊,如BIG设计的纽约螺旋塔和萨夫迪设计的新加坡空中居所(图5,6)。

3 当代MOMA 的多样化功能

4 深圳湾超级城市竞赛“空中街道”的多样化功能
(3)适应性空间。众多“空中街道”案例中,通过适宜的坡度(如BIG设计的柏林新媒体中心)(图7)、充足的自然光(如达士岭组屋)、适宜的温度条件(如香港置地广场)、完善的休憩设施(如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等保证了人们使用街道空间的舒适度,愿意在此停留成为其他街道生活发生的前提条件。

5 纽约螺旋塔的空中街道的多层次空间(BIG 设计)

6 新加坡空中居所的空中街道的多层次空间(萨夫迪设计)

7 柏林新媒体中心的空中街道的适应性空间(BIG 设计)
1.2 提升疏散效率
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安全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高层建筑最重要的问题,其中疏散系统——集中于像电梯和楼梯这样垂直的疏散系统更是其中的关键[1]。
1.2.1 借助高层群体“空中街道”疏散
在形式上,群体式水平“空中街道”即为多个高层在空中进行一个或多个层面的水平连接。在本质上,这给某高层内的人群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多个疏散出口,也有利于减轻只有单一疏散方向情况下的路线拥堵问题。瑞典隆德大学的消防工程系Egazon Haliti对高层群体的多层面水平连接对疏散效率的提高进行了数据模拟[2],数据显示全部使用天桥疏散所用的疏散时间最短。因此,水平“空中街道”的使用有助于整体疏散时间的缩短。
1.2.2 借助高层单体“空中街道”疏散
垂直式“空中街道”所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从疏散的角度讲,由于道路的宽度不同、所用的行进手段(坡道、楼梯、自动扶梯等)不同、空间形式不同,很难抽象成固定的模型进行研究。但在紧急情况下,实质上也是增大了垂直疏散面积,提供了新的疏散路线。因此,水平式“空中街道”有助于疏散效率的提高,同时一定程度解放了高层建筑的高度设计上限,因为垂直式“空中街道”则能够提供新的疏散路径。
1.3 增强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本来是一个经济学词语,这里借用来描述“空中街道”使得高层群体间或者高层单体各功能通过资源共享、互补从而相互增强并获得“1+1>2”的效果。下文将通过“物”与“人”两方面的协同进行阐述。
1.3.1 物的协同
公共设施方面:如前文大量案例所提到的,植入高层的公共设施常包括图书馆、健身房、小商店、咖啡厅、小花园等。连接起高层群体的“空中街道”,对于减少单幢高层公共设施的数量、提高公共设施利用率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通过“空中街道”实现了各高层物理上的互通之后,这些设施实质上实现了资源共享,需要某种设施的人们可以轻松通过“空中街道”前往其他高层进行使用。当代MOMA 和达士岭组屋都是很好的例子(表2)。
1.3.2 人的协同
办公协同方面:不管是高层群体之间还是高层单体,“空中街道”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办公协同提供或增强了物理联系,原先不在同幢高层之内或被楼层分隔开的不同公司、不同部门能够在这一包容性的公共空间中得以组织、整合并进行互动,激活创造力,点燃活力。
商业人流方面:“空中街道”对于商业高层的整合作用尤为明显。通过“空中街道”系统加以整合之后,对市民来说极大地提高了可达性与便利度,吸引了比原来单个商业单元所能吸引的更多人群数量,将为每个商业单元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香港中环的“空中街道”系统连接了12个独立主要商厦,超过44 500m2办公或零售面积,服务超过四万名上班族,为集体零售网络吸引了大量的人群[3](图8)。

表2 “空中街道”物的协同(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8 香港中环“空中街道”网络使商业能够整体协同
2 高层建筑“空中街道”所面临的挑战
从高层建筑“空中街道”的定义可知,“公共性”是“空中街道”很重要的一面,是高层建筑“空中街道”产生公共价值的先决条件。然而,历史上或当今的高层建筑“空中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价值实现仍面临着多种问题和挑战。
2.1 功能、管理导致的公共性缺失
管理部门为了保证人们能够恰当地使用高层建筑“空中街道”,避免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和来自其他使用者的控诉,以及安全问题(禁止不良分子进入),往往对这些空间的使用主体(被选择的使用者)和使用方式(住区守则、开放时间等)加以严格限制。
因此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许多“空中街道”呈现出两难的局面:它们有着良好的物理状态,却没有人气、死气沉沉,与地面街道的生动景象有天壤之别。在笔者对于达士岭组屋和当代MOMA的探访中,“空中街道”的使用者寥寥,与生动的街道生活场景还有一定距离(图9,10)。
严格的使用条件也限制了人们社会交往权利的行使,不利于邻里凝聚力与场所感的培育与营造。这一切都需要对当代高层建筑包括“空中街道”在内的公共空间管理模式进行反思与创新(表3)。

9 达士岭组屋通过26 层门禁选择使用者

10 当代MOMA 无人的“空中街道”

表3 达士岭组屋“空中街道”被限制的行为
2.2 方案设计导致的公共性缺失
“空中街道”公共性缺失的另一个原因是,设计上留出的城市接口不足,无法引入城市人流。一方面管理上的原因使设计抹杀了这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单一的建筑内部人流又无法支撑起空间的复合功能,导致营运困难,进一步让“空中街道”作为公共空间衰败下去。如果没有明确目标,城市人群一般不会通过电梯等封闭式垂直交通前往,无法自然地引入更高层面的空中街道,因此中高空层面的高层建筑“空中街道”先天不足,很难获得持续的人流来源,以维持足够的街道活力(图11)。

11 高空层面“空中街道”往往接地性不足
3 高层建筑“空中街道”成为有效公共空间的必要条件
高层建筑“空中街道”作为公共空间,满足了功能内容要求之后,仍需要一系列其他必要条件,公共空间才是有效成立的,其公共价值才能够最大化得以体现(图12)。恰当的管理、可持续的运营以及良好的设计是不可缺少的三个必要条件。

12 “空中街道”成为有效公共空间的必要条件
诚然,用“空中街道”构筑未来垂直城市的愿景是很多建筑师的梦想,然而100多年前针对纽约城那些疯狂的幻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实现。纵然建筑师有着对“空中街道”明确的价值认知,但在各方面挑战的压力下有着各种现实的妥协。高层建筑“空中街道”从纸上到现实的跨越到今天仍然任重而道远。然而,随着未来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远见和视野的扩大,加之运营管理等的日趋成熟,高密度城市空间立体化进程将逐步推进,高层建筑“空中街道”有望伴随实践而成熟,相信这些挑战会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