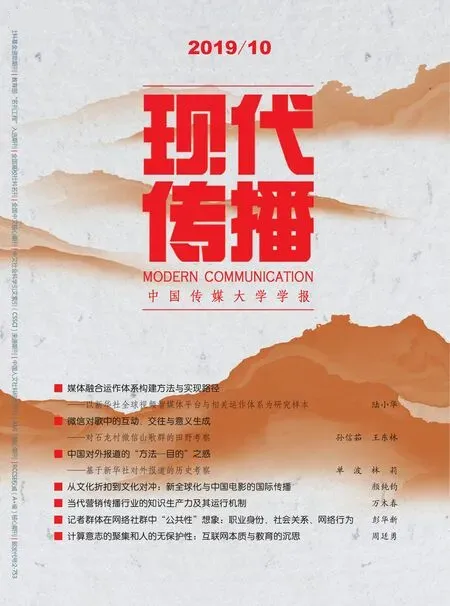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功能维度与中国形象的传播*
■ 樊小玲
国家形象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学、国际关系、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研究。中国形象是国家形象具象化的观照。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无论是对中国形象叙事模式或是传播策略的思考,还是对“中国”这个想象共同体的传播进行历史向度与当代维度的重现与解析,再或是对全球化新语境下中国形象传播进行的系谱性的考察,几乎都集中于大众传媒这一媒介。这使得中国形象及其传播研究长期以来无法摆脱被妖魔化、被误读的困境及由于话语权缺失而引起的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错位、疏离与无力的问题。如何重构中国形象传播这一命题,如何在西方强势话语中突破当下的困境,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而从话语实践角度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中中国形象传播的再思考则是本文研究的突破点。我们试图从话语实践构建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对汉语教科书功能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将教科书话语实践进行维度划分,从不同维度出发探讨汉语教科书在中国形象塑造与国际传播上的可能性路径。
一、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脉络与困境
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池田德真对“战争宣传中构建的国家形象对战争进程影响”的研究,之后随着国际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的深入而逐步发展。摩根索(Hans,J.Morgenthau)(1955)对“威望”的描述,大卫·佩里(David Perry)(1987)的“国际新闻对受众心目中相关国家形象影响”的研究,赫尔曼(R.K.Herrmann)(1988)的“形象理论”,约瑟夫·奈(Joseph Nye)(1990)的“国家声誉”,亚历山大·温特(Aleksander Wendt)(1999)的“自我和他者的观念”等在本质上都是对国家形象的研究。
在国家形象研究的演化脉络中,国家形象曾作为“信念体系”、“心理认知”、代表具体的国家“意向”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1962)、阿尔伯·拉什(Alpo Rusi)(1988)、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1989)等人的论著中出现。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到吉特林(Todd Gitlin)(1980)、罗伯特·阿尔伯瑞顿(Robert Allbritton)(1984),再到张昆(2007)、程曼丽(2008)、黄敏(2009)、姚君喜(2010)、李智(2011)、周萍(2014),这些研究者们采用框架、议程设置、构建理论、话语分析模型等理论就大众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形象是国家形象具象化的观照。对于中国形象,美国智库(Think Tank)、英国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以及其他的国外学者都有过非常多的研究。在我国,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发于90年代,兴于2006年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涌现出大量丰富的关于中国形象研究的成果。
纵观这些年来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从传播的方向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形象的国内传播,研究者有沈晓敏(2010)、吕梦含(2016)、张鹏、吕立杰(2017)等,这一类研究的共同关注点为在国内传播中如何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使整个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产生紧密联系。
另一类则着眼于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又可细化为两类:
一种是对中国作为异国形象在世界各国中呈现出来的文化镜像的研究,也就是中国形象的“他塑”研究。代表性研究有: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1972)、苏尚明(1986)、史景迁(1990)、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8)、马丁(David Martin Jones)(2014)、谭建川(2014)、詹德斌(2014)、王寅生(2015)、蒋柳(2015)、刘菊凤(2015)等。这些研究的共同关注之处在于:异国文化体系中形成了何种中国形象;这样的形象是如何生成的;作为“他者”,在他国自身文化定位以及作为别国自我确认的想象资源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在别国的思想演化过程中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
另一种是对中国作为自我形象的塑造者,向他国所传递的国家形象的研究。代表性研究有张昆(2005,2008)、程曼丽(2007)、孟建(2008)、吴友富(2009)、胡晓明(2011)、戴长征(2014)等。以上研究的共同关注之处在于:在国际话语构建中,中国用何种方式进行“自我形象”的定位,又应该如何审视跨政体、跨意识形态、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如何打破西方话语垄断,通过何种方式强化国家形象构建的话语权,从而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塑造与传播中国国家形象。
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中国在国际局势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在以上这两种研究中,学界对后者的关注尤为凸显。
综上,当前丰富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学界对于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积极观照,而看似纷繁的研究表象却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研究的复杂性。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可发现,尽管研究中使用方法多样、分析角度不同,但中心议题的设置大都集中于大众媒体,即中国形象传播的“媒介中心论”取向明显,而这样的取向所形成的解决路径显而易见会因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在大众传播中“被塑造”的不利境地和局限性影响到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从而令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研究陷入困顿的境地。那么,如何在大众传媒之外寻找新的传播载体与空间,开拓多渠道、多角度的研究路径成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汉语教科书则可作为中国形象传播的突破口,对其进行研究也许可拓展中国形象传播的载体,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开辟新的可能。
二、作为话语实践的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形象
1.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形象
“在国与国之间,教育是一种建立持久联系、发挥长远影响的方式,是发展国家间长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①汉语国际教育是使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社会的整体认知产生紧密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②“当世界各国会说汉语的人数普遍增加到百分之五,中国在国际上的安全系数、形象系数、外交系数、亲和系数都将大大提高。”③如此,汉语国际教育和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是中国形象发挥持久、长远影响的方式。胡范铸(2014)指出汉语国际教育应为“国际理解教育”,其“直接目标是汉语能力获得,而根本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共享,即实现中外社会互动”④。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汉语教科书作为教育内容的具体表现,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进行交往、沟通的中介。它不但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意识形态的体现”⑤;它不仅是知识的集合、“事实”的传输系统,还能体现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生活场景、精神面貌与文化传承。因此,汉语教科书是“中国形象”极其重要的叙述者和载体(樊小玲,2018)。
汉语教科书的编写者和使用者带着不同的意图、知识与文化背景在教科书这一载体相遇,构成一种微传播环境与动态空间。在这一空间,“汉语教科书—汉语学习者”共同构建的“文化镜像”集中体现了以中华民族这一群体的自我认知、文化表征为特点的“中国形象”;而面向不同国家的汉语教科书则体现出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另一民族的文化观照。在汉语教科书中,共同的背景知识与公共文化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交流和沟通的共同参考,而差异性则为在“分享一种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情感共同体,在促进全球大多数的民众建设性接触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文化主义”⑥提供了可能。
2.作为话语实践的汉语教科书
话语实践一词的最初使用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中对于话语和话语实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不是表达,也不是推论,更不是观念产生的过程。他将话语实践看作是一种规律,这种整体性的规律是匿名的,存在于历史之中,在具体的实践和空间中才能被确定,“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⑦。话语实践不仅在各领域之间建立起关系,“也反过来改变着它将它们之间建立起关系的那些领域”⑧。
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将社会空间看作是话语空间,他们认为存在“话语性场域”——一个不确定的差异流,“在这个场域上,既没有总体的内在性,也没有总体的外在性,社会是被建构的”⑨。
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则认为“社会实践有各种方向——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也可以在任何方向都未被还原的情况下被包含在所有这些方向之中”⑩。他认为话语实践作为一种特别的社会实践,作为一个中心节点,连接着文本与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可以再生产已有的话语结构以维持现存的社会身份、关系和知识信仰体系,还可以通过创造性地运用结构之外的语词来改变话语结构,从而改变原有的社会关系、身份和知识信仰体系”。
若把汉语教科书当作一种话语实践,便可这样重新审视汉语教科书: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中最直接的工具和手段,汉语教科书这一话语实践连接着汉语教科书中的文本与社会实践,教科书的文本便是承载汉语这一种语言学习系统的词汇、语法、课文、练习的载体,而社会实践则不仅仅是汉语学习者汉语知识的获得、汉语能力的提高和汉语水平的变化。进一步,教科书的话语实践还构建着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及汉语使用者这一群体的认知、情感、态度以及对汉语学习者所属群体与汉语使用者所属群体之间关系的认知。
与此同时,教科书语言秩序同其他社会语言秩序一样,被建构为一个市场,在市场里文本像商品一样得到生产、分配和消费(费尔克拉夫,1995)。通过教科书呈现的内容和形式,我们不但可以看出现实世界是如何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出浩如烟海的“知识”是如何被选择和组织的。通过选择,“某一人群的文化资本获得了合法地位,而另外一群人的文化资本却无法获得这样的地位”。由此,汉语教科书文本的内容,除了语言知识的意义之外,还有更加深层的文化资本的意义之所在:内容是谁来选择的,是如何被选择的,是怎样来选择的,这些通过汉语教科书这一话语实践都将对社会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教科书的话语实践具有“弱化实施者与动机的类科学叙事模式及缺乏作为互动成员的直接合叙者的特点,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在极大程度上被客观化和权威化,从而对学习者有直接的、显性的、强制性的影响”的特点,这使得汉语教科书在“中国形象”这一社会实践的构建中,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
三、知识·关系·价值: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三个维度
话语实践对于社会实践的建构效果源于话语的三种功能:身份功能、关系功能和观念功能(费尔克拉夫,2003)。“话语的身份功能指的是关涉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从而建构参与者的‘社会身份’‘主体’‘主体地位’、各种类型的‘自我’;关系功能指的是关涉话语参与者的关系如何被制定和协商,从而建构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话语的观念功能关涉文本说明这个世界过程,实体和关系的途径,从而建构参与者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当我们把汉语教科书看作一种话语实践,那么就可由话语建构社会的三种功能出发,将汉语教科书对社会实践的构建划分为三个维度:
1.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语言知识的维度
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这一维度与话语的“观念功能”中的建构参与者“知识体系”的功能直接相关。
“语言学习不仅是个体行为的结果,更在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能为其提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各种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学习者对语言学习进行‘投资’的各种回报。”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汉语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的最大、最直接的“可能性”与“资本”就是语言知识的获得。因此,作为以汉语教学为直接目的的国际汉语教育过程的载体,语言知识的维度便是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最为直接、最为基础和最为前景化的维度。这一维度属于语言体系的维度,包括汉语的语音系统是怎样构成的,声母、韵母、声调是如何组合发声的,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如何,汉语的汉字系统是怎样一种音形义的结合体。这一维度的话语实践帮助(再)生产的社会结构实践为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这一语言的认知层面及用汉语进行交际的习得层面。通过汉语教科书了解汉语是怎样的一门语言,以及如何用汉语这套语言系统进行表达和沟通,即具有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汉语教科书这一维度也是多年以来汉语教学界最为关注的维度。不仅如此,这一维度的话语实践还会对汉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造成影响,随着对汉语语言系统的不断了解,汉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汉语学习者对于汉语的亲近感乃至于对于使用汉语的人和汉语社会的亲近感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发现虽然上文中诺顿(Norton)的“投资”是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的,但其实为学习者提供各种“可能性”的社会也同样是语言学习这种“投资”回报的接受者。这也是话语实践对社会结构实践重构的结果。
2.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社会关系的维度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86)把社会环境比喻为市场,这一市场由话语实践构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不同形式的资本流通其中并在某些条件下互相转换。社会中的个体通过话语实践获取文化资本,再经由文化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以便使自己在群体中的归属和地位得以确定。教科书作为典型的被授权和合法化的文化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极大的价值。通过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教科书编写者是如何将自己的看法根植于外部世界从而构建社会关系的,即教科书如何通过话语实践重塑文化资本,更进一步说是话语实践如何通过重塑文化资本从而构建和重构社会关系,这也是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第二个维度。
在这一维度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身份功能和关系功能的构建上,即建构参与者的“社会身份”“主体”“主体地位”、各种类型的“自我”及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正是通过话语的身份功能来构建各种群体的身份,特别是“中华民族”这一群体身份,通过命名、描述、特征化等方式,定义、塑造和构筑“我们是谁”“我们的典型成员是什么样的”“我们群体的典型特征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基础性文本是什么”“我们的英雄是什么”“我们的象征是什么”等与历史、特性和界限相关的要素。
社会关系的功能有两层含义,一为某一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二为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本文中这个层面只侧重于前者。在汉语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体现“中华民族”这一群体内部关系的文本,这些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可以通过话语的指示性、定位和范畴化、评价等指标来揭示。对这些文本进行(但不限于)以上指标话语分析就可以看出在汉语教科书中关涉话语参与者的关系是如何被“制定”和“协商”的,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被构筑的:我们的社会有着怎样的构成,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有着怎样的身份定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何种话语方式呈现(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邻里亲戚之间、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等等)。
由于汉语教科书的直接目的是提高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水平,因此社会关系维度的话语实践及对于社会实践的构建功能通常或是被忽视,或是被简单归纳为文化教学要素,缺乏深入研究。
3.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价值体系的维度
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的第三个维度——价值体系的维度与话语“观念功能”中建构“信仰体系”的功能有关。教科书话语实践的这一维度体现的是话语在构建“观念”“价值”“信仰”等方面的作用及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作用。
利洛夫(Alexander Lilov)认为,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不再具有封闭性,而是具有对话性。文化对话不限于文化艺术上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促进,还涉及各国人民的语言、传统、宗教、精神和价值体系。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70)也曾指出每个世界体系的价值观和基本规则会织成一张网,形成用来区分这个体系和那个体系、“我们”和“他们”的一些文化标准,用来区分的不是政治标准而是文化-文明的基础。“地缘文化被视为和平的地缘文化,抑或被视为相互依存和集体安全的地缘文化,更准确的特征是理性的地缘文化,包含和平相互依存以及其他因素”。“汉语国际教育是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造就国际社会互动的重要力量”。阐释自身的观念、价值与信仰体系,再现他者世界的观念、价值与信仰体系及阐明二者相似或相异的信仰体系的这一系列的话语实践的过程就是构建新的地缘文化的过程,这些都可以在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对社会实践的构建过程中进行审视。
在汉语教科书特别是国别化教科书中,不仅有体现“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文本,更有体现中国与他国在文化、历史、传统和习俗等方面进行比较的文本。这些观念、价值与信仰体系的构建过程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方阵聚焦于“指称策略”“述谓策略”“论证手段”“视角化”,或通过“陈述的显性与隐性”“陈述的强化与弱化”等指标来揭示;也可以通过语义结构进行意义和参照的分析,包括“预设”“情态”“施事”“话题”“焦点”等,或通过形式结构如“超级结构”“视觉结构”“声音结构”“限定性表达”“修辞策略”等来揭示。在我的观念里“他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的,“我们是如何看待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是如何区分这个体系和那个体系”的,“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标准的态度”,等等,对这些文本进行(但不限于)以上指标的话语分析便可看出在汉语教科书中“自我”与“他者”的再现和重构,可以看出每个世界体系的价值观和基本规则是如何在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中被制定和协商的,新的地缘文化是如何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磋商和建构的。
四、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中的“中国形象”:再现与重构
若我们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角度来看待汉语国际教育,将其根本目标看作是实现文化的共享,即实现中外社会互动,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构建社会实践的意义便落到如何通过话语实践构建中国形象,达到促进其他国家和民族对我们的理解进而促进沟通交流的层面。
依据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三个维度,对我们教科书话语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可得出在三个维度展开的中国形象:语言文字维度的中国形象、社会关系维度的中国形象和价值体系维度的中国形象。
1.语言文字维度的中国形象
这一维度的中国形象是依托于汉语语言系统和汉字系统展现出来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语言系统本身以及基于语言的“概念元功能”,关于“中国”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具象化的描述体现了何种中国形象。
2.社会关系维度的中国形象
在这一维度则要关注在汉语教科书中,汉语教科书的编写者通过什么样的话语模式对“中国人”进行了何种“身份构建”:如何进行自我“定位”、自我“描述”、自我“特征化”、自我“范畴化”,又通过何种话语模式,对中国社会中“家庭关系”“社会阶层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等关系与社会行为进行话语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汉语教科书展现出了何种中国形象。
3.价值体系维度的中国形象
在这一维度,我们要关注汉语教科书的编写者是否把“中国”放置在一个宽广的“全球”语境中,又如何在“全球”语境中再现自我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如何通过话语实践表达对世界上的不同体系、不同文化标准的态度,又如何对“自我”与“他者”的价值体系的关系进行话语重构,在建构新的地缘文化过程中构建“世界中的中国”的形象。
我们对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中中国形象不同维度的解析正与美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化三分法相契合:语言文字维度的中国形象属于器物文化的层面,社会关系维度的中国形象可归属于制度文化的层面,信仰体系维度的中国形象则可归属于观念文化的层面。若从这三个层次对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加以分析,不仅使得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具有可把控的切入点,并且使得国际汉语教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研究具有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与展开的路径。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重构话语实践,重铸说者的身份,改变中国形象被塑造的局面,建构、传播可形塑语境的中国形象,进而探讨建构新地缘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中的中国形象”传播的可能性路径,那么,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也便有了在角度、方法与路径上突破的可能。
五、结语
当我们把汉语教科书看作一种话语实践可发现,汉语教科书话语有构建社会实践的功能。被构建的社会实践不仅仅包含汉语学习者汉语知识的获得与汉语交际能力的提升、语言情感和语言态度的变化,还包括“中国自我身份”“中国的社会关系”以及“中国与他者的价值体系”。而“中国自我身份”“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国的价值体系”都是构成中国形象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涉到中国形象的塑造、传播以及中外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由此,我们可以对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不同维度中的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进行探究,进而探讨如何通过重铸说者的身份、重构话语实践,建构和传播可形塑语境的中国形象,拓展新地缘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中的中国”形象传播的可能性路径,从而实现中国形象传播研究在角度、方法与路径上的突破。

图1 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不同维度中的中国形象分析方法与构建路径
注释:
① [美]约瑟夫·奈:《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②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曾说过:“教育是推进同一种认知在更多的‘同质人群’中延伸、扩大,从而与整个社会的整体认知产生紧密联系的一种方式。”转引自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③ 金立鑫:《试论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家策略和学科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④ 胡范铸:《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新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⑦⑧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0、93页。
⑨ 朱彦明:《话语实践与激进政治: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云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