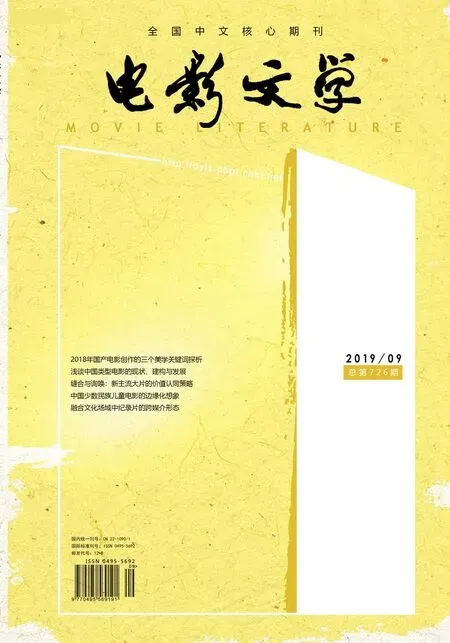论伪纪录片追求“真实”的双重向度
——以电影《明月几时有》和《黄金时代》为例
马权威 (南阳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
“伪纪录片”作为一种亚类型电影,其名称最初有多种描述性的表达,如“psuedo-documentary”“flak-documentary”“fiction documentary”。但是,“伪纪录片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始于1965年剑桥英语词典收录的mockumentary一词”[1],这意味着伪纪录片作为真正独立的一个亚类型命名的存在。实际上,伪纪录片的实践早在1964年理查德·莱斯特的《一夜狂欢》中就有了成功的典型尝试。该片融合了喜剧片、纪录片与摇滚乐的虚假剧情片,上映后大获成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所以,才有了1965年剑桥英语词典的收录。“1984年,好莱坞的一个新导演罗伯·莱纳(RobReiner)为他的处女作《摇滚万岁》做宣传时,在媒体面前特别强调该片是采用 ‘mockumentary’的方法来拍摄,直接推动了‘伪纪录片’概念的传播。”[2]因此,可以看出,伪纪录片概念实际是从最初形式的维度对影片的一种外在形态的关照,逐步扩展到形式与内容呼应性命名,它利用纪录片常见技法,顺从观众惯常性审美经验,通过形式或片段的真实,逐步建构起具有纪录审美倾向的影片样态。伪纪录的外在形式类型有很多,比如采访镜头的“真实呈现”,故意晃动的虚拟真实的影像营造等,都是伪纪录片常见的外在类型样态。而本文主要所讨论的是利用人物扮演的方式或者面对镜头的采访形式。“伪纪录”的人物采访方式,在许鞍华的电影中已不是首次尝试,她曾在《投奔怒海》中就曾以一个摄影记者的视角作为贯穿线索叙述影片。然而在《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中的对镜陈述的采访,都是以一个事件的亲历者的视角,采用固定机位,面向镜头现实回忆般地进行陈述,极大地拉近了观众的现实距离。两部作品都通过纪实采访营造虚构的真实,同时又通过精彩的情节和细节深入事实的内涵,进而实现真实地营造故事讲述的语境真实,在营造的语境真实中塑造人物、铺陈故事。但有所不同的是,《黄金时代》里的伪纪录采访因叙事线索和人物的复杂,常给人以故意出戏的虚假之感,而《明月几时有》中的回忆式伪纪录采访更能让观众进入到故事的讲述之中,但我们不能将此作为两部影片孰优孰劣的评价指标,而更应分析其背后潜在的一般规律和独特价值。
一、伪纪录的形式期待与“艺术真实”的直觉建构
人类无论观看戏剧表演,还是阅读小说,抑或是听音乐看电影,总会注意到艺术形式的存在,并且在潜移默化中会受到其影响,形成了形式的期待。姚杰在《艺术概论》中指出,“形式期待是指欣赏者由作品的类型或形式特征引发的期待指向”。[3]从宏观层面来讲,各种媒介形式都可成另一种媒介形式的叙事手段或叙事方式,在叙事中观众会自觉地形成对另一种媒介的形式期待。在微观层面,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叙事或表达的手段,每一种表达手段都会对观众形成期待,这是形式期待的第二个层面。对于形式期待来说,不仅包括形式的客体,还包括还是期待的主体即受众的心理。受众之所以对形式有所期待是因为,期待形成于以往的艺术经验和生活中。在观看作品时,观众将以往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充分调动形成期待。采访镜头是纪录片或者电视纪实节目在再现性影视作品中常用的惯用手法,它往往能够让观众通过观看采访,回忆起以往的真实,进而采访成为呈现真实的有效手段。因此观众在看到采访镜头时能够联想到影视作品的纪实性或叙事的真实性。《明月几时有》和《黄金时代》均采用了这种伪纪录式的采访镜头,通过扮演的演员之口,以亲历者的身份,对着镜头的采访讲述,以此种形式构筑起“艺术真实”的外壳,形成了“艺术真实”的直觉建构机制。
《黄金时代》以民国时代为背景,讲述了女作家萧红传奇的人生爱情故事。影片以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为基本线索,以萧红自己撰写的多部作品中的细节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作家或亲属等的共述为印证,采用传记、回忆录剪裁拼贴而成,艺术地运用旁白、独白、对镜采访等形式艺术多元地真实呈现了萧红的一生。在这部电影中,大量地采用了伪纪录的采访镜头形态,让当时的当事人讲述萧红一生中的传奇情节和细节。当事人的叙述以萧红一生中生存空间的转移为基本线索,把其弟弟、舒群、蒋锡金、张梅林、胡风、梅志、聂绀弩等人的采访,采用多点共述的伪纪录采访镜头形态,搭建影片形式逻辑上的艺术真实,在多人的陈述中尽力还原萧红一生中的人和事,将萧红一生经历的逃婚、弃子、逃难以及与萧军、端木、骆宾基等人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都予以了呈现。整部影片的人物口述,形式上大部分采用了亲历者的视角予以回忆,比如其弟弟回忆了她逃婚的事件和会面事件。舒群回忆了其逃到哈尔滨初期居无定所的情况。白朗和罗烽回忆了她在旅馆的日子以及和萧军相遇的情况。聂绀弩回忆了萧军萧红二人分离的事件。蒋锡金回忆了他们初到武汉的情况以及后来萧红的离开。这些回忆叙述,实际是在这些人或者其他人的文章出现的影像化真实的呈现。一方面导演努力通过这些人的伪纪录式的采访尽力还原萧红的故事,真实地营造叙事的真实,建构起基本的艺术真实逻辑。另一方面导演还尝试将文学作品以及回忆录的语言,直接用在了电影的对白中,努力呈现出其具有的文献记录价值,建构起基本的“艺术真实”直觉感知体系。
《明月几时有》以“东江纵队”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以真实人物小学教师方兰、游击队长刘黑仔、李锦荣等人在日军占领的香港,讲述了他们如何营救转移文化人的抗日故事。导演通过对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开展大营救的史实,以细腻的女性手法,从香港抗战的小切口入手,管窥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宏大画卷,表达了导演对当年那些平民英雄们的史诗性赞美。
这部影片也采用了倒叙、插叙回忆相结合的伪纪录采访方式,在影片的开篇、结尾以及发展中都采用了扮演的游击队成员老年彬仔口述方式,努力真实地营造影片的叙述语境。在开篇的讲述中,老年彬仔讲述了游击队的任务。接着影片围绕刘黑仔展开了叙述。在影片的发展部分,老年彬仔交代了自己最初在东江游击队的任务,以及与方老师他们的情感故事。在随后的故事讲述中,围绕方老师、方老师的母亲等人的故事逐步展开,逐步呈现香港普通百姓的抗战故事。在影片结尾的采访,许鞍华的提问交代了当年参加东江游击队的现在只有彬仔一个人了,这种看似客观的呈现,让影片建构起了艺术真实的感知体系。
二、伪纪录形态与可能世界理论中的真实观念
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世界可能理论提出者,认为“世界是可能事物的组合,现实世界就是由所有存在的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一个最丰富的组合)。可能事物有不同的组合,有的组合比别的组合更加完美。因此,有许多的可能世界,每一由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就是一个可能世界”。[4]当形式的真实遭遇故事的虚构与导演将与呈现真实的时候,一个可能的世界就诞生了。但是,这个艺术的可能世界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想象性的。它往往以作者强大的创作想象力为成长的基础,又发展在艺术接受者的解释想象力之中,这就使得艺术的可能世界更加丰富和多彩,尤其是可能世界的真实性就更加复杂多变。作为伪纪录片的艺术样态,可能世界的建构不仅依赖于伪纪录形式的真实感觉,更有来自作者想象性的可能世界建构,这种建构既可以依赖于纪录形式的真实,也可建构在形式真实的想象之中。
伪纪录片常常运用讽刺或仿拟的方式来分析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社会事件,遵从人们对于既定纪录范式的认知,引导着观众的思维朝向,并且,也挑战着纪录片核心命题的“真实”观念。童庆炳在其《文学理论教程》中认为“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虽然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型启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生活真实不同于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并表现在假定情境之中”。[5]表现于“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只是导演的手段和工具,而真正的“客观真实”也就是所谓的“生活真实”,往往隐藏于导演的创作动机和初衷之中。因此,这种所谓的客观真实也是不确定的,需要读者的参与才会被唤醒,也就是“真实是需要被揭露的,但如何被揭露,便不仅是形式和技巧的美学问题,同时也是文化、意识形态与商业的问题。并且,什么是真实,同样也是值得质疑与探讨的问题”。[2]在两部作品中,导演都最大限度地调动纪实的手段,极力营造真实的情境与语境,但是二者在观众所理解的客观真实上有较大的差异。
《黄金时代》中围绕萧红创作中的“黄金时代”与社会的时局变化展开恢宏的历史叙事,作品采用了多条线索 ,努力呈现萧红坎坷的真实人生。萧红一生认识过的众人集体出面,他们用往日日常的回忆讲述萧红,这些回忆记录在萧红的小说、文章中,散落在他人的回忆录里,文献的记载中,这些人物采访充满了真实性和荒谬性以及虚幻性,最终在真实营造上影片将虚幻推向混乱而又故作真实的矛盾境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导演认为生活真实是客观的,但又对这种真实充满了怀疑,所以她就用众人之口和伪纪录的形态来表达这种虚假的真实感,她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样的纪实或许根本不存在,进而在影片的主题上对于“黄金时代”产生了怀疑和拷问。
《明月几时有》虽然在形态上采用了伪纪录的采访方式,但相对来讲叙事结构并不复杂。伪纪录的采访仅仅是单个人的视角和简单的镜头组合。导演旨在通过伪纪录的形式告诉观众香港曾经有这样一个群体为抗战而努力的真实故事,即便是结尾处也极富深意与真实。作品中彬仔的主观讲述与影片的客观呈现既浑然一体,又相互联系,让观众能够很好地融入叙事流程,又极具启发意义,做到了间离叙事与流畅叙事的有机统一。
三、伪纪录片追求真实的双重向度
在伪纪录片的形式之下电影的真实首先是直觉层面的感知真实,而理性的真实存在于观众的理性思考之后,是隐藏在作者创作动机和目的之下,它既是观众反思现实生活真实的理性思考,也是导演的原初动机。然而两种真实的构建机制却完全不同,直觉层面的感知真实存在于影片的叙事语境和情境之中,而理性的真实建立在直觉层面的感知真实之上,并形成在观众的观影之后,隐藏在导演的创作初衷之中。这是伪纪录片追求真实的双重向度。我们习惯将“形式”与“内容”视为相对的存在,或者是相对的概念。但这种假设往往忽略了形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往往产生内容比形式更重要的错觉。实际上,主题、故事的内容和抽象的外在形式都属于电影艺术作品的系统,它们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引发观众去期待或推测剧情的发展走势。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候,不但需要连接影片中琐碎的个别元素,而且导演和观众之间会形成有机地互动,形成内容与形式水乳交融性的一种存在。伪纪录片不仅仅作为形式的存在,它更是作者力透纸背真实表达的内容所在。导演通过伪纪录力图实现叙事语境的真实与创作意图所指的现实真实,这是导演实现叙事真实与表达真实的有机统一。
在《黄金时代》里面,时而是萧红对镜头陈述自己的生平,时而是萧军个体书写式的回忆,时而是他人对镜采访式的讲述。观众的叙事视角游走在导演极力用真实手法构筑的伪纪录形态之上,为了真实,导演牺牲了叙事的流畅,故意采用文献记录方式样态,用突兀的外在真实表现导演理想中的“真实萧红”和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进而通过这种真实的形式让观众自己怀疑和思考萧红所处的“黄金时代”。在这里导演表面上是采用一种“纪录”的形态来顺从观众的期待视野,实际上是在解构一个真实萧红和所谓的“黄金时代”,进而在观众的想象性建构中完成一个真实萧红的艺术形象。导演旨在用解构的“真实”唤醒观众创造的“真实”,但因时代的远去,普通观众可能无法创造观看时刻的真实,因此,普通的观众会感受到导演叙述的繁复而无法真正地理解其艺术的真实,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导演追求真实的双重向度诉求,更不影响作品本身在真实创作方面的实验价值。这种实验价值不仅体现在导演对伪纪录形式的娴熟把握,更体现在导演创作初衷和观众观看体验的交流与互通。
与此相反,在《明月几时有》里面,伪纪录的形态却极具代入感,片头部分的交代背景字幕、片中的采访真实可信,伪纪录追求的又具有现实真实的启发意义和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明月几时有》里的伪纪录采访不同于《黄金时代》的用真实的形式去反思真实,而是用真实的形式构造现实真实,这就较之于《黄金时代》里让观众反思所谓众人和文献、文艺作品里的现实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进入情景与角色。
四、结 语
麦克卢汉曾经指出“媒介即讯息”,然而,何为媒介?从传播学意义上来看,媒介是传播或承载物质信息的工具。但媒介也作为一种形式的存在,对于伪纪录片来说,伪纪录的形式本身就是携带信息的媒介。这种媒介成为导演与观众思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和形式。首先在形式上伪纪录片不仅利用外在的惯常形式,创造性地转化为观众的形式期待,建筑起基础直觉层面的“艺术真实”,进而达到叙事语境的真实。其次,在艺术作品的可能世界里,伪纪录片通过真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嫁接侨联,亦可形成了一个可能世界里的“真实”,尽管这种“真实”存在于导演强大的创作想象力和观众作为接受者的解释想象力之中,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真实”,它并不是虚幻的,而是经由伪纪录片外在媒介形式传达而来,但也正是在这亦真亦幻中实现了导演创作初衷的真实。最后,从总体上来看,对于伪纪录片来说,无论是基于形式之下直觉层面的感知“真实”,还是存在于观众的理性思考之后的理性“真实”,都是伪纪录片追求真实的双重向度。这种追求真实的双重向度,对于创作者来说,不能停留在对纪录片直觉层面的效仿,不能简单地将伪纪录片作为纪实的外壳之下的故事述说,而是建立在现有纪录片讲述与观众接受机制之上的一种故事片类型。而对于影片的接受者来说,不管是在叙述语境的“真实”之下,还是叙事事实的不确定之下,认清导演的创作原旨,厘清自己的“真实”认知,便是其中要义。在许鞍华的这两部作品中,伪纪录的采访形式以其自身的形式,在不同的叙述语境中,凭借相同的媒介形式,携带不同的媒介信息,用真实的营造手法营造了艺术的真实,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真实的建构与解构。与此同时,伪纪录的采访形式也是一种观众接受的内容存在,两部片子表面上都是运用纪实的形式,但两者也都将纪实作为一种内容传递的方式,特别是在《黄金时代》中,伪纪录式的采访更是一种叙事的形式和内容。因此,可以看出两部片子伪纪录形态具有一般的意义和典范的价值,为开掘媒介形式的表达带来了崭新的思考空间。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