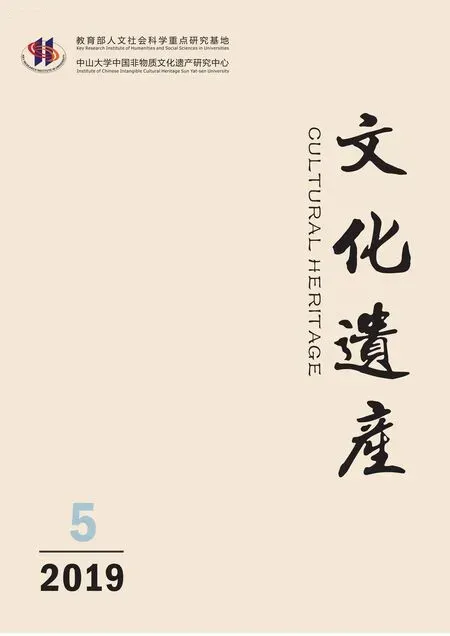论传统技艺知识的模糊性
——以闽西客家大木作“过白”技法的实践为例
欧玄子
引 言
“要想富,一匹布”,是笔者在闽西调查当地大木营造技艺时常听见的一句谚语。它被当地人用来指前后进厅之间的过白尺寸,其字面意思就是想要发财,过白得是一匹布的尺寸,即二尺二分到二尺三分。发财和房子的布局之间显然很难存在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然而,它在实际中却被当地人笃信,并在本地工匠的建造过程中得到普遍遵循。对这一俗信到底该作何解?
一、文献回顾
对于这句谚语的解读,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什么是过白?为何要富就得遵循一匹布的尺寸?
(一)什么是过白?
不论是在多元的南方民居,还是在故宫代表的北方官式建筑中,过白都广泛存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也已有不少积累。1992年王其亨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一文中早已作出较为清晰的解释(1)参见王其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天津大学建筑系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 。,后续有张宇彤对澎湖地方民宅中的“见白”(2)他将见白解释为:由厅神龛的高度(4尺2寸,为定值),自厅内往外看,在庭的檐板与前砖平间需看到天空或其他建筑物。参见张宇彤《澎湖地方传统民宅之营造》,《华中建筑》1997年第1期。参见汤国华《岭南祠堂建筑中的“过白”》,《村镇建设》1997年第7期。、汤国华对岭南祠堂建筑中的见白(3)他将见白解释为:由厅神龛的高度(4尺2寸,为定值),自厅内往外看,在庭的檐板与前砖平间需看到天空或其他建筑物。参见张宇彤《澎湖地方传统民宅之营造》,《华中建筑》1997年第1期。参见汤国华《岭南祠堂建筑中的“过白”》,《村镇建设》1997年第7期。、李秋香对闽粤地区围龙屋的 “望天白”(4)参见李秋香《闽粤围龙屋建筑剖析》,《建筑史论文集》2002年第1期。、程建军对岭南潮汕地区建筑的过白(5)参见程建军《风水解析》,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等研究。在这些过白现象面前,张海滨追根溯源,认为过白“起初由江西匠人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发现并逐渐流传,成为营造风俗中的一种原始风水观念”,后被以杨筠松为代表形势宗所吸收,“以移民传播为基础,以风水观念为媒介,广泛传播至岭南各地,并通过为皇家服务的形势宗风水师廖均倾等,自民间向上影响到了官式建筑的设计”(6)参见张海滨《从“过白”看赣北敞厅——天井式住居类型及谱系流布》,《建筑遗产》2018年第4期。。
这些过白定义基本达成的一致之处是:“白”为站在后进厅某一位置并距离地面某一个高度往前看,前进厅正脊上沿水平线与后进厅前檐下水平线之间所构成的视窗内的天空光,过白为所见到的天空光线照射到视点位置,可见图一。过白这一动词词组在日常中代指可见的天空面积。然而,在具体的视点位置、距离地面高度这两点上却出现了出入,其实这两点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可将问题转换为“到底是什么站在哪里以何为视点”。汤的解释是站在后进纵轴线的拜桌,离地1.2米高处,因为香炉是人间与天上的联系物,过白是人通过神、佛、祖先与天上对话的空间通道(7)参见汤国华《岭南祠堂建筑中的“过白”,《村镇建设》1997年第7期。;
李秋香的说法似乎更贴合“动态的营造”实际。她认为“在上堂的神橱前,地面上有一块“合石”,地理师站在合石上向外望,上堂前檐口和下堂的屋脊之间应该可以见到一条天光”(9)李秋香:《闽粤围龙屋建筑剖析》,《建筑史论文集》2002年第1期。。在民居建造的实际中,许多关键位置的确是由地理师靠人体感知进行操作后确定的,她更明确的说到“那块合石的位置,是由地理师根据主人的生辰八字和流年等确定的,并非到处一样”(10)李秋香:《闽粤围龙屋建筑剖析》,《建筑史论文集》2002年第1期。。因此这个高度,应当是地理师即一个人眼睛的位置。由此观之,之前定义中有些数字看似精准,却恐怕无法贴合变化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汤国华的“纵轴线”说法是非常精准的,因为建筑轴线事关风水,不过其在面阔方向上的定点却与过白控制的高度计算基本无关。由此,建筑学专业中有关过白的定义可概括为:人站在神龛前往前看,所见前进厅正脊上沿水平线与后进厅前檐下水平线之间构成的视窗内的天空面积。
然而,仅有这种学科内概括性的定义依然不够,还需要结合具体地区的实际建造过程进行考量。就闽西地区而言,这里的正脊上檐水平线与前檐下水平线看似精确其实未必,实际操作的工匠和住房的民众说的是下厅的“栋脊瓦”和上厅的“滴水”。建造中正是这块小小的栋脊瓦大大地给了工匠调整过白至于合适尺寸的便利。滴水,其实是说滴水处,是上厅前檐的实际最低处,它本是古代营造实践中的常用参照点。
因此,本文对闽西地区过白的定义为:人站在神龛前往前看,所见前进厅栋脊瓦上缘水平线与后进厅屋檐滴水处水平线之间构成的视窗内的天空面积。
(二)为何要富就得遵循一匹布的尺寸?
实际上这个问题讨论的是数字与建筑功能实现之间的关系,下文将聚焦于文献的解释框架,而非其具体的论据,来谈论学者们对过白存在理由的阐释。仅以汤国华和王其亨这两位比较早期而解释较全面者的说法为代表。
王其亨将过白定义为“处理组群性建筑空间序列,利用近景建筑或其他景物,形成视线方向上的中景或远景画面的框景、夹景”(11)参见王其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第134页。。可以看到他是从建筑相互关系的结构角度,强调过白所形成的空间艺术效果。接着他重点解说了过白的关键是景框的构成和观赏点的确定。在第一点中,他强调框景和夹景构成“过白景框”(12)王其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第134页 。,若是得当则能达到风水形势说的目标。在第二点中,他将过白的欣赏点泛化为“凡与过白的景框构成直接关联的空间序列上的行进起止点、转折点或交汇点”(13)王其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第134页 。,关键在于合宜的视距和视角控制。这样,王的说法可以拆解为三种,一为风水形势说,一为建筑控制说,一为审美艺术说,皆影响深远。直到2018年,赵建波、林小莉依然在用Itti-Koch算法数据来说明过白是“从势的轮廓感知到形的细节感知的转换点,即从建筑各部轮廓的视觉扫描到具体细部的视觉关注的变化点”(14)赵建波、林小莉:《基于Itti-Koch算法的建筑视觉显著性研究——过白的空间分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这实际上是用精细的算法对王其亨的三种说法同时进行了验证。更多的研究偏向于从审美来强调过白的艺术效果,例如党培东认为过白所具有的建筑意义和风水学涵义,在中国画里可称之为“布白”或“留白”(15)党培东:《建筑风水在中国山水画中的应用》,《艺术教育》2018年17期。。
汤国华的过白研究,可视为控制建筑物间距的建筑说、强调“阴阳平和”的风水说、控制厅堂地面泛潮的物理说三者的结合(16)汤国华:《岭南祠堂建筑中的“过白”》,《村镇建设》1997年第7期。,朱瑾、刘晨澍对徽州建筑的构图研究就是延续了汤说法中的前两点(17)参见朱瑾、刘晨澍《徽州建筑的对位构图艺术》,《装饰》2006年第6期。。
综合王与汤的说法,可归纳为风水说和包含审美、防潮等在内的功能说,现在许多学者如程建军等常将此两类解释框架内所涉可能性并举(18)参见程建军《风水解析》,第299-301页。。对于过白存在后功能的讨论,已然预设了过白的部分合理性,多是用现代科技对人的理解来拆解重构历史早于它的中国古代建筑及其知识体系,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王其亨和汤国华都强调的风水说。然而无论是王其亨的风水形势说,还是汤国华的阴阳平和说,都不能对民居建造的具体过白尺寸及其区域变化作出回答,其分析都因专业所限以建筑技术为中心聚焦于建成物,或有延伸。
本文将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建造参与者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从工匠的具体营造实践切入,以闽西三明市滕村滕氏宗祠大木工匠运用“要想富,一扣布”的过白谚语之过程为例,在延续以气为本体的理念之上,剖析大木在实现过白时遭遇的三重情境——技艺知识在专业上的复杂性、地方知识系统对技艺知识的编织、工匠根据变化的社会生活进行创造,及其带来的谚语意涵模糊的结果,推进对传统知识理解的多样化。
二、技艺实践中人的主体性
在大木作这门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简明的书面知识与零碎的谚语等口头知识,与繁复的建造活动形成了对比,而后者在建造过程中不断生成默会知识,其实只有二者结合在建造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前者的内涵。由此,这部分将突出工匠在技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分析这句谚语代表的表征知识在以实践为根本的技艺活动中的地位与性质。
(一)翻译图纸——多元的地方造法
对于最后一级包工并负责具体施工管理与操作的立师傅来说,手上拿到施工图纸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图,因为多数情况下,招标图纸上的数据呈现的运算逻辑与本地造法中的算法逻辑没什么相干。然而懂得后者才是本地人认同的“好师傅”,造出来的房子才是有“讲究”的好房子,而过白就是其中的基本讲究之一。立师傅认为施工图纸“只能看个大概,定个样子”,从后来施工的结果看,其中真正取用的精确数据只有面阔、进深和檐高,其他的数字与安排都是他按照地方做法重新计算之后再确定的。
在这份滕家宗祠的施工图纸中,被取用的檐高、进深、面阔三个数字,它们都由上一级的包工头、村里的地理先生维敬与族长文振共同商定。就本文所讨论的过白而言,它们在大木中的控制点落在天子壁(19)天子壁是闽西当地的说法,位于上厅心间(在当地指房子厅堂的四个中心柱构成的空间)靠后的两根柱子之间,用木板拼成墙面,墙壁上可挂祖容,壁前有案桌。、上厅出檐和下厅栋高上。在檐柱既定的腾氏宗祠,与之相关的大木结构确定过程大致为:第一步,根据檐高来算水以确定上厅柱高和间距、檐口高度(20)上厅的檐口高度虽与过白的控制点之一相关,但它的确定也与连接厅堂之间的过廊高度相关,过廊的梁架系统亦由大木决定。,第二步:上厅与下厅之间距离既定,根据所求上厅栋高,结合过白尺寸的需要推算出下厅屋顶的高度范围,进而确定下厅梁柱的高度;第三步,参照既有进深,确定下厅的柱高和间距。
在第一步中根据檐高来算水(21)算水,是当地工匠计算屋面的俗称,具体根据柱子的多少和进深来算每根柱子的高度,这决定了屋面最终呈现出的弯曲度。心间柱子的安排,基本决定了整栋房子柱网的排布。在闽西龙岩,根据当地木工的一般说法,屋面的水最大约为7,多用于庙宇,民居建筑则多取用3.5~5,大于5则太陡,而出檐处小于3.5则水会回流,排水不畅。如果算上软水(有的地方叫弯水),使得屋面相较于均匀变化构成的硬水更具曲线美感。,立师傅根据给定的檐高反推出了上厅的栋柱高度,同时其他柱子的位置也确定了下来,因为后大中、后小中不落地,后小小中被定成为天子壁两边所在的柱子,也就是说确定了过白所在天子壁的位置。即,过白的起点,直观而言是背靠天子壁,实则是在综合了建筑的类型 、柱列落地习惯、分配进深、确定上厅高度等之后综合确定的。
第二步,结合上步所定视觉起点,在符合二尺二的过白要求基础上,计算下厅的高度范围,再用算水计算出下厅柱子的排列。从一技术过程可知,过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事关厅堂乃至整栋房屋的高度与整体比例,尤其在面阔进深等条件既定或者难以有较大改动之时(民间建造的常见情况),它成为控制房屋高度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影响到了整栋房子的柱网排列。
第三步,推算出下厅的柱高和间距。在闽西当地的屋面装饰中,过白所指的下厅高常落在栋脊瓦的顶点。下厅的高度由下厅面的梁柱高度、梁树的皮(梁柱两端的上顶点)、屋脊的装饰、栋脊瓦的高度叠加而成,因为构件众多,所以其中实现控制的可操作性空间很大。若是调整梁柱高度,整栋房子的其他构件都需要跟着调整,事关建造成本(23)尤其梁树和栋柱的造价常为整栋房屋最高,因为木材越大越难得,超过一定规格后,木料价格越趋向于几何增长。。通常大木会选择调整栋脊瓦的高度。
因此,实现过白,不仅是在高度上的控制,而且是整个进深、面阔与高度等多方面的修整,在考虑梁架成本与效果的基础上几近刻意的对比例追求。算水与控制成本,虽有套地方做法的习惯,但更多的取决于大木师傅个人,这是大木师傅在建造中处于主体地位的体现。正是这些构件搭建起来的空间基本格局,表征出居住者日常的生活秩序,同时也是建筑作为持存物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场所,无怪乎村民会认为懂得他们能说出乃至不能说出的“讲究”的木工才算得上是好师傅。
(二)屋面算水——经验性的算数法
若要细究算水的方法,立师傅只说,“一千个师傅,一千种做法”。的确不同的工匠算水方法各异,现将工匠解决问题的途径加以分类整理,下面将列出此次施工所用到或听闻的方法:
1.计算类。立师傅有比较精确的计算逻辑,并有如“‘软水’那样的窍门”或不外传的秘技,通过较为周密而精确的计算过程实现。孙师傅的算水方法与此类似,但是其计算方法没有那么严密,他在确定了最开始、中间和最后的水这三者中的任意两个后,辅之以眼力进行调整。
2.记忆类。明师傅没有计算过程,但是他心里有些直接记住数字,那是他的师父传给他的,他也不问其缘由。当地老房子的样式有限,高度一般不会超过两层,高度重复性的建筑形态催生了模数化的做法,许多口诀与此相关。这套数字本身也分为很多种,可以供工匠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还可以根据工匠的个人意愿增减。
3.模拟类。这种方法本地匠人叫放大样,常用于计算比较麻烦或者无法计算之处,即用不同材质的材料做成模型,再按比例放大或缩小获取所需数据,最后按比例应用于实际制作之中。年师傅有个师兄,通过修一根竹子,将一端大致固定住,然后弯折中间或另一端至所需屋面大致的样子再固定,并量出和记录下相关的数字,根据倍数放大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数字。立师傅说有些人用棉线,摆出想要的屋面曲线之后,拉直棉线量数,同样按照倍数推算得出结果。图3为工匠放大样定卷棚数示意图。
这三类是工匠求数的常用方法,在实际中多有交叉或变通,它们都会因依赖经验产生模糊之处。在第一类相较最为精确的算法中,在符合当地建造习惯的范围内,使不使用软水、柱子如何落地等更取决于工匠的个人选择。在第二类中,口诀的来源可能是其师父根据自己的建造经验累积而来,亦可能有不知源头的师承,但是数字稍作改动也不会导致屋面出现严重问题(25)稍作改动也不会轻易出现屋面问题的原因可能有:1.当地的民居建筑高度有限,多为一层或两层。2.木结构作为多处相互支撑的框架结构,在水平上比较稳定。3.当地所用杉木材料弹性较大。,因此也极具个人性和偶然性。第三类模拟性算法中,得出数字的过程更难抽象化或书面化。归根结底,这种算法及其类似的技艺过程里产生的知识,无论是不同精度的计算方法,还是外人看来莫名其妙的数字口诀,亦或是就取材比比划划,都只需要求出了当前问题的答案将其解决就行,至于如何优化这些解决方法本身,不是这些修建民居建筑的普通工匠们考虑的重点(26)这三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之中无优劣之分,因为算法不同所带来精度上的区别,可以用工匠的眼力、手上功夫等个人才能通过实际操作来弥补。工匠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基本功,让他们的感知能达到极为精确的程度。技艺知识的精细,与其说符合工匠职业对精度的天然追求,不如说以解决问题所需精度为止,更重要的是,与在实际操作中所蕴含的诸多默会知识相配合,共同实现制作目标。当然这并不代表传统技艺知识并没有系统性累积和精度要求,只是本文从大多数没有家传系统的民间木工最为平常的建造活动出发,关于这点的讨论暂仅止于此。。
如果我们将木匠日常所使用的文字也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那么就不难理解这部分传统知识的独特之处。除了木工行业内广泛流行的苏州码,立师傅本人也有许多极简而随意的木工标记符号,如作为构件名称“又前小言”而非右前小檐(如图四),齐同而非骑童。它们是彼此能理解的熟人之间为快速直接解决具体问题而作,而这样的情境往往才是乡村木工的工作常态。有意思的是,立师傅自己都觉得自己的算法太过精确而显得呆板拘泥了,太多细致的变化意味着更多的费工。正如阿伦特所言:“技艺者把它(工具)设计和发明出来以建构由物质构成的世界,而且这些工具的适用性与精确性是由诸如他希望发明等“客观”目标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主观的需要和愿望所决定的”(2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这样,过白的实现,实际上是对建筑基本结构整体进行反复调整后的结果。多元的地方做法,算水等经验性的计算方法,实际施工中对成本的衡量等都充满了变数,地方惯习通常给出的只是一个控制范围,而真正占据劳动主体的工匠,常以关注问题解决的态度运用和累积自己的实践知识。这种劳动的主体性与知识的个体性,在第一个层次上构成了传统技艺知识的模糊性。
三、地方知识对传统知识的编织
如果说过白的实质是基于面阔、进深、檐高和算水等进行的比例控制,那么坚持取用这些数字的意义是什么?面阔、进深、算水与梁架安排综合决定的过白控制点,在这些数字基础上算出来的平面柱网排布及高度,实际上多吻合压白尺法特别强调的吉利尺寸(29)参见程建军《风水解析》,第284-286页。。即所谓的算白,实际上属于讲求吉凶的压白尺法。这节将回溯到滕氏宗祠确定面阔、进深与檐高的具体过程来加以阐释。
(一)打卦太保——地方权威对风水的编织
滕村内部对于此次扩建存在争议。村里近年来外出经商的人比较多,许多人家都盖了新房子。宗祠是老房子,在新房子的比较下显得特别破败,于是有人建议重修祠堂。又因村子发展还不错,有人认为不能把这么好的风水改了而不赞成重修。村中地理先生分为主张修的维敬和主张不动的家根这两派,家根派认为从忌神煞法来说当年根本不宜动土,但是维敬却说此法在清代官方的风水文献早已经被删除,借此质疑前者依据的权威性,并认为即使按照部分算法的确存在不宜之处,也可以在九星飞宫法等其他算法中“找补”回来。
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就去了村里人都信的太保庙(30)根据太保庙前的碑刻来看,太保疑为南唐李存勖。村民对确定这位神仙的身份并不大关注,然而一直崇信,庙里香火不断。,通过打卦来让太保定夺。打卦用两个牛角类似物,先问问题,然后抛掷,根据角落地的朝向来确定太保的意思,一般三局为定。结果,维敬一派的意见两次即通过,就是说新修祠堂是太保同意了的,接下来村里人便着手找地理先生。
闽西、赣南与粤东同属客家文化区,尤其赣南所在的江西有风水大师杨筠松,滕村村民自然想到的是去江西请先生。第一个先生看了之后说当年不宜动土,但村民此时已经在太保面前打卦得到了神灵的应允,遂请第二个。第二个江西先生测量的坐朝与族谱记载有出入,大家觉得他水平不行遂又作罢。第三个江西先生由家根派的人请来,严格恪守原来的中轴线,讲求左右对称导致面积扩展太小,村民又不满意。如此再三折腾,加之经费有限,于是宗族理事会决定取用本村地理先生,经在太保庙打卦决议,用维敬。三请风水的故事说明,江西风水为宗的地理行业权威不得不在地方的太保民间信仰和既定的社会事务面前让步。不过,家根派的意见也没有被忽视,最后达成的方案是,在不改变坐朝和水口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其实维敬的权威,不仅有上文所提及的太保权威,还与他本人在村中的声望有关系。维敬所在房派在村中占据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而他本人在村中德高望重。他的儿子辈和孙子辈有经商成功者,有吃官家饭的(公务员),有三个大学生,被村里人称为“芝兰林立”。村民都认为是他家风水好,维敬自己也这样认为。
这样,维先生及其所用风水理论的得以施行,并非是直接用三合派理论说服了反对派理论的结果,而是在借助类似于太保这样的其他权威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权威,在自身所用理论本身也面临竞争性话语的情况下,多方权衡后的结果,是地方社会文化对风水理论的胜利。
(二)坐朝水口——基于风水的营造尺法
维敬认为不改坐朝水口可保宗祠基本风水,何以坐朝如此重要?据滕氏家谱记载,宗祠的坐朝为坤山艮向。坐朝在实际中是房屋在纵轴线及其延伸线上与周围山势的关系,上厅的先天八卦与下厅的后天八卦也与山向呼应。既然要保持朝山不变,那么就是要尽量保持房屋轴线不变,而当地传统民居严格恪守左右对称。面对不规整的地块和扩建的需要,维先生权衡再三,最终定下了申山寅向,即在不改变朝山的基础上移动了七度(31)而这个七度,也成为了日后上梁时出现家根派挑衅的由头。在上梁的当天,家根派一众人来,站在房子的纵轴线上说宗祠的坐山朝向改变了,不行,坚决不能上梁。族长文振带领其他房派的重要人物过来,才平息了争端。维敬明白本来这次扩建在吉利时间的选择上并不完美,未免村中老人出事,哪怕他不认为是他选择的日子或者扩建本身有问题,村民也会如此归因,他最终放弃在已经定好的当天举行上梁。这样即使整栋房子的大木结构拼装了起来,房子的上梁仪式最终并没有举行,而是在梁树与栋齐同的之间垫了一个铜钱,等到适宜的日子把铜钱抽出来,上厅梁树落在栋齐同上,方算落成,而这个日子在一年后。。这样保持了坐山水口的风水格局和左右对称的建筑传统,在这些前提下最终尽可能的利用了地块,方定出最终面阔与进深。实际上,此次扩建可利用的地块很大,在宗祠的左边是某一房派的老房子,其房主曾表示若是需要,他可以免费将地让出来给宗祠扩建。很显然,这栋宗祠的扩建对吉利风水的追求远远大于扩大面积的欲望。对水口的坚持,逻辑亦然。
山与水,地理之道。《释名·释宫室第十七》将宅作为择也,意为选吉处而营之。《管氏地理指蒙·管氏本序》有云,人由五土而生,气之用也。气息而死,必归葬于五土,返本还原之道也。不仅如此,宅子本身没有宅气,是由移来的气变化的,人与万物共栖,形碍之物乃至人畜鬼神,都可以因气产生形态变化。(32)王玉德、王锐编著:《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3页。因此,万物之生以乘天地之气是风水的基本共识。这里的“气”,正如《古本青乌经》文末所说“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由外而内,皆有讲求。在大木结构框定的宅内,则以理气为代表,贯通着同样的逻辑。简而言之,风水实际上是理气。通过觅龙、观砂、察水、点穴这地理四科来理气以达到“内乘龙气,外接堂气”的目的。天子壁前的案台,上方供奉着神主牌位,下方则另有偶像,无论外形与名称如何,实则为“穴”之所在,是宅基核心的物质化(33)在王其亨有关祠堂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他说到:住宅内部也强调有一个核心,正堂中,一张条儿居中,正墙是祖容,或将祖宗的神主牌位供在条几上;下方,还常供有“地脉龙神”牌位,象征着宅基的核心,即“穴”的所在。徐苏斌(王其亨化名):《风水说中的心理场因素》,天津大学建筑系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如图5所示。因此,风水之谋是为了让人“乘生气”,即气为本体。
由此,聚落选址可理解为寻找蕴藏生气之地。祠堂的本体非仅止于所见建筑物实体,而是气的整与理之场所,而人之生皆需乘其气,无怪乎滕氏祠堂为全村人所重视,甚至旁涉到其他有血缘关系的村子(35)在该祠堂的立屋过程中,可以看到有外村人来,据滕村村民的说法,来的人多是祖上从滕村分出去定居于其他地方的人。,修建费用平摊,仪式参与者甚众,整个建造过程都在全村人的众目睽睽之下。风水理论中论述方位与各房支人事吉凶对应关系的言语比比皆是,即风水实际直接涉及到各房利益分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祠堂的本质是,先有气穴构成的吉利位置,后有物质搭建起来的空间以做区隔,而位置确定与空间区隔,复合而成为事关全村民众命运的集体空间。在当地人心中,它的力量,并非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符号系统,而是以气为本体,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和更改的实体,即《宅经》所云“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36)王玉德、王锐编著:《宅经》,第9页。。通过气及其所在风水之说,可知“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37)王玉德、王锐编著:《宅经》,第63页。一语,在信者心中不是虚言。进而,木工所掌握的鲁班尺法因此确能定吉凶,尺上所写“财病离义官劫害吉”及其对应的数字不是通过象征符号对人事的心理暗示,而是以理气为手段,对社会生活的操控。
大木建造,从根本上来说是用物质的性质与尺寸,来落实理气,以可见的物质来实现对不可见气之隔与通、流与止,进而切实的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以吉凶数字的形式表达。古建筑中的数字,多属于这一吉凶的尺寸系统。一匹布的二尺二,也应如是,至于具体以何种方法来确定这个二尺二数字为吉在本文中无需深究。
总之,包括风水在内的传统知识系统,其内部也充斥着竞争性话语,谁成为权威并影响实践是风水知识本身与落地所在社会之文化互动后的结果。这样,风水这一看似比较专业的系统知识,仍处在以“讲究”为代笔的地方知识支配下,被编织进它所遭遇的地方生活世界里,这是传统知识模糊性生成的第二层因素。
四、流动背景下实践的创造性
“要想富,一匹布”中的一匹布,似乎不言自明地指传统社会中的布匹,意思极为含混。也就说,即使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理想情况本身就充满了暧昧之处,然而,正是这种用语特点给了基于实践的技艺知识进行创新的空间。下文以“立师傅的大匹布”故事为例进行说明。
滕氏宗祠建成后的见白接近八十公分,远超出了传统大匹布约为二尺三即七十六公分的上限,这是立师傅个人有意设计的结果。他认为滕村的人,因为经商有钱,在外头的人很多,住在城市里的不少,他们早就习惯了外面的过法,对光线的要求高,因此他得扩大天白。当然这种脱离了惯有取值范围的创新,遭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在起架后,族长和其他几位村里说得上话的人,都过来对立师傅说,其他都挺好,就是上厅的檐口太高了。这里的高,显然不是说檐口的绝对高度太高,而是这个高度打破了他们对老房子的审美惯习(38)惯习作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体现行动能动性的关键所在。他受到潘诺夫斯基有关哥特建筑研究的启发, 本用来解释学者思维在建筑领域内的影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后来布迪厄将其视为一种无需通过算计而能在空间中找到得宜的方向和位置的游戏的感觉。他多次阐释了这个概念,认为它是反复灌输和必要适应的产物, 其使作为集体历史产物的客观结构可以用持续并带有倾向性的形式, 在类似条件长期持续情况下的有机体中再生,可以说惯习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 参见Bourdieu,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The Edinburgh Buil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89-90.,但最后还是被立师傅的手艺声望压下去了。
徒弟明弦问立师傅,不是说要想一匹布么,这八十过了二尺三,不是一匹布了,会不会就富不起来了。立师傅笑着说,这造出来的当然是一匹布(的尺寸),只是这个一匹是特别大的一匹,在以前要找也肯定能找出这么大的一匹布。这样说来,要想富一匹布暗含的取值范围可以扩展得很大。这样,既没有违背这句谚语的字面意思,也考虑到了时间与人的变化,立师傅不动声色适应了老问题下的新情况,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创新的实践。这种创新的实践,是延续一贯“各得其宜”式的问题解决思路,而非意在累积和完善工匠个人的技术知识,因此常被排除在强调沾染了现代性的科学创新定义之外。
在实际负责建造的工匠看来,能达成一匹布的尺寸,并非机械地落实理想数字,而是直接而敏锐地觉察到他所服务的人及其所处社会的变化,对材料及相关成本、美观及相关装饰、风水及相关知识、筑造及精准便利等多方权衡后,在实践理性指导下解决新问题。这样,在新的社会形势基础上工匠技艺实践的创造性,构成了传统知识模糊性的第三层。
总 结
对“要想富,一匹布”这句谚语的理解,若仅从“过白达到二尺二可发财”的字面意思进行解读,是其视为真理性断言的做法,谚语将被贬为构不成因果关系的数字游戏。高度聚焦于“二尺二”这一数值精确性,会将建造过程束闭起来,与建造活动所在的生活世界割裂开来,褫夺这句话在当地人心中的理解。
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涵是,客家人为追求财富等现世美好生活要素,不仅运用以气为核心概念的风水等传统知识,例如坚持营造尺法中有吉利意味的二尺二,还基于地方既有文化权威和社会结构的博弈对这些知识进行编织重构,例如太保权威对吉利时辰的扭转,并通过工匠之手以常规或变通的方式,回应着现代性在地方生活世界中的渗透,例如立师傅口中大大的一匹布,从而实现与祖先神灵乃至风水说所涉万物的共栖,期盼血缘家族绵续昌盛。它所代表的传统技艺实践知识中的表征部分,因匠人在技艺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伴随而来的知识的个体性、被落地的地方社会文化编织、工匠个人在实践过程中生发的创新或再解读等此三层情境,都催生了它的模糊性。与其说传统技艺知识在现代科学知识前有暧昧与沉默,不如说它们本就需要基于大量的默会知识,并在实践中等待被多元的地方生活世界编织,进而转化成为地方知识,其中的模糊之处,可能正是讲求无限贴合生活世界的技艺知识追随后者的多样性与流动性,而不断生发演化的空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