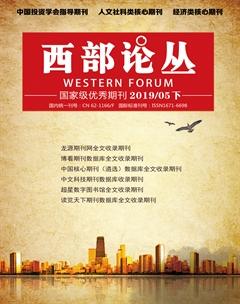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社交媒介伦理
王聪
摘 要:社交媒介是技术的产物。从IM(Instant Media)产生以来,至今社交媒介经历了一次更新换代。无论是在社交媒介1.0还是2.0时代,社交媒介中的伦理问题一直为学者和公众所关注。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学派认为,人的主体性已经丧失,技术理性完成了对主体的“复仇”。本文将从鲍德里亚后现代传媒理论的角度,以热点事件为例,来探讨微博、微信朋友圈这两大中国最热的社交平台中的伦理问题,并从技术和人等方面,讨论媒介技术如何完善,倡导平等对话、宽容差异性、诚信待人以及积极向上的社交媒介规范。
关键词:社交媒介 伦理 鲍德里亚 微博 朋友圈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拟象”。所谓“拟象”就是游移和疏离于原本,或者说没有原本的摹本,它创造出来的是一种人造现实或者第二自然。模拟与仿真产生了超现实,即用模式和符码制造出来的“现实”。社交媒介将模拟与仿象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真实与想像的界限被消解了,信仰、价值和文化也被消解了。在社会、文化和媒介被高度拟象化的情境下,大众只能在当下的直接经验里,体验时间的断裂感和无深度感,体验日常生活的虚拟化。[1]在符号构造的社交媒介中,伦理问题大量存在,而在对付伦理问题方面,技术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当然,媒介技术最终产生作用,还是要依靠人类。
一、微博、“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与伦理问题
关于社交媒介中的伦理问题,笔者将它们归纳为三类:第一,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负面的伦理问题,如网络谣言,网络煽动等;第二,由使用程度决定正负面,如网络舆论、网络揭露;第三,无法避免只能尽力做好,如技术歧视。
微博是由虚拟和仿象构造出的第二自然。微博作为社交媒介,其中用户的关系脉络十分庞杂,一个社会问题出现,便会同时暴露在亿万人的眼下。微博上信息的实时发布和快速传播,让很多人能够同时参与到同一件社会事件当中。这是现实生活中难以出现的场景。
网络流言、欺凌和盯梢是微博等社交平台常见的伦理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匿名和化名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虚拟身份只是大部分社交媒介的其中一个特点,而非社交媒介的全部。一直有人建议实行网络实名制,这对于媒介技术来说算不得什么问题。但是,实名制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未可知。前几年,谷歌、雅虎等曾组成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与普通的假设相反,实名身份信息的帖子似乎不加重风险。相反,风险与互动联系在一起。”[2]
朋友圈同样也是符码和模式构造的虚拟世界。相较于微博的开放性,朋友圈则属于私人空间,由于保留了对外界的入口,因此具有半开放性。虽然是“实名制”,但朋友圈仍是虚拟世界,人们在进行自我呈现的时候,极容易利用符号来误传事实。今年5月,“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件是一个典型例子,关于婴儿丢失的信息在朋友圈广泛传播,在微博上也形成了很大声势,在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后,真相却是整个事件都是婴儿母亲自导自演。
社交媒介除了以上的伦理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例如,非理性輿论,网络暴露与揭露,不雅、血腥图片和视频的传播,网络欺骗等。
二、社交媒介与人的伦理
(一)社交媒介是非中性的
社交媒介并不是“中性”的。莱文森说:“实际上,枪械和枕头有许多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可能被用于或好或坏的目的。” [3]笔者认为,如今的社交媒介还没有和“枕头”一样的属性,而技术能够进步的空间,大概就是枪械和枕头之间的距离。
微博是被机械化即效率驱使的工具,这句话应该不难理解。微博设定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关注和转发。为了能在微博上更好地生存,一个微博账号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关注和转发量。正是由于这条终极的规则,一些别的价值和规则被忽视了,比如信息的真实性,比如责任。微博上一些有违伦理的现象,或许并非源自恐惧、羞愧的缺失,而是终极规则的印象过于强大和深刻。
朋友圈这种社交媒介,虽然人际传播是主要模式,但在进行人际传播前,需要经过大众传播。这种大众传播来源于朋友圈可以分享其他平台信息的功能设置。这个看似简单的功能,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当人们在一些网站上看到感兴趣的信息时,会有分享的欲望,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朋友圈是一个分享选择,于是毫不犹豫地点击分享。戈夫曼说:“显然,许多表演者都有足够的能力和动机来误传事实;只有羞愧、内疚或害怕才能让他们放弃这种企图。”[4]很明显,那个按钮不会感到羞愧、害怕或者内疚,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些顾虑。
(二)社交媒介中的道德主体被消解
这里所说的道德主体指的是人在社交媒介中的虚拟身份。这种虚拟身份的消解的因素主要来源于技术客体和道德主体自身。
(1)技术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消解主要是通过匿名化(或虚拟化)和行为主体符号化来实现。社交媒介从一开始的技术设置就是人的匿名化。但是,社交媒介的技术环境,使得行为主体符号化,行为主体的多变性和多重性使得伦理道德无法将其规范,身份的匿名化更是加大了这一难度。
(2)道德主体的自我消解来源于对技术理性的顺从和自我约束的弱化。技术客体为人提供了虚拟化的身份,它的初衷是为了营造轻松的社交氛围。但是,身份的虚拟使得人们越来越忽视现实生活中的伦理价值,转而以社交媒介的工具理性为行为准则。社交媒介中的人更容易主动逃避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
三、社交媒介的救赎
社交媒介已经与人分不开了,因此,在谈到社交媒介伦理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谈在社交媒介世界中的人的伦理。至于社交媒介的伦理体系如何构建,还是要谈到技术与人。
(一)技术的“救赎”
1.为微博用户建立信用评分机制
笔者认为,应该在微博中建立起一套信用评分机制,对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进行扣分等处罚。比如一个媒体账号发布了影响恶劣的假新闻,微博就可以对它进行封号处理,封号的时间视造成的后果而定。考虑到微博用户量的庞大,这个规则可以着重于限制影响较大的用户,从而达到“上行下效”的效果。
2.技术公益化
微博是开放的社交媒介,监测自然不成问题。然而像朋友圈这样的私人空间则无法得到监测。但是,朋友圈中已经可以看到投放的广告,这一功能同样可以用来发布一些有助于澄清谣言、引导圈中舆论的信息。但是,此类技术的使用不应侵犯私人空间、探取私人信息。
(二)人的“救赎”
1.建立平等对话关系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其提出的对话理论将自我主体与其他的自我主体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相互依存,人与人之间该是既独立平等又相互交往的关系。[5]在哈贝马斯看来,自我和他人的对话关系以平等为基础条件,即在对话关系中不存在任何人的特权和优势。
巴赫金和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是一种对话中平等的互相的积极的交往方式,这也是社交媒介中所应遵循的方式,即平等对话。微博上大部分的攻击、谩骂都来源于未能建立平等对话关系。每个个体或者群体都认为自己的言论是惟一正确的,其他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骂战。因此,笔者在这里倡导在微博等社交媒介中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在表達的同时也能够尊重别人的言论。
2.学习社交媒介
笔者认为,既然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是需要教授的,那么,社交媒介同样需要人们加以学习。然而,如今人们对于社交媒介仍是自学的状态,导向偏差或迷失便不足为怪了。构建社交媒介的伦理规范的重中之重是提升人的媒介素养,即学习虚拟世界中的“进退之礼”。
从技术和人的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单纯地讨论技术的自我完善和人的自我提升,那么就割裂了技术和人已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建立完善的社交媒介伦理体系,最重要的是技术与人之间的协作。“以道驭术”是一种理念和境界,技术的完善和人的伦理修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四、小结
社交媒介与人已经密不可分,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技术无法做到“明哲保身”。如果技术的属性是“枪械”,那么无论用作何途,它的最主要的属性仍是危险性。但如果技术的属性是“枕头”,那么它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因为柔软、舒适才是枕头的属性。因此,技术完善的目标就是将“枪械”属性改良为“枕头”属性。人在社交媒介中的交往忽视了伦理规范。传统的伦理规范依然有借鉴意义,但在新媒介时代,社交媒介的伦理规范应该有新的阐释。在社交媒介中,应该建立平等对话、包容、诚信以及积极向上的交往规范体系。人们需要学习在虚拟世界中的“进退之礼”,了解社交媒介的本质,形成对社交媒介的批判意识。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10.
[2] 速途研究院2015年8月7日报告:http://www.sootoo.com/content/653234.shtml.
[3] 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6),169-169.
[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47.
[5] 陈太胜.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文精神.学术交流.2000(01),08(07),109-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