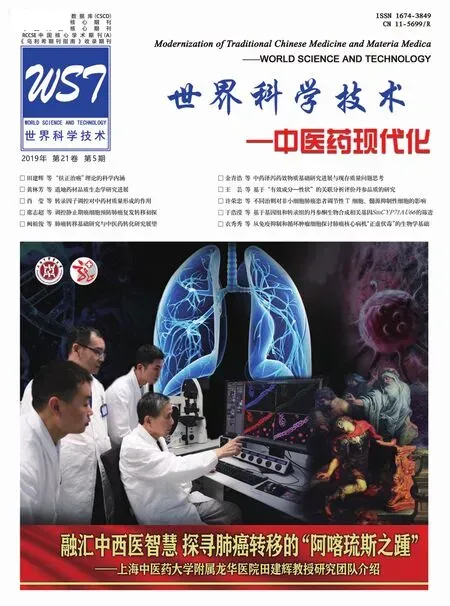薛生白《湿热病篇》以六经辨析湿热病规律探究*
马 鹏,李群堂,成茂源,郑秀丽,杨 宇**
(1.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成都 610075;2.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 400011)
薛生白《湿热病篇》采用三焦辨证方法已被学者广泛接受[1]。笔者在《薛生白<湿热病篇>与六经辨证》一文中提出“薛生白的三焦分证,只是湿热之邪病及太阴阳明、郁遏三焦相火后出现的部分兼夹证”[2],不能囊括湿热病的全部证候。所以,将湿热病部分兼夹证表现出的三焦特征总结概括为湿热病的辨证规律就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认为,《湿热病篇》是采用六经辨证体系认识湿热病的。具体而言,从证候规律来看,“正局”和“变局”是《湿热病篇》湿热病分证的两大纲领,其中,湿热病的“正局”以太阴、阳明经为中心,在证候上体现出《黄帝内经》的三焦分布特征,“变局”则是指在“正局”的基础兼见少阳病、厥阴病、太阳病和少阴病;从湿热病总体病理特征来看,“气钝血滞”贯穿湿热病的始终,是湿热病“正局”“变局”产生的内在病理基础。
1 湿热病之“正局”
湿热病的“正局”是指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的证候,并非“湿热病病机变化之常”[3]。追溯《湿热病篇》“正局”、“变局”原文,薛生白谓:“此条乃湿热证之提纲也……而提纲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诸证,皆湿热病兼见之变局,而非湿热必见之正局也。”[4]102湿热病的提纲是以表述具体的证候为主,并不涉及病机,而且临床所“见”到的也均是证候。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湿热病篇》的“正局”与“变局”指的是证候,并非病机。“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阳明和太阴经为湿热病的病变中心,所以湿热病的必见之“正局”实指湿热阻遏阳明、太阴的证候。
1.1 太阴、阳明是湿热病“正局”的生发中心
综观《湿热病篇》全文,薛生白常把太阴与阳明列在一起论述湿热病的病位。如“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4]102,“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4]104,“湿热之证,阳明必兼太阴者”[4]104等等。太阴主湿,阳明主燥热,湿热属于半阴半阳之邪,同气相求,故湿热病的发生发展与太阴阳明密不可分。
1.1.1 阳明是湿热邪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5]
阳明胃是湿热邪气侵入人体的主要门户,化热生火的原点。薛生白谓:“湿热之邪从表(指太阳经)伤者十之一二,从口鼻入者,十之八九”[4]103,“邪从口鼻而入,阳明为必由之路”[4]111。口鼻是湿热邪气伤人的首过路径,邪从口鼻而受,循着阳明经进入,“始虽外受,终归脾胃”。正是因为阳明是湿热邪气从口鼻进入人体的门户,与《伤寒论》风寒邪气从太阳表伤相对举,薛生白提出“湿邪初犯阳明之表”[4]105的概念,提示邪气伤人具有各自特有的生发机制。从六经气化的角度来看,阳明本燥而标阳,易于化火生热,湿热邪归脾胃,很容易郁遏化火生热出现但热不寒,胸痞,汗出渴饮的症状。
1.1.2“太阴内伤”是湿热病发生的内在基础
湿热病的发生多有太阴内虚的病理基础。薛生白谓:“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指湿热)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4]104为了避免学者误认为这种太阴内虚是由于湿热邪气所致,薛生白还明确指出“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脏之谓”[4]104。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湿热病的发生以表里同病、虚实夹杂最居多数。湿热病的发生不但与太阴虚损有关,病情的轻重也关乎太阴虚损的程度。如薛生白谓:“若湿热之证,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4]104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若平素中气充实者感受湿热邪气,病情也易于康复。因此,太阴内伤是湿热病发生的基础、病情轻重及转归的关键。
基于同气相求的原则,素体太阴内虚夹痰湿者易于感受湿热邪气而发湿热病。湿热邪气多从口鼻而入,循阳明之经侵犯人体,“始虽外受,终归脾胃”。阳明是湿热邪气侵入的途径、化热生火的原点,太阴是湿热邪气侵入的基础、病后转归的要点。
1.1.3“内外相引”是《湿热病篇》重要的发病观
如前所述,“太阴内伤”是湿热病发生的内在基础,阳明是湿热邪气的“所入之门,所受之处”。与风寒等邪气伤人的方式不同,湿热病发生的始动因素可以是因为触受的热邪与内湿交结而发病,也可以是直接口鼻吸受湿热邪气。但不论是那种方式,湿热病的最终呈现形式都是表里同病。而导致湿热病呈现表里同病的重要机理即在于“内外相引”。太阴虚损生湿或湿阻太阴则易于给湿邪或热邪入侵提供基础,并且太阴虚损的程度可以影响湿热病的病程和预后。因此,所谓“内外相引”既指湿热病发生的内在机原,也提示了湿热病治疗上的关键着眼点,即分离湿热[6],使不相引[7],如薛生白谓:“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4]110
1.2 湿热病之“正局”与三焦的关系
学者一般认定薛生白《湿热病篇》采用三焦辨证的依据有三点:其一,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明确提出了湿热“未尝无三焦可辨”,如其谓:“湿热之邪,不自表而入,故无表里可分,而未尝无三焦可辨。犹之河间治消渴,亦分三焦者是也”[4]110[8];其二,薛生白演绎了湿热病三焦变化的证治规律。如第9条“湿邪蒙扰三(王孟英认为‘宜作上’)焦”[4]109,31条“浊邪蒙蔽上焦”[4]119,10条“湿伏中焦”[4]109-110,14 条“湿热阻闭中上焦”[4]113,11 条“湿流下焦”[4]110;其三,薛生白提出湿在三焦的治疗法则。如湿浊蒙蔽上焦,轻者“宜用极轻清之品,以宣上焦阳气”[4]109,重者“宜涌泄”[4]119,如湿“病在中焦气分,故多开中焦气分之药”[4]109;“湿滞下焦,故独以分利为治”[4]110。
考察这些文字似乎易于得出《湿热病篇》三焦辨治的结论。但笔者细绎原文后发现(具体见表1),这些“中上二焦”“下焦”“三焦”的名词与《温病条辨》的三焦不同,并非上焦(心肺所属)中焦(脾胃所主)下焦(肝肾所主),而是以胃为界线的上中下位置划分,如“湿邪蒙蔽上焦”的证候指的是胃气不舒的脘腹痞闷,湿阻下焦指的是太阴内虚夹湿的下利。事实上,《湿热病篇》所论的三焦源于《黄帝内经》,如《灵枢·营卫生会篇》云:“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出焉”[9]。

表1《湿热病篇》条文与自注对照表
归纳原文,笔者总结出了湿热病“正局”的三焦分布表(表2)。分析此表可知,湿热证因其病发即是表里同病,“故无表里可分”,因其证候具有三焦特征,确实“未尝无三焦可辨”[4]110,但此处的“辨”并非湿热病的三焦辨证而是分析确定的意思,即确定湿热病之“正局”证候的三焦定位。至于《湿热病篇》中提到的宣通上焦阳气、分利等的治法,仅是薛氏借用当时习用的措辞来表达湿热病“正局”出现病位上下偏移后具体论治方法,并不能构成严格的三焦辨治体系。

表2 湿热病“正局”三焦分布表
综上,可以知道,薛生白《湿热病篇》中“上焦”,“中焦”,“下焦”,“中上二焦”等三焦,实乃《灵枢·营卫生会篇》中生理位置之三焦;《湿热病篇》论述湿热病“正局”有三焦分布的特征。这些不足以说明薛氏的本意是用“三焦辨证”的方法完成对湿热病总体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写作的,六经辨证才是薛生白认知湿热病的基础。
2“气钝血滞”是湿热病的基本特征
湿邪郁阻气血的观点遍布《湿热病篇》。比如“阳为湿遏而恶寒”,“湿蔽清阳则胸痞”[4]103,“湿遏卫阳之表证”,“湿邪之郁热上蒸”[4]105,“湿热蕴结胸膈”,“湿热阻遏膜原”[4]108,“湿邪蒙绕上焦”,“湿伏中焦”[4]109等。考察这些“遏”“蔽”“蕴”“阻”“蒙”“滞”“闭”“留”“困”等与“湿”相接的高频词语,可以看出湿邪困阻气血的特征。与风寒邪气伤人阳气的观点类似,易于阻滞气血是湿热邪气伤人的基本特点。若从湿邪伤人的结果来认识,薛生白提出的“气钝血滞”[4]120一说最为精准。
“气钝血滞”体现在具体的脏腑经络上,既可以表现出湿滞阳明的胸痞[4]103、甚至神昏笑妄[4]108、舌白口渴[4]112、脘闷[4]109、呕恶[4]114、大便不通[4]108等症,也有湿阻太阴的四肢倦怠[4]103、身重关节疼[4]105、自利尿赤[4]110、腹痛下利[4]117等症。以上所列的阳明、太阴证候即属于薛生白所谓的“湿热必见之正局”[4]102。在湿热病的发生发展中,湿热易郁遏游行于少阳三焦的相火导致“耳聋干呕”,引动厥阴风火导致“发痉发厥”[4]102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点,因此,薛生白将湿热所致的少阳、厥阴证等定为湿热病“兼见之变局”[4]102。总之,湿热病的“正局”和“变局“均体现出了湿邪郁阻气血导致“气钝血滞“的病理特征。
3 湿热病之“变局”
湿热病之“变局”指“正局”以外的其他证候。《湿热病篇》论及的“变局”以少阳热郁和厥阴风火最为典型。究其原因与湿热邪气易阻滞气血导致“气钝血滞”的病理特征有关。
3.1 湿热郁遏相火是出现少阳热郁的关键
考察《湿热病篇》的少阳证主要以呕恶和寒热往来为主,分别列在第1条、第8条、第15条、第16条、第27条。薛生白认为“病在二经(指太阴阳明经)之表,多兼少阳三焦”[4]102,而形成少阳热郁的关键在于“盖太阴湿化,三焦火化……若湿热一合,则身体中少火悉化为壮火,而三焦相火未有不起而为疟哉。”[4]111据此可见,湿热郁遏游行于少阳三焦的相火是出现少阳热郁的关键,其中呕恶和寒热往来是少阳热郁的代表证候。
3.2 肝肾素虚、火气郁闭是出现厥阴风火的前提
痉厥证被薛生白视为厥阴风火的典型证候,分别列在第1条、第4条、第5条、第7条、第23条、第34条。“风火闭郁”是引发厥证的要点之一,如薛生白谓:“盖痉证风火闭郁,郁则邪势愈甚,不免逼乱神明,故多厥。”[4]106肝肾素虚是引发痉厥的要点之二,如薛生白谓:“若肝肾素优,并无里热者,火热安能招引肝风也。”[4]111因此,可以认为肝肾素虚、火气郁闭是出现厥阴风火的前提,而郁闭气血的病理因素即为湿热。
《湿热病篇》第4条历来受到医家关注。有质疑药不投病者,比如王孟英就认为“地龙殊可不必,加以羚羊、竹茹、桑枝等亦可”[4]105,加重了原方平镇肝气的作用。也有高度评价并于临床中广泛使用此条者,比如李士懋[10]以“舌红苔黄腻,脉濡数”为诊断要点,将《湿热病篇》第4 条用于治疗内科常见的肢体酸沉、疼痛、麻木、憋胀、肿胀、痉挛、抽搐、转筋、僵硬、萎缩、歪斜等症,取得良好效果。笔者认为第4 条是薛生白治疗湿热病早期发痉(“三四日即口噤”)的证治。而引起湿热病早期出现痉厥的原因在于湿热困阻经络气血,故“选用地龙、诸藤,欲其宣通脉络耳”[4]105,“厥证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4]107,湿开热透,痉厥自止。若湿热病进一步发展,湿热化火燔灼肝经耗伤真阴后出现痉厥之证,则须使用重剂平肝潜阳之品,如《湿热病篇》第5条、第7 条所示,此非辛泄之品所能及也。因此,湿热痉厥的早期治疗以辛凉泄热为主,中后期的治疗则以咸寒清热为主,二者治则相反若是,但确是病情所需。这属于湿热所致的痉厥的特有病理特征。
3.3 病在太阳是湿热邪从表伤的少见形式
湿热之邪是薛生白研究的对象。薛氏认为湿热邪气多从口鼻而入,阳明主燥,太阴主湿,故早期以阳明、太阴经证为主。但也有部分湿热邪气(特别是湿邪)可从太阳之表伤(“从表伤者,十之一二”),这种湿邪入侵的途径以暑月伤寒最为多见,如第40条、第45条,属于湿热病的类证[11]。
值得提出的是《湿热病篇》第2 条和第3 条。第2条(“湿热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湿在表分”)名为阴湿伤表,实为湿热受自口鼻之阳明之表、湿重遏制阳气的证候。第2条所列的方药仅可暂用,一旦寒解热透,湿邪化热,汗出不恶寒则需要改弦易撤,另立新法,比如第3条所示。第3条(“湿热证,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湿在肌肉,不为汗解”)较第2 条病位略深,而且热邪渐盛。这种情况不但要辛凉解表,更要重用清利湿热之品,“不欲湿邪之郁热上蒸,而欲湿邪之淡渗下走耳”。因此,第2条和第3条所示的并非病在太阳的湿热证,而是病在阳明太阴之表的湿热证,与暑月寒湿证截然不同。
3.4 病入少阴有寒热两端
湿热病久也可进入少阴一途,有热化和寒化两端。薛生白在第24条展示了湿热证,十余日后出现的少阴热证(“下利咽痛,口渴心烦”),第25 条展示了湿热证从阴化寒、“湿中少阴之阳”的少阴寒证(“身冷脉细,汗泄胸痞”)。毕竟湿热邪气与风寒不同,更易于郁阻气血、从阳化热,故较少出现单纯的少阴证,薛生白论述亦不多。
4 小结
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湿热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正成为医患共同面对的难题[12]。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湿热病篇》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湿热病篇》以六经辨治湿热病[13]。笔者此文仅围绕薛生白如何以六经分析湿热病证候,得出“正局”和“变局”是其分辨湿热病证候的两大纲领,其中“正局”以太阴阳明经证候为中心并体现出三焦分布特征。《湿热病篇》的“三焦”源于《黄帝内经》,是以胃为界限而划分的三焦,与后世吴鞠通《温病条辨》的以脏腑构成的三焦(上焦心肺所主,中焦脾胃所主,下焦肝肾所主)不同。因此,后世学者认为《湿热病篇》的辨治体系采用三焦辨证[14,15],恐属误读。“变局”则展现了湿热邪气与其他四经(指太阳经、少阳经、少阴经和厥阴经)的关系。限于篇幅的原因,本篇主要探讨湿热病六经证候特点,笔者接下来将在相关文章中再具体阐释薛生白《湿热病篇》的六经治法和方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