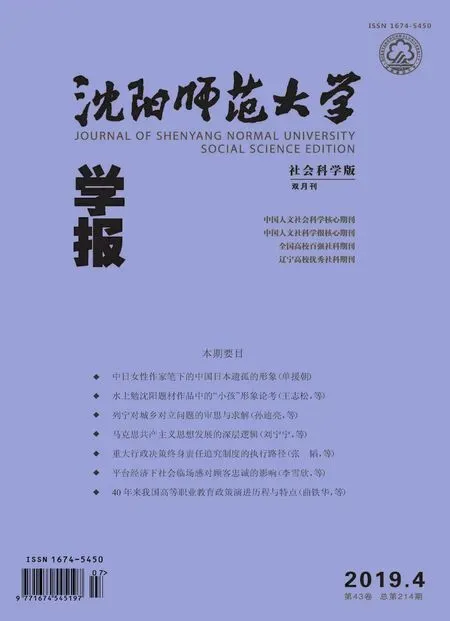阿万纪美子的“满洲”书写及其“满洲”认知
——以《云》为重点考察对象
林 涛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一、阿万纪美子及其“满洲”题材儿童文学
阿万纪美子(Kimiko Aman)1931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抚顺市,后移居新京(今长春)、大连,1947年返回日本。因童话集《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①原题为《車のいろは空のいろ》。同时获得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和野间儿童文艺推荐作品奖(1968年),从此登上文坛,成为日本战后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我国对其译介较晚,据笔者了解,单行本始于2007年,由彭懿翻译的《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等,其后便逐渐被大量介绍过来。这些作品,大多想象丰富,充满温情,且以面向幼童、低年级学生为主。但实际上,她的作品涉猎题材丰富,尤其是在早期创作出了堪称儿童文学中异类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系列作品②如《ぼくらのたから》(1965年)、《白鳥》、《すずかけ通り三丁目》(1967年)、《ただ一機》、《海から、空から》、《こがねの船》、《雲》(1968年)、《美しい絵》(1969年)、《どんぐりふたつ》、《とらうきぷっぷ》(1971年)、《赤い凧》、《おはじきの木》(1975年)、《ちいちゃんのかげおくり》(1982年)、《しらないどうし》(1984年)、《黒い馬車》(2006年)等。。通过这些作品,阿万纪美子暴露了日军滥杀无辜的罪行、殖民地异民族间关系的错位、开拓团对战争的协力及日本政府抛弃本国移民的行径,书写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创伤,表达了反战这一共通的主题。其中《天鹅》(1967年)、《云》(1968年)、《一幅美丽的画》(1969年)、《红风筝》(1975年)、《黑色马车》(2006年)等5个短篇,内容直接关涉殖民地“满洲”这一话题。而这一话题之所以被反复书写,正是给作者带来的沉重负疚感为其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书写“满洲”之于阿万纪美子而言,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用来厘清长期困扰于自身和既是故乡又是异乡的“满洲”之间的纠葛的重要手段。由于这几部作品尚未译介到我国,因此首先有必要在此对其内容加以简述。
《天鹅》和《云》,发表时间前后仅相隔一年,后者是基于前者的改写本,讲述了中日两国少女在殖民地“满洲”这一时空下产生的友情的故事。中国女孩爱莲居住在山丘以北的“满人部落”,日本女孩小雪居住在山丘以南的日本人开拓村,二人时常相约在山顶上玩耍。原本相对平静的生活因便衣队突袭日本人村的事件陡然改变,“满人部落”集体受到牵连,遭到日本军队的枪击和火烧。为救小伙伴,小雪从山丘上奔向了火海。至此,两个文本内容基本一致,但其后的结局大相径庭。当小雪落入火海的一瞬间,在《天鹅》里,两个女孩同时化作了飞向天空的天鹅。而《云》中女孩则双双惨死,开拓村的人们在哀恸中为二人建墓祭奠。对于作者前后所采取的超现实和写实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日本学界早有议论①请参照高井節子「あまんきみこの作品の魅力」(『日本児童文学』1982年2月),畠山兆子「あまんきみこ初期作品の研究―『車のいろは空のいろ』収録作品を中心に―」(『梅花児童文学』2005年6月),木村功「あまんきみこの戦争児童文学―戦争体験の表象とその問題」(『岡山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録』第142号、2009年)等论文。,本文不再赘述。
接下来,《一副美丽的画》讲述的是日本临近战败之际,开拓团移民为躲避苏联军队追击提前撤退、在途中发生的悲惨故事。身怀有孕的母亲为了不拖累年仅10岁的大儿子,哄骗他随大队人马撤离,自己则选择了和逃亡困难的村民集体吞下氰化钾自绝的道路。得益于中国和尚的救助存活下来的大儿子回到日本后终于明白,母亲和那些一起自杀的开拓团移民其实是被日本政府,也就是自己的国家抛弃了。而时隔30余年后的《黑色马车》是对该文本的又一改写之作,尽管内容和叙事角度有所不同,但情节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动。
《红风筝》记述的则是一对祖孙从“满洲”回到日本以后的日常生活,以及祖孙二人之间截然不同的“满洲”观和战争观。
以上5个短篇主题各有偏重,但均涉及开拓团这一“满洲”的日本移民问题。《天鹅》和《云》从正面书写了殖民地“满洲”日本移民的生活,以及“满人”与日本移民、“满人部落”与便衣队、日本移民和日本军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属日本“满洲”移民侵略行动推进阶段的故事。《一幅美丽的画》和《黑色马车》着眼于临近战败移民在撤退时遭到日本政府抛弃而被迫自杀的弃民问题,属于“满洲”移民侵略行动进入尾声阶段的故事。《红风筝》则把视点聚焦在了回到日本后的“满洲”移民的日常生活上,属于“满洲”移民行动的后遗症问题。尽管只是几个短篇,关联起来看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在“满洲”殖民历史上曾经大力推进的移民侵略的整个过程,以及由此给中日两国人民所造成的创伤。笔者认为,研究这些作品对于了解阿万纪美子的儿童文学创作全貌及其战争观、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综观其上述“满洲”题材作品的基础上,选取代表作《云》为个案进一步加以深入细致的考察。
最初,《云》刊登在1968年9月发行的《日本儿童文学》第14卷第9号上,后又于1970年收录入《现代日本童话我们的夏天》第11卷中,2002年再经作者改稿后为中学教材《现代国语1》(三省堂)录用至今。从作者几易其稿再到被教科书录用这一事实来看,无论是对于作者个人还是日本社会来说,《云》都堪称是一部重要作品。通过考察“满洲”这一形象在该文本中是如何书写又为何如此书写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描写在上述三个版本中有哪些变动、又为何如此改写,以期明确作者阿万纪美子的“满洲”历史认知是本文探究的目的所在。
二、对“满洲”时空下的友情解析
如前所述,《云》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乎两个少女之间友情的简单故事。不过,它发生的时间、空间及在此时空下的人物身份属性还是很特殊。时间是在“满洲国”建立之初,具体的空间位于殖民地“满洲”中日两个村落的分界线、一个可以清晰地望得见“地平线”和“琥珀色高粱地”的山丘上。两个主要人物“满人”孩子爱莲和日本孩子小雪分属山北、山南两个村落。于是,在这样的时空、身份属性下产生的友情便注定是一个悲剧,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分量和特殊的意义。二人的友情具体体现在作者笔下描写的几件小事上。
首先,小雪父亲答应爱莲带她坐火车去措林镇。《云》总共由五章构成,在第一章中有一个爱莲讲梦的场景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她兴奋地告诉小雪说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飞翔的鸟儿,从空中看见了措林镇和泛着粼粼波光的鹤江。读者清楚,爱莲之所以会做这样的美梦是因为三天前确切得知了能被带去镇上的消息。无疑,这是小雪同情爱莲没有坐过火车,特意央求父亲才有的结果。
其次,小雪准备偷偷把饭团送给爱莲。开拓村被袭击的第二天学校放假,小雪立刻想到可以去找爱莲玩耍。小雪知道“爱莲喜欢吃饭团”,于是在午饭时“拿到了三个热气腾腾的饭团,但只吃了两个,剩下的一个偷偷地用纸包了起来”。因为朋友喜欢,即便自己吃不饱也要与她分享。而同样这句话在教材版中被改成“爱莲也非常喜欢吃饭团”,进一步强调了爱莲在小雪心中的重要位置。比起央求父亲带小伙伴一同前往镇上,送饭团,尤其是再加上“偷偷地”这一修饰行为的词汇,应该说更体现了在殖民地“满洲”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小伙伴间的纯真友情。
众所周知,“满洲国”是关东军1932年在我国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国家,口头上标榜“王道乐土”和“五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实则为在满的日本人统领各民族,实施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关于食物的分配,“满洲国时期,人被分为三等:一等为日本人,二等是朝鲜人,三等是汉、满人。等级不同,分配到手的粮食种类也不同。日本人是大米,朝鲜人是大米、高粱各半,中国人只有高粱。(中略)日本以外的民族若是吃了大米饭就要受到等同于‘经济犯’的处罚”[1]。“偷偷地”这一行为通常会被看作是小雪出于担心大人责骂的孩童心理,但或许还可以理解成是小雪既想让爱莲吃上大米饭团又不让她遭受处罚,所以就连父母也要隐瞒的缘故。当然,小雪只是一名十来岁的小学生,不可能清晰地了解严格的民族身份等级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但笔者以为,战争年代的孩子会以敏锐的神经感知到其中的利弊关系。一个小小的饭团不仅折射出了“满洲”严峻的粮食状况和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而且还体现了在远离成人的儿童世界里,无论怎样特殊的年代都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最后,小雪为救爱莲失去生命。如前所述,日军认为突袭开拓村的便衣队潜入了“满人部落”,于是把“部落”中的“满人”统统驱至凹地,准备浇油烧死。当发现头扎自己赠予的黄色发带的爱莲也在其中,而火焰已经从凹地向四周开始蔓延的瞬间,小雪猛地从山丘上的草丛跑出直奔大火而去,同时嘴里喊道:“爱莲!快逃!”当日军的枪声接连响起之时,小雪更是拼尽全力挣脱山内队长扑向了火海。小雪的死被描写得十分悲壮,由此,两个小伙伴的友情被渲染到了极致。
综上,两位小主人公之间的友情主要体现在小雪对爱莲的关爱乃至生命的付出上。而“小雪”和“爱莲”①原文中的名字分别为“ユキ”和“アイレン”。这两个寓意纯洁无瑕的名字也显示出了作者对中日之间的友情所寄予的美好希望。
然而,说到友情,笔者以为首先它应该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关系上,其次行为也应具备互动的双向性。但在小雪和爱莲之间,前者始终处于施恩的一方,而后者仅是受惠的一方。爱莲除了会翻几个跟头以外,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称得上予以小雪友情的行为。这一对友情单向性的书写,不得不说反映了作者虽力图表现特殊时期超越异民族隔阂的友情,但终究囿于自身的身份而将书写的视点完全集中在了同属大和民族的小雪身上的局限性。当然,这一书写特点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作者是在竭力通过塑造充满人性温暖光辉的日本女孩小雪这一形象,来表达自己对“满洲”的愧疚及受难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赎罪之情。更加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像一般儿童文学作家那样回避对战争杀戮场面的细致描写,而是以他者的视线从正面书写,将剑锋直指造成两个女孩及“满人”死亡悲剧的罪魁祸首——日本军队,体现了一个作为有良知的日籍作家正视日军侵略“满洲”历史的勇气。在此,不妨引用文中描写日军实施暴行的场景如下以示佐证。
中队长转身大声喊道:
“好!敢对天发誓说自己不是便衣队的人站到对面的凹地里去!”
他手指向的是空地旁边盆地一样凹陷下去的地方。
满人堆里立刻炸开了锅,推推嚷嚷地朝凹地里跑去。他们彼此嘴里还嘟哝着,得快点,不然他们会从背后开枪,从背后开枪!
一个小脚老太太大叫一声后跌倒了。紧跟着的四五个人也倒下了,但很快又站了起来,连滚带爬地进到了凹地里。
“把便衣队剩下的石油泼到他们周围去!谁要敢跑出来,就杀了他!”
中队长冷冷地大声命令着。山内好像嘴里嘀咕了句什么,中队长并没有理睬他。
这些满人像是困兽一般,只安静地注视着日本士兵的一举一动。时间凝固了,就好像是大地吞没了世界上所有的声音。
(中略)
大火熊熊,红色的灰烬“噼里啪啦”地在空中翻飞。升腾起的白色烟雾淹没了人们的身影。
紧接着枪声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2]。
三、对异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解读
除却悲剧性友情这一主题的书写之外,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云》这一短篇小说还反映出了在“满洲”这一特殊历史舞台上所展示出的、异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极为复杂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从文学的空间设定来看,以村外的小山丘为界,爱莲生活在“山丘以北的满人部落”,小雪生活在“山丘以南的日本人村”。也就是说,“满人”生活在山阴地带,日本人生活在山阳地带。在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山阴山阳地带在气候上有着天壤之别。它不仅仅影响农作物的培育生长,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起居。不难想象,正是因为日本移民的到来,原本生活在温暖的山阳地带的中国人被赶到了寒冷的山阴地带。在教材版《云》中,作者将“土匪”的身份明确定义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反对日本人廉价收购土地和为所欲为的便衣队”。这一改写可谓昭然揭示了移民中国的日本开拓团的土地掠夺行为,以及其与日本国家的共犯关系。由此看来,山南山北两个不同的生存空间显然体现了日本移民与“满人”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重新确立。当然,也正是从这一文学空间的设定中可以看出作者阿万纪美子对日本曾经所推行的所谓的“满洲”移民事业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对于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满洲”这片土地的某种负罪意识。如前所述,阿万纪美子自幼在伪满长大,直至回国才惊诧于曾经生活了16年的“满洲”原来是异国他乡。这一事实的发现成为她日后频繁前往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试图弄清过往历史的动力。在对谈节目中,她常说:“每当回到温暖向阳的地方,我都有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觉得是自己侵占了本应属于那里的人们的空间。我无法回避这一事实。”[3]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清晰地意识到日本人与“满人”之间这种不正常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阿万纪美子才将《云》这部讲述异民族之间的友情故事的发生场所设定在既不是山丘以北,也不是山丘以南,而是南北交界线上的一座山丘上,且与成人保持一定距离的儿童世界里。然而,这个发生在村外山丘上的孩子间的友谊果真超越了“日满”民族间的隔阂了吗?
这一点,可以从中日两个孩子形象的塑造上来寻找答案。关于爱莲,文中丝毫没有提及其家人的存在,而其本人,从“没有坐过火车”“只看见过山北的满人部落和山南的日本人村”,当得知会被带去措林镇时兴奋得“连翻三个筋斗”等只言片语的描写透露出爱莲是一个家境困难却对外面世界有着强烈憧憬的活泼的乡下女孩。与此相对,文中关于小雪的描写则十分详细。在文本第二章的开头部分,作者写道。
父亲去村公所商量收麦的事情还没有回来。妈妈在给肚子里的宝宝织着毛衣,小雪在一旁玩着翻绳游戏。
小雪一家共三口,三十出头的父亲、母亲和九岁的小雪。不过到了正月,小雪就要成为姐姐了。小雪急切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2]35。
一幅中产阶级家庭的温馨场景跃然眼前:三十出头的年轻父亲,满心欢喜编织毛衣的母亲,以及在一旁玩着翻绳游戏、满心期待成为姐姐的小雪。另外,文中第三章还写到日本人村被“便衣队”袭击后的第二天,“学校放假,小雪今天不用坐火车去上学。上午,小雪帮着做家务,喂了猪、鸡,给浴缸装满了水。”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白米饭团,可见小雪和爱莲所处的家境全然不同。小雪不仅每天坐火车去上学,家里还养有猪、鸡等家禽,并经常吃到白米饭团。反观爱莲,既上不了学,也吃不上白米饭团。由此看来,前文提到的小雪之于爱莲饭团的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善举,但实际上只有当小雪处于支配者的地位时才能得以实现。这一点,作为孩子的小雪或许自身意识不到,但其行为不得不说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满铁员工收入表[4]
阿万纪美子的父亲是“满铁”的员工,如上表所示,1927年初,日本员工的月薪约为“满洲”人的3.6倍,日薪约为4.4倍。
因为是七口之家中的独生子——祖父母、父母和父亲的两个妹妹,从小似乎就有很多双手围绕在自己的身边。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说吃寿喜锅时,好像不用伸筷子,那些我喜欢的食物就自动跑到了我的盘子里了[5]。
父亲的高收入给独生女阿万纪美子带来了上述优渥的“满洲”生活。《云》中小雪的幸福生活场景,正是作者真实“满洲”体验的某种投射。另外,除了拥有温暖的大家庭,作者还曾就读于大连南山麓小学和神明女子中学,这两所学校都位于南山麓高级住宅区,属于富家子弟学校[6]。据她回忆说,当时不可能去中国人的住宅区玩耍,印象中学校里也只有一两个和日本人姓氏不同的低年级学生,日常生活中和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交集[5]192。由此看来,《云》中小雪和爱莲的友谊在现实世界中恐怕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难以维系,因为二人从一开始就注定处在了支配与被支配这一不平等的关系之中。爱莲这一“满人”孩子的设定,不过是体现了作者阿万纪美子对于超越民族壁垒的友情这一美好事物的希冀。与此同时,爱莲这一形象塑造的空泛也恰恰证明了“满洲”各民族之间实际所存在的生活上的差距和精神上的隔阂。
那么,在与儿童不同的成人世界里,日本移民与“满人”之间的关系在《云》中又是如何被书写的呢?下面,不妨来看几个例子。
例1,在二人的身后,还只是骨架的日本小学教学楼拖着长长的影子,静静地伫立着。就在刚才,还有很多满人在那里干活儿[2]34。
例2,平常早早就来了的满人佣人,不知怎么快中午了也没出现[2]37。
例3,原本应该有很多满人在教学楼干活儿,可现在连个人影也见不着[2]38。
虽说是一个日本人学校,却有“很多满人在那里干活儿”。小雪家中也雇了满佣。文中短短的几句描写,已然暴露出在殖民地“满洲”,日本移民是把“满人”作为“苦力”来使用的,二者之间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据有关学者考察①请参考高成龙,高乐才.论日本民族在伪满洲国的地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1(3):26;王胜今,高瑛.以“开拓”为名的日本移民侵略——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分析.东北亚论坛[J].2015(2):118;細谷享.満蒙開拓団と現地住民——日本人移民入植地における「民族協和」の位相――.立命館経済学[J].64(6)等论文。,开拓团原本鼓吹的是要做“原住民的先驱”,带领他们共同致富。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大部分日本开拓团若不雇佣当地居民实在难以完成农耕生产。因为寒冷地带的播种期短,必需快速作业。而当时日本移民的平均家庭人口为2.7,仅靠自家劳动力根本无法实施大面积的耕种[7]。小雪家雇佣了“满人”这一描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事实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便衣队、日本移民和“满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文本第二章中一段有关日本移民和便衣队作战的场景描写或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高高的石墙围起来的村公所位于村子的中央。这是去年日本政府的官员来视察时修建的。
山内站在大铁门前,拿着枪,仔细地确认进来的每一个人。男人们都发了枪和刀,女人也有一半发了枪。
“抚顺第二中队已经朝我们这里赶来。但到达这里还需要两个小时。请大家坚持一下!”
山内来回喊道。四十多岁的山内是这个村子的队长。就像平常紧急演练的那样,村民们已经各就各位。
架起梯子,枪口朝外。
(中略)
连着几声枪响,五六个人坠下马来,对方暂时撤退而去。
紧接着,激烈的枪声又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小雪,也不停地忙着运送弹药。
开始有人受伤了。小雪父亲的肩膀也受了伤。但是,能作战的人简单地包扎一下后就立刻又提枪回到了战场。
眼看子弹就要打完。再这样下去,只有冲到城墙外迎战来保护女人和孩子了。一旦让对方攻了进来,势必寡不敌众,全村都会覆灭[2]36。
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东北地区的反满抗日运动情绪日渐高涨。借此由头,日本关东军打出维持治安的旗号,正式开启了推行日本移民“满洲”的行动。自1932年10月第一次移民桦川县永丰镇起,至1936年7月移民密山县止,前后5次共约3 000日本人移民到了“满洲”。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满洲”彻底殖民化,更是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即在1936—1956年的20年间计划移民100万户约500万日本人到“满洲”。不过事实上,截止到1945年日本战败,据统计移入“满洲”的日本移民为27万人。《云》开头写到“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初建‘满洲国’时的事情”(教材版)。由此可以推断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由关东军主导的移民试行阶段,而这一阶段其主要任务在镇压抗日势力和应对苏联的南下进攻,因此大部分移民来自日本的“在乡军人”。即事先在日本国内接受短期的农耕指导和军事训练,移民后则接受关东军配给的武器和军服,耕作的同时肩负军人的职责,发挥作为“屯垦军”的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从《日本儿童文学》版《云》中上述激烈战斗场景的描述中,恐怕日本读者不但难以读出作为日本移民计划协从者的开拓团和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入侵“满洲”的共犯关系,而且只会对开拓团移民给予深厚的同情。之所以如此,其根源就在于作者对便衣队身份的交待模糊不清:究竟是普通的劫匪,还是不满日本移民“满洲”而坚持抵抗的民众武装呢?由于缺乏对便衣队行动的合理解释,于是主客关系发生颠倒:分明是自己的家园被侵犯、不得已才奋起反抗的便衣队成了袭击日本人村的罪魁祸首,而跑到“满洲”侵占他人土地的日本移民反倒成了遭遇不白之冤的受害者。众所周知,同情弱者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如此一来,日本的读者便会站到日本移民一边,认为引发悲剧的原因在于中国便衣队的袭击,从而削弱对悲剧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府为开疆拓土而实施的“满洲”移民政策及日本军人的残暴行径的思索与拷问。另外,也正因便衣队身份的模糊不清,文本中以内山为代表的日本村民对庇护便衣队的“满人部落”给予同情的相关描写也就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但是,在《现代日本童话》版和教材版中,尽管词句不多,却对日本移民前往“满洲”的目的有了交待——“他们都是怀揣竭力‘开拓’荒地梦想的人”。在教材版中,更进一步说明了移民前往“满洲”的原因,是因为相信了政府所说的“漂亮话”。此外,最大的变化则是对便衣队的描述。“所谓匪贼,据说大多是反对日本人廉价收购土地为所欲为的便衣队。他们白天和普通百姓没有两样,穿着同样的衣服,过着同样的日子。只是到了夜里就聚集起来,像黑旋风一样袭击日本人的村镇”。通过这一改写,便衣队的身份得到澄清,他们绝非平白无故袭击开拓村的盗匪,而是为保卫家园奋起反抗的普通民众。表面上处于优势的便衣队,实质上不过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满人”。当然,三个版本之间还存在一些细小的改动,在此不作赘述。总之,透过这些改动的语句,我们可以感知阿万纪美子随着岁月的沉淀,对“满洲”这一特殊时空认知的逐步深化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的自省精神,以及对日本政府曾经实施的“满洲”移民政策的讽刺与批判。
当然,改写部分也不乏存在令人感到遗憾的内容。譬如前面所列举到的3个例子在教材版中变成了如下的表述。
例1,在二人身后,还只是骨架的日本小学教学楼拖着长长的影子,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第179页)。
例2,平常总来的中国人,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也没来(第182页)。
例3,还在建设中的教学楼里也不知为什么见不着人影(第183页)。
对应《日本儿童文学》版中的内容,例1和例3删除了“满人干活儿”这样的字眼。删除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它却掩盖了在殖民地“满洲”日本移民和“满人”之间不平等的主从关系。例2中的“满人佣人”被改写成了“中国人”。尽管只是一个称谓的变化,但它却彻底消除了原有“满人”一词中所含有的歧视语感。同样是改写,但与前面所提到的对日本移民开拓“满洲”的原因、目的及便衣队身份的说明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增改不同,此3处修改可以说反倒让原有文本中具有的一个重要视点——暴露有意或无意支持战争的平民百姓与国家的共犯关系消失了。作为教科书,这一视点的缺失必然导致向日本学生传递的是日本民众是纯粹的受害者这一信息。某种意义上,这只能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认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版本的《云》,它都揭示了在殖民地“满洲”,不论是在孩子还是成人世界里,异民族间都存在着的复杂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四、阿万纪美子的“满洲”认知
综上所述,《云》是一个试图书写超越民族隔阂、关乎友情的反战故事。作者深知在实行严格民族身份等级制度的“满洲国”这一时空下表现这一主题的困难性,故特意选择了和成人世界保持距离相对纯粹的儿童世界,并将故事展开的具体场所设定在了处于中日境界线的“山丘上”。然而,和其他“在满”日本人一样,阿万纪美子自幼生活在日本人圈中,几乎没有与中国孩子有过实际接触。因此,《云》中所描写的中国女孩爱莲,也仅仅是作为其笔下主人公日本女孩小雪的友情单向输出对象而非一个真正实现对等交流的丰满人物形象存在。
而从《云》的两次改写中也不难发现,阿万纪美子对于“满洲”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譬如关于“便衣队”①即抗日义勇军。的描写,在《日本儿童文学》版的文本中被说成是一群身份可疑的盗匪,但在其后的《现代日本童话》和教材版中则成了土地被掠夺的普通“满人”。这一改写显然体现了作者对“满洲”认知的深化。但在教材版中,“满人”“部落”等称谓被修改成了“中国人”“村”,而关于被雇佣者“满人”的相关描写被删除。这一试图消除带有歧视语义的改写尽管体现了作者自身对历史、对“满洲”认知的修正,但与此同时,也掩盖了在“满洲”殖民地语境下支配与被支配的复杂的民族关系。
另外,《日本儿童文学》版中关于日本人村的描写给读者以一种它原本就存在于“满洲”大地的感觉,但在后来的两个版本中,作者对其增加了开拓意味的描写。由此,日本人村遭遇便衣队袭击的原因变得多少明朗起来。但总体上,作者强调的仍然是作为日本国策受害者一面的开拓团移民的形象,未能真正揭示其同时也是日本国策的实施者的另一侧面。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后来发表的《红风筝》反倒显示出了作者更为深刻的“满洲”认知。因为在文中,虽然爷爷坚信自己的儿子也即主人公加奈子的父亲“渡满”的目的是“为了五族协和,共建和平美好的国家”,但是孙女加奈子却清清楚楚地说到“爸爸的双手沾满了看不见的鲜血。只要在那里待过,就都一样。我的手也是。”在此,加奈子深刻地意识到凡是去过“满洲”的日本人其实都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不过遗憾的是,在文末处,金子还是向正在生气的爷爷道歉说“爷爷,对不起,让您伤心了。今后我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从这样的结尾处理显然可以看出,尽管随着岁月的发酵,阿万纪美子在文学文本中对“满洲”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和书写,但在严峻的现实抑或说某种社会共识面前,仍然显露出了作为一个书写者的无力和无奈感。
而这种无力和无奈感同样存在于从《一幅美丽的画》到《黑色马车》的改稿中。如前所述,《一幅美丽的画》(1969年)讲述的是因为苏联的进攻而开始逃亡,并在逃亡途中被迫走向自杀的“满蒙开拓团”的悲剧,它对日本战败前夕日军抛弃本国普通民众的政策和行为予以了揭示和批判。关于逃亡途中的情形,既有开拓民遭遇“满洲”当地居民袭击的场景描写,也有日本少年得到一位善良的“满人”和尚救助的具体记述。但在改写版《黑色马车》(2006年)中,相关内容被删掉。书写者的视点从异民族“满人”的身上彻底转移,使得一个原本立体丰满的关于“满洲”殖民地的故事简化成了仅剩下开拓民和日本军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此,笔者不得不扼腕叹息。
可见,阿万纪美子对于“满洲”的认知在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并未保持完全一致。1945年日本战败,“满洲”之于她,瞬间从“祖国·故乡”变成了“异国·他乡”。这一变化所带来的震惊促使其在撤离“满洲”回到日本以后重新对这一时空及身处其间的自我加以认真的思考。最终,阿万选择了作家这一职业,并以移民“满洲”的“开拓团”为题材,试图通过书写来揭露日本对“满洲”的殖民侵略,从而洗刷自身在“满洲”无知幸福地生活了十几年的罪恶感。然而,在“满洲”认知的重建过程中,作为写作者的阿万纪美子即便本着最真诚的态度,尽最大的能力去还原战争的真实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时局的影响。从前面所列举的有关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这一系列作品集中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和作为美军后勤补给大本营的日本(冲绳)是当时日本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让儿童了解战争的残酷,理解和平的重要性,以反战为内容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受到社会广泛的拥戴和好评。因此,日本的作家纷纷唤醒记忆,创作出了大量取材于战争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大多以二战中遭到空袭的日本本土为背景,内容多记述日本人受到伤害的经历。笔者以为,这些作品对于儿童了解战争的残酷性来说确有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掩盖和抹杀了在战争中犯下罪行、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的另一面形象,阻碍了普通民众对日本政府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创伤的清醒认识,以及自身也有意无意参与其中,成为战争胁从者的反省意识。以《云》为中心的系列“满洲”故事可谓独树一帜,它们以“满洲”为舞台,从正面对日本开拓民的加害行为进行了审视和拷问,并对日军之于中国民众的残暴行径加以揭露。当然,阿万纪美子的“满洲”故事如上所述并非没有问题存在,但笔者以为,恰恰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更为充分地体现了“满洲”殖民地这一时空的复杂性,以及作为文学书写者的阿万纪美子重建历史记忆的困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