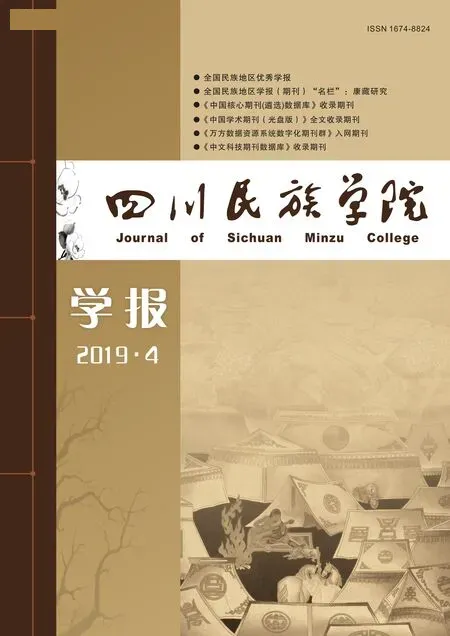清末新政与西南川边①新式教育改革
林 松
“清末新政”之季,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系行将崩溃,废黜科举、广兴学堂、引进新学、革除旧学的教育体制改革蔚然成风。在这场空前剧变的历史影响和推动下,川边地区在以赵尔丰为首的封建官吏的主持下兴起了别开生面的教育体制改革。它有别于清季川边地区各民族所接受的以寺院为核心内容的宗教教育,而是一种以藏汉双语教学为主,以推广和普及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为宗旨的新式学堂教育。只是因为当时国事多舛,危机深重,使这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之决策在落实中难尽人意。然则于今人来看,不仅其筚路蓝缕之功决不可没,且那种透露着忧患意识的新教育政策、教育理念于后世仍有启迪深意存焉。固需要当世者重新为之定位,以弥补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新内容。
一、兴起之背景
“清末新政”之季,在“文化兴邦,教育救国”思想的激劝下,川边地区以推广普及近代科技知识为核心的新式学堂教育大有燎原之势,之所以如此,倘无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区域内的近代化浪潮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固有文化的猛烈冲击,在“僻处荒蛮,声教隅绝”的川边亟图施行什么新式教育乃无可想象之事。仅从当时中国教育的角度看,值此列强环伺、“亡国灭种”这一关键时刻,若不彻彻底底澄清落后腐朽的科举教育制度的恶劣影响,代之以西方文明的新式教育,并探索出“救亡图存”之新式教育的亟急良策,“教育救国”口号明显是一句难以落实的空喊,尤是僻处国防前线的川边地区,当局力倡“教育救国”之意蕴便更加突显。它不仅利于改变川边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以来原始落后的局势,还从深远的角度看,此必有助于加强中国西南边疆的国防力量。
回溯西南近代教育史,不难发现,在清季鉴于历史、地理位置的缘由,川边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滞后于中原腹地和沿海地区,造成此局面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施行的某种特殊政策,譬如在政治上,清王朝竭力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君权至上,唯吾独尊”的大一统皇权,对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实施“拉拢地方土司贵族上层”,使其向化,以达到“联络属地,同化祖国之要枢”之旨。虽至雍乾以后,出于统治阶级利益的考虑,清中央政府于川边“改土归流”,但其统治的“忠君、顺化、天下共主”集权思想自始至终在不断地强化,人为制造专制集权的政治奇观,从而使川边地区成为与世隔绝的政治真空之地。
在经济上,由于清政府对边地采取异于内地的“羁縻政策”,并与“土司制度”一起实行,使得当地民众在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基本成为一个“守斯土者以奉行操防为尽职”的特殊性社会组织,虽然后来川边经历多次“改土归流”,可经济上依旧“粗糙单一,封闭落后”,这种貌似安定的经营模式实际上“利未见而害已(深)矣!”从此,川边地区经济便与内地差距逐渐拉大。
在文化上,川边地区一直被清王朝视为“蛮地”,川边少数民族为“蛮民”,而边地的地方风俗是以“藏传佛教”为主,与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相距甚远,加之地方宗教上层竭力维护传统的宗教文化,力避中原汉民族文化的影响,结果无形就切断了川边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契机,“使非教以礼仪,导其知识,将何以格氆氇之氓,而启文明之化?”[1]因此,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悉心谋划,在“改土归流”中被称为“经边六事”之一的兴学便成为重点经营的内容之一。
在教育上,川边地区由于深受西藏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川边地方的教育一直被土司贵族或者喇嘛上层所垄断,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读书识字,正是在此等原始落后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其所谓的“寺院教育”明显是远远地滞后于具有悠久文化底蕴的“儒家之学”,这无形中就更加大了川边与中原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待西学东渐后,最初的儒学已悄然于西方文明的冲刷之下风光不再,川边的宗教教育就更没有办法与时代接轨,何况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格局剧变之中,川边已由昔日的大后方陡变成英俄列强窥伺,竞相宰割的国防前线。可见此刻大力发展近代教育,迅速扭转川边地区教育文化落后的局面已然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如“教育救国”新思想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吹到了地处于边陲的西南地区。新思潮的兴起则开始于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前后,其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关于“教育救国”呼喊声尤其是震耳欲聋,“兴学为育才急务”[2]这一主张不光获得民众的认可,也迫使清中央政府将“尚实”之教育作为济世宝鉴,督促地方当局讲求新式学堂教育。自此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开始步履维艰地在中华大地展开。1905年清中央政府督饬地方各省“次第开办新式学堂”并着重强调新式学堂教育乃“握要之图”,这成为当时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该政令既出,川边立即做出反应的姿态,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筹措资金成立兴学机构付诸实践,而就当时川边文化教育落后的现实情况而论,骤然间实现“新”到“旧”的教育体制改革似乎不可思议。可是,形势咄咄逼人,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发动的两次侵藏战争以及沙俄对西南边疆的渗透,种种情况都极其猛烈地震惊了西南地方官吏与有识之士,这些士子无不感受到值此国难当头、危机四伏之际,必须要“除旧布新,有所振作”。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教育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川边“改土归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二、发展之过程
推行近代新式学堂教育乃当时我国教育体制之一大改革,而在西南边疆“则非学校之改革,直教育的创始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川边地区除了日渐废弛的寺院教育之外,几乎没有所谓的正规化教育,可是在“清末新政”时期经过清中央政府与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直至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已然成为了川边地区重要的教育形式,其发展当用“敷教最迟,而进化颇速;论程度则居后,论速率则超先”来进行概括。
当时川边地区新式教育是以“初等教育”作为起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川边地区原有滞后的教育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直到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川边地区除了日益没落的“寺院教育”之外,几乎已经没有所谓的其它类型的教育。早在前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之时,清政府为了兼顾在川边地区的汉家子弟读书识字曾于巴塘创办过义学,但是该校极不正式。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实施“教育新政”。就在此年,打箭炉的伍文元在城内开办了一所大同学校“是为川边近代教育所办学校之始。”[3]清末教育新政,赵尔丰于炉城(后改为巴塘)设立关外学务局统管川边教育。有鉴于川边“僻在蛮荒,其间夷民辙因声教隔绝,不时梗化”[4]及中等和高等各类学堂一时间猝难兴办的实际,当局在兴学初创之时就着眼于“以期教育普及”的初等学堂教育,这应该说是比较符合教育发展普遍规律乃实事求是之举。情况大致如下所述。
清中央政府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曾明确地规定:“设初等小学堂,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学。小县城必设初等小学堂二所,大县城必设六所,著名大镇必设三所”希望以此力图新式学堂教育能够迅速地在全国普及,为此,时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颁布《巴塘善后章程》里提到“一、学堂,蛮民于是不知道理,不知轻重。若能明道理,审轻重,亦无杀害凤大臣及法司铎之事,安能遭此次大兵,重者害及身家性命,轻亦伤损财物粮食,此皆由于不学之故。俟将来筹有余款,官为立一小学堂,无论汉、蛮,凡小儿至五六岁,皆送入学堂读书。不惟明白道理,将来并可为官,荣及父母,荫及妻子,岂不美哉!将来立学堂时,再定详细章程示知。”[5]此章反映出清政府统治上层设立学堂是为了维护旧有的封建统治,就当时情况来讲,能如此提出兴办近代学堂仍有其合理性。为了筹备办学经费,赵尔丰通过奖励社会贤达捐助,将战争所缴获匪物变价处理作为学堂经费。为鼓励优秀孩童深造,赵尔丰筹办了多处高等学堂,并置备印刷机器印刷图书,分科设学,凡“改土归流”之地,他都“设学”,且每“设置一县,即成立学校数处。”
依据清学部所颁《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初等小学教育为五年,高等小学教育则为四年”。由于川边地区教育较内地滞后,文化程度普遍降低,为迅速提高川边初等教育的步伐,关外学务局对学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凡“惟三年届满,即可变通毕业。”又根据中央学部的相关规定,川边初等学堂课程以讲经、修身、地理、历史、格致、国文、算术、体操等科目为主。由于川边教育起步较晚,学堂多系新设,教师尤为缺乏,当局相继创办四川藏文学堂、师范传习所等高等学堂临时培养师资,以补兴学教习之需。虽然西南川边地区由于教育基础较为薄弱,在全面施行新式学堂教育期间与内地省份教育比较是有较大差距的,即使与邻近的省份如云南、四川等也有差距。但是就本身比较低的起始点来讲,川边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乐观的。截至光绪三十四年,关外学务局在禀报该年学校情况时谈到“本年已成立学堂共三十四校,男女学生一千零二十五人。”[6]且该时期学校数量仍在动态性地增长,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川边共有各类新式学堂200余所,在校生总数约9000余人,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初等学堂快速普及与发展相比较,“清末新政”期间川边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究其缘由是与川边地区小学、中学的兴办均开始于教育新政之后有着密切关系,单纯地就学生生源来讲,初小学堂短时间兴办是难以把优秀的初小学毕业生输入相应的高等学堂,高等学堂教育自然而然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望其发展尚需时日。因此关外学务局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比如“先筹办高等小学之预科……于初小学堂各学生中考取最优秀者为预科学生。一年毕业,升入高等小学”。[7]此举为使达到快出、早出人才的目的奠定了基础。
另据统计,赵尔丰于川边兴学期间,从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关外学务局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将近三年多时日,川边地区初、高等学堂教育成效显著,其中绝大多数基础小学由政府督办,受教育者多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藏族学生),办学规模较内地并不算大,显示出川边当局创业之艰苦。
川边当局在其固有条件之下,尽其所能兴办“实业教育”,此举主要针对晚清川边地区所处内外交困的境况而作出的决断。正如前文所述,有清以来,地处西南边陲的川边地区由于土司势力的强大,使该地长期“与世隔绝”,近代以来面对英国的入侵边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更成为制约川边地区全面协调发展的负面因素。此外由于清政府西南防线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所洞开,导致外国殖民势力介入,川边地区社会生产力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务不堪收拾,产业亦不自保”,其触目惊心之场景,着实令人扼腕!此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局兴办“实业教育”势必就成为有识之士重新考虑的重要议题。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川边在“教育新政”期间所推行的“实业教育”是在政府积极督饬倡导之下循序展开的。比如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调拨银24000余两于巴塘地区开办制革厂,挑选边民先赴省城学习制革技术,学成回到家乡工厂工作。宣统二年川边当局又拟在巴塘创办陶艺学堂,制定规则,挑选寒门子弟学习制陶技术。同年六月关外学务局开办蚕桑局,招男女学徒学习,以期“学成真知良能,然后放归各处推广。”[8]另外当局还相继成立“农事试验场”、“农牧研究会”和“畜牧学堂”等等,这些实业学堂的相继开办为川边这块长期沉睡的土地带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疑是对发展川边地区新式教育是有利的。验之历史证明,当时川边在这种开放风气的影响下,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川边“实业教育”的起始阶段。
三、意义与不足
晚清“教育新政”时期,由于在川边地区藏汉各民族之间广泛推行了近代新式西方教育,使这片昔日看似荒蛮之处隐约间添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纵使此种类型的教育起步稍晚一些,并且因为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局限未能达到臻至善境,但是其历史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川边地区藏汉各个民族所推行新式教育的初始和发展无形中昭示了有清一代的统治阶级在川边地区长期施行教育蒙昧政策的失败,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川边藏汉各个民族中的人民从此可以进入学堂读书识字去接受最起码的知识文化,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通过新式教育的洗礼,为西南川边地区藏汉各个民族走出封闭、原始、滞后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文化准备,为川边人民从此以后能真正和全国其他各民族人民在文化、经济,尤其是民族心理和人文领域方面达到一致性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养料。无可否认,这也是赵尔丰及川边学人志士的初衷,当初许多忧国忧民志士痛感川边地区教育文化的滞后,他们殷切希望该地“人文蔚起”,期望当此国难之际能使教育为之凝聚国魂民心、多育人才。清末以来,学堂教育所开设的新学无论汉族、藏族,还是其他各个民族,无论省城、县城还是村镇,都一律设学,这就明显打破以前读书讲求门第、等级出身的界限,使学校教育管理体制正式纳入到一体化统管的现当代教育发展的轨道。此种变革不应该仅仅当作是便利了学务上的统一管理,而其深层次内涵则在于,它的出现,在真正意义上展现出现当代社会在文化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之民主内涵,与此同时也更意味着川边地区亘古以来“宗教寺庙”垄断文化教育政策的彻底破灭。虽然在当时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日甚的政治形态下,传统的旧有封建制度的瓦解,新制度的孕育、诞生看似并非一帆风顺、尽如人意,甚至其间反反复复,且此时川边近代化新式教育的发展远非尽善尽美,可是因为它终究是新生的事物,它的出现也体现出晚清中国与当时世界近代化文明潮流相接轨的新观念、新思想、新形势,固而从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阶段,它便孕育了顽强的生命力,他使川边地区藏汉各个民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其次,晚清川边地区藏汉各个民族所接受的学堂教育也是在西南边疆空前危机的情形之下悄无声息般崛起的,自然它随处都能渗透出一种浓郁的忧国忧民与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所谓实事多艰,亟应广兴教育,造就普通民众使之徐图文明而后进步。这便为此时川边地区各个民族新式学堂教育增加了更高层面的历史意义。其一,川边当局通过广兴新式学堂教育能将抗御外敌、守土之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潜意识般地融入到文化教育的实践当中去。其二,可以改变川边各民族经济文化落后、原始的状况,这无疑又是一种双赢的良策,不得不说此乃川边新式学堂教育的一个亮点。
再次,川边所行新式学堂教育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之上抛弃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看重儒家所倡的道德伦理纲常,轻视近代科技文明的传统做法,并将近代西方器物文明适当地融汇到教学课程中去。如川边兴办的初等学堂课程有国文、体操、算术、历史、地理、讲经、修身等,这就凸显了西方教育“经世致用”的理念。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当首推科举,明清之际八股又以“四书五经”取才,这就造成当时的士子们脱离实践,秉书高谈阔论,相较之下近代化的新式教育似乎富有生机,川边所兴各式各类学堂所采用的课本或借鉴西方文明或由当局结合地方特点编写教科书以适应本土化的需求,最大程度地展现时代化的科技文明与文化内涵,所开设的普通教学课程如英语英文、历史、舆地、算术、测绘等较之于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儒家纲常伦理”的教条空疏,前者更加利于学生们开阔知识,增长见识。该时期川边地区所开办的大多数新式学校里皆采用教师课堂授课的教育形式,所讲内容仍然保留有部分传统儒家伦理讲求的“尊孔、忠君、明伦”等思想,不过更为多数地增加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图画、测绘、算术、体操、格致等课程。这些科目对学生智力的开发与身心的全面发展无形中是极为有利的,该时期的新式学堂(初等、高等、官话和师范学堂)里,讲经读经课程比例大大缩小,对它们的设置也只是为了迎合川边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文化的需求而设,改变过去死记硬背的学经模式。历史、地理、算术、英语、体操等课程比例显著提升,这些内容的出现都极大改变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生员所学知识结构单一、知识范围狭小的境况,较之于之前的八股经义、儒学典籍来讲可谓绚丽多姿,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课程内容设置不仅合理、科学,还充分展现“学以致用”的新思想理念。如川边兴学期间,四川藏文学堂其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出英文、藏文、算术和体操课时最多,而修身伦理、国文、历史、舆地、图画、测绘等科目也占相对较多的比重,这些在传统的教育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晚清时期川边这样一个荒蛮、闭塞的地区,在多数边民还未知西方科技文明的年代中,近代新式学堂教育以它传承的方式向当地民众传播了当时欧洲人早已视之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当事人却视其绝妙、稀奇,新一代川边人正在学堂中学习电、化、声、光原理,认识了地球自转公转、牛顿定律,明白了原来在孔孟荀之外还有哥白尼、卢梭和孟德斯鸠,这些无疑对西南地区传统社会的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表1 川边教育改革期间(1906-1911年)四川藏文学堂学科及学年、学期时间列表[9]
然则我们也必须头脑清醒地意识到,在晚清内忧外困、积贫积弱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于西南地区大力实行新式教育是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固对赵尔丰川边兴学所取得的成绩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值此清廷大厦将倾自顾不暇之时,其内部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国库入不敷出、外部民族危机加剧,地处边塞的川边地区则因“穷荒坐困”而无一事不急着筹办,每筹办一事又不得不需巨款,且教育之事尚属长远投资,不待一时之效。由此可知,投入到新式学堂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定是有效,能办的实事也甚为有限。复次,文化之差异也铸成新式学堂教育发展举步维艰,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以藏族为主体世居此地,长期以来接受教育者少之又少,一时间迫使他们告别原来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突然纳入到近现代学堂教育之列无疑是很难适从的。因此川边民众“以派遣弟子就学为惧,乃由村保头人集资,雇请汉人子弟或贫穷儿童应之”,称为“学差”。每童每年雇价,藏洋(系硬洋)60元至100元不等。偏远地方,有至300元,代人读书,成为职业。”[10]特别是常居山林的部分藏族学生身体抵抗力较弱,对定居之地病毒的入侵难以抵御,他们来到学校加之生活环境的改变容易感染疫病。加之多数来到川地从教的教师多系外聘,不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无法体谅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生活困难,种种的一切使得当地百姓视上学为支乌拉(差役),心中不免抵触,固学校放假之后不再返回学校读书的学生较为普遍,更有甚者,有家长带孩子迁居它处,逃往山林之事似非鲜见。
纵然如此,晚清川边各族新式学堂教育还是在我国西南边疆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毕竟它是在较之于其他先进省区还艰苦的环境下孽生出来的新鲜的“产物”,毕竟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上层士子们所采用的一种较为缓和的历史抉断,毕竟是清政府为开发落后的边疆文化所尽的全力。固我们理应不过于苛责前人,而应对该时期川边地区各族教育给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以便作为今天所做同类事业一则有益之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