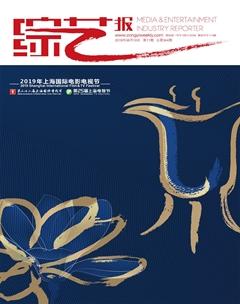制片管理应引入更多科学工具
陈昌业
一部影片在上映前,以导演为核心的主创团队,以及影片的制片公司、投资公司都会进行内部审看,这种制片管理制度上的审看行为,在影片寻找剪辑方向、确定粗剪和精剪版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参与此环节的大多是经过长期职业训练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的意见对于导演、剪辑来说是创作上的重要补充甚至是修正,而且常常会给影片带来艺术质量上的提升和改进可能。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专业性,有时候审看人士与导演、剪辑指导等主创互补、沟通得并不充分——特别是考虑到电影最终要面向观众,而如今一部目标是3亿-5亿元票房的电影就意味着要吸引几百万、上千万的观影人次,十几位或是几十位审看人几乎无法代表观众。毕竟,绝大部分观众都没有审看人的职业训练、艺术品位,以及中国人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的本位限制。观众们评判电影的时候可没有审看人的那些责任、负担以及忌讳。
艺术层面的探讨本来就是主观对主观,遇上大导演的项目,大部分制片公司都会面对难以说服导演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很早就引入了试映——借他人之口说服导演、剪辑,而这个“他人”又正是观众的代表,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说服力。
最近重温李安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也提到了自己曾经借助试映修改结局的成功经历:在《冰风暴》的剪辑阶段,李安曾通过试映会来了解观众反映,可没曾想,第一次试映会后,观众的推荐度仅有17%,和他此前最好的成绩差了70多个百分点。“试映那天观众没有心理准备,看是李安的片子,又是凯文·克莱恩主演,以为会很有趣。没想到笑闹中尽是挑衅,到后来产生弹性疲乏,就算少数喜欢的观众都没反应。对我来讲,这是个很新的经验。”成片完成前,《冰风暴》吸取试映会所提出的建议,共修改了18版。最终,该片大获成功,李安凭借此片确立了他在好莱坞A级导演行列中的地位。
因为反馈直接来自观众,所以试映可以更有效地针对市场去调整影片内容,包括改变剪辑节奏、删减片段或是增补/找回素材,以及为观众提供他们更喜欢的结局。尽管这可能会与导演对艺术的追求有冲突,但好在大部分导演都已认同“为观众拍电影”这一职业使命。
对于中国电影业来说,组织志愿者观众观看试映并非新鲜事,也有越来越多的电影项目会雇请专业的服务机构提供试映服务,以期尽早得到市场反馈,并据此对内容做出调整,创作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电影版本。
如今在試映的实践和研究上,国内已经有了更多的“新鲜”工具,但似乎还未被广泛应用。比如,很早就在游戏测试中使用的脑波测试、眼动测试——通过专门的仪器装置,记录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脑波反应、眼动轨迹。这种测试方法并不新鲜,也早已为科学界所认同,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如今可使用的设备更加轻便,对参加测试的观众来说也更舒适。相比于20世纪早期测试观众通过摇杆记录喜欢/不喜欢的方式,如今的设备能够更加敏捷和客观(实际上是观众自然的生理反应的记录)地给出测试结果。
最近听一位研究者介绍,她的实验室曾经以上面所说的实验设备为某国产影片提供过观众测试实验,也给出了测试结果,对影片的内容提供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但是,导演并未因此去做调整。直到影片上映后面对失败的市场结果,导演才后悔,也承认了他对测试结果的认同。
运用科技方法“算”出的结果,有时会被视为对艺术、对个人表达的一种冒犯,但实际上这种客观性也常常代表了可以被“预知”的事实。应当说,对科学工具的使用和信赖是科学制片管理含金量的重要基础。这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并不相悖,所有的管理都要做出平衡或是妥协。仅从试映这一科学方法的实践来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但似乎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